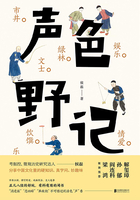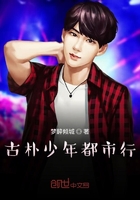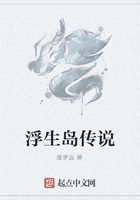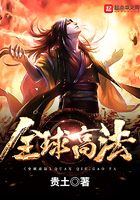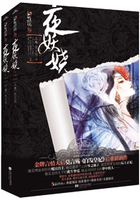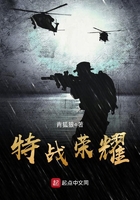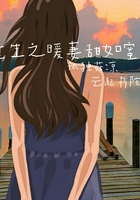说起小时候在农村过大年,还是无比留恋。那时候,每进入冬月,就有了年味。甚至每天都要问我妈一次:“还有几天过年?”盼望过年的心情可想而知。天越来越冷,大雪盖满了田野。每天早晨都有树挂,太阳一出闪闪发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地里没活,人都在家里活动,最常做的是扒麻秆、纺经子和编炕席。说起编席子,我也会,是跟我老叔学的。这席子也是为过年而准备的,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编出几领来,除了留出一领供家谱用,其余都在过年时铺在东西屋的炕上。过了小寒,进入二九,天更冷,猪也难喂了。每年都是由伯父先张罗说,“今天杀猪”,于是就杀猪。杀猪的时候我能干的就是帮着大人拔猪毛。猪杀好后,还要请亲戚和有交往的屯邻吃一顿。然后把猪肉放在窗下酱栏子里,用冰埋好,再泼上水冻住,到腊月二十七八再刨出来。
更多的准备是推碾子拉面。粮食打下来之后,放在仓子里,要吃的时候,得先要脱皮,推碾子是脱皮的主要方法。虽说推,但不是用人,而是用牲口拉,即把马或牛套在碾子上,蒙上它的眼睛,吆喝牲口拉着碾子转圈走。需要脱皮的粮食,主要是谷子和糜子。谷子推出来的是小米,糜子推出来的是大黄米。为了能推得干净,事先还要把粮食倒在炕上干燥几天。这样推起来,掉皮快,出米率高。我十一二岁就会干这个活了。因为碾子大家轮流使,每次占一回碾子就要推十多天。除了过年,还为明年一年准备好吃粮。拉面,非是现在饭馆里卖的那种面条,这个“拉”字在我们屯里读去声,意思就是“磨”,是我们家乡农村人加工面粉的一种古老方法。在“拉”之前,先把麦子用水喷湿,闷透,有时还要用抹布反复抹几次,以除去麦子表皮粘的浮土,然后上磨再“拉”。这个活最累的是筛面,得一刻不停地来回晃动架在笸箩里的筛箩。一头牲口一个多钟头换下来歇一歇,换上第二头。人一天下来,浑身飞满了粉尘,变成了一个白人,连眉毛都是白的。碾子和磨都安在一个屋子里,俗称碾坊。碾坊就设在我家的西厢房里,出门几步远就到,有事一喊,家里就会出来人帮忙。
另一件事是做豆腐。平时虽然也吃豆腐,但次数很少。过年了就要多做一些,家里做豆腐的高手是我伯父。每年一进腊月,都是由他张罗做,我们小孩只能帮忙打下手。第一步,泡豆子。先把黄豆簸净,去掉杂质,倒在大缸里,用热水泡上。记得在泡的时候,还要用凉水截一下,不知什么道理?浸泡一宿,待豆子都膨胀起来,再往下进行。第二步是拉磨。做豆腐与拉小麦不同,磨豆子要边拉边加水,做成稀浆。滴水方法,是用农家以前使用的泥盆,在底上钻一个孔,再用高粱秆横竖交叉做一个水流调节器,插到盆孔里,需要水多的时候,就往上提提,需要水少的时候,就往下按按。由人用瓢把水填到这个水盆里,水盆吊在磨眼的上方,称为“滴水盆”。拉出来的豆浆,马上倒在大锅里,一边烧火一边搅拌,以免煳巴锅底。待豆子拉完了,锅也满了,要多烧一会,彻底开了才行。因浆里含有大量豆渣,熬的时候,经常假沸,稍一不注意,就会溢得到处都是,所以必须用人看着。熬好豆浆,接着过包。在房梁上吊一个十字架,把包(实际就是一大块四方纱布)四个角系到十字架的四个臂上,在下面形成一个兜,兜下放一口大缸接着,把熟豆浆到兜里,用手摇晃架臂。为使浆都滤出来,还要用木制的夹板,狠狠地夹几下豆腐包,使豆浆彻底过滤出来。过出来的渣滓,就是豆腐渣,一坨一坨冻在仓房里,日后可化开炒着吃。第三步,点豆腐。过完包后,趁热点卤水。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序,必由伯父亲自操作。卤水过多,豆腐发硬,卤水不足,豆腐发软,没有经验的人很难掌握,点好之后还要盖上盖子焖上片刻。最后一步是压豆腐。这个工序就比较简单了,只要人有劲就可以干。豆腐做出来之后,留几块新鲜的当天吃。大部分都要送到仓房里冻起来,待到过年时再化了熬着吃。
每次做豆腐,都烧得热气腾腾,堂屋里伸手不见五指,衣鞋都弄得湿漉漉的。越是这样越觉得年味越浓,我们小孩子高兴地东西屋乱串,不着消停。
还有一项值得特别说说。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过年有吃粘豆包的习惯。但压黄米面比较费事,黄米得用水淘了,控干才能上碾子压。因是冬季,滴水成冰,一家一户压就难了。所以一说压黄米面,就全屯子一齐行动,家家都在同一天淘米。压的时候,先要用冷水把碾子浣一下,即把刚从井里挑来的凉水,泼到碾盘上,碾盘上立刻结出一层厚冰,用锤子把冰砸掉,就可以上米压面了。一家一家轮流地压,你帮我,我帮你,一直到压完为止。每年压面都要贪很大的黑,经常是到半夜才能结束。如果要冻冰,还要在碾坊里生上火盆,架上木头燃着,让火苗烤着碾子和筛面的箩。当然干活的人是近水楼台,手冻僵了,可以随时取暖,再加上总忙活,也就不感到太冷了。
男人在外面忙这些活的时候,女人在家里也不闲着。晚上贪黑给大人孩子做新衣新鞋,一做就到参星平西的时候,白天还要准备过年的东西。每次做饭都要多放些米,烧得半熟后,用笊篱捞出一些,做成饭坨冻起来,以备正月里玩牌,或看秧歌的时候,减少做饭的时间,到开饭的时候,拿出来放在锅里一化,烧把火就可以吃了。这些冻饭坨,有小米的,也有苞米茬子的。女人们最忙的是蒸豆包,黄米面压出来以后,要想吃到嘴里,得先发面,才能蒸豆包。发的方法也很特别,先烧一些滚开的水,把黄米面放在大号泥盆里一部分,倒上滚水,用勺子搅拌,烫成熟面。待凉后,主妇们就挽起袖子,边往里边加面边揣。揣匀后,放在热炕头上发酵。一次发好几大盆,这些大盆都是当地土窑生产的,有大、中、小三号,发面多用大号的,那时,我们家里做饭都使用这种泥盆,根本看不到铝盆和不锈钢盆。一两天面发好后,把事先烀好的豆馅包在面里,团拉圆了放到锅里蒸熟,一蒸就连蒸许多锅,要好几天才能蒸完。蒸好的豆包冻起来。有时太忙篜不过来,就冻生的,到吃的时候,捡回来一些,放在锅里一蒸,就做好了一顿饭。
在我们小孩心里总嫌年来得太慢,每天早晨醒来,第一句话就是问妈妈:“还有几天过年?”得到答复后,总嫌太慢。但实际上时间还是很快的,转眼就到了腊月二十三,这天是小年,照例要吃一顿饺子。每年小年前后,我爹都带着我们竖灯笼杆。找一根长木杆,上端固定一个铁环,穿上一条长绳子,绳子两端垂到地面。然后把杆子竖起来,一般是靠在马圈的柱子上绑牢,根部再泼些水冻结实,以备除夕夜升降灯笼。屋里妈妈、婶子和姐姐们除了洗洗涮涮,还把房子彻底打扫一遍。平时很难碰到的地方,也都把积垢除掉。如果有旧报纸,还要把墙糊一遍。然后把新买的年画,逐屋贴好。早些年有《香鹤美鹿》、《二十四孝图》、《鸳鸯戏水》等。后来有了新年画,如《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祁建华识字法》、《白毛女》、《小姑贤》、《将相和》等。当然解放以后,东西屋都要恭恭敬敬贴上一张毛主席画像。
腊月二十三晚上,是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候。把事先用秫秸篾编的车和马,买的大块糖都拿出来,再一碗凉水,供到锅台上,然后把旧灶王爷画点着,口中说:“一年过去了,灶王爷辛苦了。现送你回天,希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吉祥。”待灶王爷像烧成灰,就可以分大块糖吃了。这种糖平时没有,只在腊月里才卖,辽宁人叫它灶糖。其实小孩子热衷这个事,主要是可以吃到灶糖。每年过年,父亲都要赶一两趟街。龙泉比较偏僻,去一趟讷河,要走三十多里路。早晨起大早赶着马车从家出发,还得贪大黑回来。那时,父亲一去讷河,我就盼着快点回来,天黑以后,一趟一趟出屋去望,看见回来了,兴高采烈。当父亲把置办的年货都搬到屋里时,我最关心的是买没买炮仗。至于烟酒糖茶、鲜鱼、豆油、酱油、煤油、冻梨、年画、挂钱、红纸和香烛等等,看一眼就放过去了。把小洋蜡、鞭炮和二踢脚单独收起来,放在犄角旮旯。买回来的东西,往炕上一摊,任家人欣赏,红红绿绿,五光十色,屋里顿时有了过年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