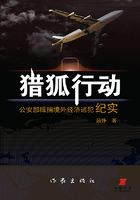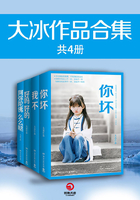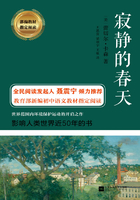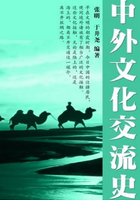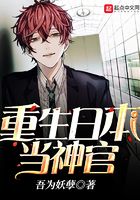大年三十这一天,是家里最热闹的一天,也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一天。因为从祖辈起我家就有这样一个规矩:不论是谁,在过年这些天,不能粗声大气说话,不能互相生气吵嘴,不能骂孩子打孩子。因此,我们小孩子,即使有了过失,也不受任何责罚,可以尽情玩耍。
这一天有好多事情要做。早饭过后,男人们打扫一遍院子,然后把借人家的东西,如锹镐犁耙、升斗、杆称和泥抹子等物都还给人家。再把别人借我家的一些东西找回来,不论大小物件,不能在外头过年。外边的活忙完了,回到屋里,开始供大纸。我有了一些文化之后,竟然成了先生。东邻西舍,老邻旧居,拿着红纸来找我写对子。他们要求不高,既不讲究艺术性,也不指定写什么。只告诉我有门对,有天地对,有灶王对,还有的要写三代宗亲。我有求必应,一家一家写好放在一边,等他们来拿回去贴。待忙完邻居们的事,我开始贴自家的对子。房门和过堂门,两边是对联,上面是横批,横批下贴上三张五彩挂钱。挂钱早年都是买现成的,自我学会了简单的剪纸后,都是我用剪子铰的,比买的还好看。院里还设一个天地牌位神龛,用耲耙竖起来做骨架,上下和左右用粪帘子围上,中间架一块木板,上面摆香炉和供品,也要贴上“天地之大也,鬼神其盛乎”的对联。
我家过大年最隆重的事情是供家谱,祭祖宗。布置神堂,称为供大纸。供大纸的人,多半是我爹,或是我叔叔。把家里使用的条桌,由我妈或婶子彻底刷洗干净,抬到长辈长房屋里。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席子,竖起来搭到棚杆上,形成一面席墙,靠席墙安稳条桌。妥当之后,打开宗谱匣,把里面收藏的彩绘家谱展开,挂到席墙正中,两边挂上彩荷配屏,再于配屏外边挂上大金字对联。上方借助棚杆挂好挂钱和横批,还有拉花,吊灯两盏也挂在棚杆上。之后把宗谱匣放在供桌上,这样就与桌面形成了两个梯次,第一个梯次是桌面,第二个梯次是匣顶。外屋厨房里,早已热气腾腾,蒸馒头,做供菜,累得汗流浃背。供馒头做得特别大,一次蒸不熟,先做个小的,熟后把外皮扒掉,裹上面再蒸一次,大约有二三斤重。摆到供桌两边,再插上两朵大翻花。供菜五碗,放在中间,上面也有供花。这供花是大姐张淑清没出嫁时,用手工做的。她还用面蒸过枣山,也是上供用的,她出嫁以后就没有人会做了。这些供品都摆在顶层上,下层即桌面上,中间是香炉碗,两边是烛台和香筒,合称五供。各空之间分别置小高脚杯四个,以装祭酒。供桌前还要围上红围子,上面印有鲤鱼卧莲图案。一切都摆放妥了之后,满屋顿时生辉。
这里说的实际上是龙泉以及整个东北早年民间祭祖的风俗。彩绘家谱,一般人家都有。上部绘着两位神像,一男一女,称为高祖爷爷、高祖奶奶。下部画着大门楼,门前绘着几个人物,说是家奴院公。门口还有一个童子,正在举火点爆竹。中间偏上部分是空格,上写一辈辈先人的名字,没有其他信息。人们都把这张彩绘叫作家谱,实际上它只是祖宗牌位,和南方大家族祠堂里的木制牌位作用一样。就我们屯的住户来看,大都是山东人闯关东者的后裔,一个屯里有几十个姓,各有各的祖籍。因此发明了这种祭祖方式,以寄托对远祖的怀念。就连最贫之家,也要请人写一个“某某门三代宗亲之位”供上。
供完大纸,就到该吃团圆饭的时候了。这时令孩子到屋外放几个炮仗,或放一挂鞭,全家人把桌子放一起,聚在一个炕上,寓示团圆。我家早年会喝酒的人不多,只有我叔叔能喝两口。孩子们自然以吃为主,有肘子肉蘸蒜酱、皮冻、小鸡炖蘑菇、煎鱼、酸菜炖粉条、拌凉菜、灌肠等。主食是馒头,小米水饭。饭后天黑,里外屋都点上灯烛,因供了家谱,墙上有年画,门上有对联,屋里焕然一新,显得特别亮堂。最高兴的还是孩子们,提着小灯笼,里外屋乱串。真有“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气象。
入夜,开始包饺子。把事先准备好的馅,和好的面,放到面板上,大家一齐动手,边包边讲瞎话(故事)。妈妈经常看着家谱前面挂的印版八仙挂钱,讲吕洞宾、铁拐李、曹国舅、汉钟离、韩湘子、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的故事。有时还讲《王小卧鱼》、《大黄狗和傻子》;婶子则善于说谜语。如:“南边来个白大姐,没有骨头没有血。”打一食品。“横三竖四一地麻,一根麻扒二两,共扒多少麻?”大表哥李占元饭后来串门,也参加出题,讲得更有意思。曰:“一山兔子一山鸡,两山并到一山里,数数脑袋三千六,数数大腿一万一,问有多少兔子多少鸡?”我妈爱听唱书,大表哥会唱,并带了唱本来。一边包饺子一边听唱。大表哥盘腿坐在炕沿上,捧着唱本唱。唱一段,念一段道白。歇气时,赶紧点上旱烟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记得有《呼延庆打擂》,《燕王扫北》,《小八义》,《张彦休妻白玉楼》等。大约九点左右,有人说:“该接神了!”大表哥回家去接神。我家厨房里也烧开了水,把饺子下到锅里。接神人提着灯笼,带着一二子侄,走到屯外,找一处地方,把香点着插在雪地上,再点燃烧纸,火光升腾时,洒酒于地。口中并说:“过年了,张门列祖列宗在上,我来接你们回家过年,请起驾回家接受香火。”然后跪地磕三个头,起身往回走。到家时,房门大开,意为身后的神可以进屋,归到祖宗板上。饺子已经煮好,先盛两碗上供,每碗里两个饺子,放在供桌两端。同时倒上酒点着,酒火蓝蓝;烧上香,香烟袅袅;两只高烛齐辉,好像供桌上真有了神灵。一家老小,分别跪地磕头毕,上炕吃饭,多因刚吃得酒足饭饱,每人吃两三个饺子,就不吃了。
接着继续包饺子,讲瞎话。上岁数的老人,喜欢安静,躺在一边睡觉。小孩子精神头最足,提着灯笼东西院串着玩。包完饺子,年轻姑娘、媳妇开始玩嘎拉哈,守岁到半夜。
那时农村没有钟表,靠看日月星位行事。参星偏西,开始发纸。屯里家家院中火光冲天,鞭炮齐鸣,声震夜空,这红火热闹的场面标志着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到来,正是过大年的高潮。我家习俗,每到这一刻,把一家人都攉动起来,睡觉的小孩也叫醒,穿好衣服,以防感冒,男孩子由大人领着到院里举行祭天拜地仪式。院心放一张桌子,把屋里供桌上的供菜和供器端出几样,放在桌子上。旁边用好柴生起一堆明火,灯笼杆上红灯高挂,天地神位前明灯亮烛。我们和叔叔燃放鞭炮,响声与临院鞭炮声遥相呼应,整个屯子都在沸腾。马圈里的马匹,惊吓不止。每当这时,伯父都要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盆小米饭倒在马槽里喂马,口中说:“打一千,骂一万,年午黑夜一顿饭。”算是对牲口一年为人出力的慰劳。最后不论老少都要给天地磕头,我家是南城人,所以面南而拜。此刻,屋里掌勺的主妇已经煮好了饺子,出锅先捞出四个,分别装在两个碗里,给祖宗上供。待外面发纸的人撤回屋里,把供器和供菜等都放回供桌上,就开始给祖宗磕头和互相拜年了。
磕头从家里年高位尊的人开始,跪在地上面向着供桌,边磕边说:“给祖宗磕头了。”其余的人,也这样继续给祖宗磕头,同时还要给长者拜年。但不对着本人,对着家谱,磕一下,喊一声:“给父亲磕头了!给母亲磕头了!给大哥磕头了!给大嫂磕头了……”,等等。辈分越小头磕得越多。当然这个头也不白磕,可以得到长辈的压岁钱。这个程序结束,全家人围在一起吃饺子。为图吉利,包饺子的时候,有几个饺子里包了硬币,说谁吃到硬币谁一年就有钱花。还有几个饺子包了橘子瓣糖,说谁吃着谁嘴甜。结果孩子们大有不吃到不肯罢休的意思,逗得人人乐得非常开心。
吃完新年第一顿饭,愿睡觉的睡觉,愿玩的玩。年岁大的人,一般都和衣而卧。小孩子则玩嘎拉哈,或者用纸牌摆八门。早年还有全屯拜年的习俗,人们成群结队挨家挨户走,进屋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跪在供祖桌前就磕头,口中说:“给你们拜年了,过年好。”然后起身就走,去第二家。地上铺着麻袋,我大娘盘腿坐在炕上,叼着烟袋等着。家里也预备了瓜子、糖块等,但很少有人坐下来吃一点。这样几乎一直到天亮,人们才和衣而睡,但没过多久,太阳一出,外面的炮仗又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