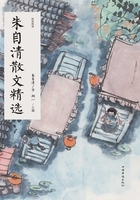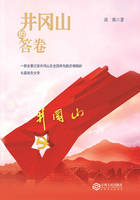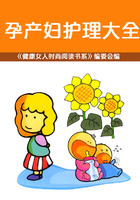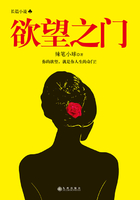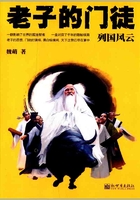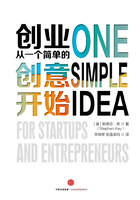大年三十一过,年味就开始下降。从初一到初五,我家每天早晨都吃饺子。一天两顿饭,晚上吃事先准备的干粮和饭坨。人们玩够了,把饭坨拿回来放在锅里一化,做成水饭,再热点馒头豆包之类,清淡可口,吃完了再玩。年轻姑娘和媳妇聚在一块,歘嘎拉哈。这东西就是猪后腿上的一块骨头,每年杀猪都有两个,攒的年头多了,家家都有一小笸箩,辽西人叫“猪子”。“嘎拉哈”这个名字,我猜想可能是满语。它有四个面,分别叫“肚、背、驴、珍”,辽宁人把“肚”叫“背”,把“背”叫“坑”。有两种玩法:第一种玩的时候,几个人都行,坐在四周,把嘎拉哈倒在中间。轮到谁,谁就把码头往空中一抛,看准炕上自然散开而成对的嘎拉哈,比如两个都是“肚”,迅速抓起来,反手再接住码头。不掉就算成功,两个子留下一个,另一个砸向嘎拉哈堆,使之能出对。有时候,两个一样的隔得很远,中间是别样的,就得学会跳。即在抛起码头时,能迅速把两个都抓到手里。如果有三个子在一起,两个是成对的,一个是不一样的,还要学会吐“一”,就是在把三个都抓到手里,接码头时扔出一个子。玩得好的,一口气能把所有的子都赢过来。玩得不熟练,一有失误,就要把码头交给下家,这样轮流进行。在我的记忆里,玩这个,大姐张淑清总是拔得头筹。所谓“码头”,就是用旧铜钱十几枚,以红绒线穿起来,两头系在一起形成的小钱串。喜欢轻一些,就少用几枚。我家原有旧大钱好几大串,是用来镇蜡台的。那时,过年买回来的洋蜡,又粗又高,分量很重,插在蜡台上,会把蜡台压翻,所以就用钱串子坠着,名曰“镇”。后来大钱都叫我们小时候扎毽子,姐姐们做码头用光了,现在连一枚也看不到了。想起来,感到十分可惜。
第二种玩法是掷珍:几个人玩的时候,把“嘎拉哈”平均分开,每个人都一样多,然后约定一人拿出几个。如两个或三个,放在一起,由一个人捧起来,掷到炕上。当这些“子”散开时,大家一起观察,看有没有“珍”出现,如有就捡起来,收入自己囊中。捡完之后,拿出一个“嘎拉哈”,捏着一头,拨拉其余的“子”。如果也能出“珍”,也算自己的。如果没拨拉出“珍”,就算失败。必须交给下一个人玩,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有人赢了满贯,有人输光了为止。
男人们,愿意看纸牌的,出去找人看纸牌。愿意听书的,就找一个识字先生聚在家里说书。愿意热闹的,就领头把人组织起来,扭大秧歌,到各屯去演出。到谁家院里,先扭一圈打个场子,然后领队人,随着鼓点起落亮一个相,冲着这家门口唱道:“一入新春喜事多,春人路上唱春歌。春风春雨下春种,春女楼上绣春罗。”唱一句,打一通锣鼓,扭舞一阵。秧歌队里,都是年轻男人,装女角的擦脂抹粉,包上头,戴上花,扭起来也蛮像闺中少女。有时还有各种扮相,如:猪八戒、孙悟空、沙僧和唐僧;还有“许仙借伞”。我二弟凤祥,十几岁时,扮过一次青蛇,很受屯人青睐,都说很像。队伍中还有一个人装老太太,拿着特制的长烟袋,扭扭搭搭,逗得看客捧腹大笑。队伍后头还跟着一个骑“驴”的媳妇,身傍扭着一个艄公模样的人,装作划水,看客称之为“跑旱船”。每到这时,屋里玩“嘎拉哈”的姑娘媳妇也都出来看热闹。凑趣的孩子,在人群里趁人不备时放几响炮仗,吓得胆小的人,捂着耳朵到处乱躲。这种秧歌队,每天要来一两次。一听屯头有锣鼓响声,扔下手里的事情就往外跑,看了几遍,还是看不够。
半大孩子,像我这么大的,没热闹看时,就聚集几个伙伴,在院里扣匝玩。我小时候,很爱动手做东西。春节一过,阳气上升,春风渐高。我就鼓鼓秋秋做风筝,但所做风筝,没有一次能飞上天的。倒是做的风翅楼,质量不错,能玩好长时间。“风翅楼”是我们家乡的方言,大多数地方都叫“风车”。做起来也比较简单,找一块硬点的彩纸,裁成正方形,然后沿四个角,向中心方向铰开,不能铰透了。把铰开的角,提起一个顺着一个方向,集中到一块粘牢。在中心用香头火烧个眼,用铁丝穿上轴,安上一个把,举在手里,顶风一跑,就呼呼转了起来。
到正月初三,我家习俗还有一项活动,就是送神。据父亲讲,很早以前都是初二送神,有一年过年,出去玩了。回来太晚了,就说明天送吧,这样就改在了初三,以后就成了定例。初三天黑以后,大家玩够了,到夜深时,把包好的饺子煮上一锅,先给祖宗上供。祖堂上灯烛齐明,香烟袅袅。这时把已睡的孩子或大人都叫醒,放上桌子全家人吃饺子。吃完,由一成年人拿一个水瓢,里面放点水,到供桌前,一边说:“年过完了,我现在送你们回山。望祖宗保佑一家老小平平安安,旺旺兴兴。请即刻启程,跟我走吧。”一边把供桌上的东西,各样都揪下一点,扔到瓢里。然后提着灯笼,带着二三子侄,开门去到原先接神的地方,把水瓢里的东西撒在地上,燃着三炷香,洒点烧酒于地,烧纸磕头,并说:“到时候请回家过正月十五。”反身回来,到门口把水瓢扣在马窗台上再进屋。这时屋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供桌上的供菜已全部撤掉,彩色家谱已经卷起,露出后面写成壶形的“喜气满堂”和金字对联,只留下五供和其他装饰。这样一直放到正月十四,每天三遍香,夜间点着长灯。送神以后,把这几天积下的垃圾,脏水都倒掉。因为祖上留下的习俗,从三十到送神前这几天,不准往屋外倒东西,怕把运气倒没了。正月十四把家谱再供起来,规模和三十那天一样,正月十六晚上睡前撤供,正月十七早饭后,全部收起来,放到宗谱匣里,把宗谱匣放回原来的地方,至此才算过完了年。
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我们那一带人家,都有给祖坟送灯的习俗。吃完晚饭,天一黑就把事先做好的面灯带上,再用小瓶装点豆油去到坟地。所谓面灯,就是把面粉和好,做成一个高脚杯型,用香缠上棉花,插在杯心,然后冻硬。这事一般都由妈妈和婶子来做,而送灯,就是我们晚辈人的专利了。到了坟头,在地上踹个雪窝,把面灯放在里面,倒上豆油,点着。如果是二人合墓,灯里做两个灯捻,然后烧纸磕头起身回屯。这时再回头一看,野地里,白雪中灯光闪闪,也很壮观。这风俗现在还有,不过不再做面灯,改用一种使用五号电池的灯。
正月十五老百姓也叫“灯花节”。早年有撒灯的举动,即在一口铁锅里,把谷糠伴上煤油,用明火点着,用马爬犁拉着,沿着村街,边走边撒在地上,看起来像一条火龙。还有一个请姑姑的活动,到寡妇人家偷一个饭勺子,那时饭勺都是木制的。拿回家,把饭勺糊上纸,画上眉眼鼻口。下面用树权做腿,再给它穿上小衣服,由童子背着,后面跟几个人,念着什么咒语,专找胡同旮旯的地方走。据说姑姑专在肮脏的地方生活。转几圈以后,问背者:“沉不沉?”如说沉就证明请到了。转回家中,炕上放一张桌子,用人扶着站在桌边。然后一帮人围着问吉问凶,事先声明,好,磕几个头;不好,磕几个头。这“姑姑”就磕起头来,有时说好有时说坏,也不知真假。玩闹够了,再顺着原路把姑姑送回去,把饭勺子拆下来,洗干净,偷偷给人家送回去,这种活动后来就没有了。
正月十五晚上,还有一个健身活动。就是年轻女子成群结队,到南沟子上去滚冰,说可以防病祛灾。我也随姐姐们去过,躺在冰上看着天上的明月,可地打滚,也别有一番诗意。正月十六晚上,在睡觉前,令一个孩子提着灯笼,房前屋后,犄角旮旯都照一遍,说可以求得全年亮亮堂堂,至此快乐的大年就结束了,小孩们又盼着过下一个年了。
不过,还有一点应该说说。我们那块的人把初一到初十,都与事物联系起来,一天代表一样事物。常听大人说的是:“一鸡、二菜、猫三、狗四、猪五、羊六、人七、马八、九籽、十成”。而在《荆楚岁时记》里,则为“一鸡、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这可能是中国南北差异所致,但鸡日和人日是一样的。每年到人日子这一天,几乎家家都要吃打卤过水面条,祈人长寿,而且十七,二十七也吃,说是中和老年的日子;初十这一天专门吃饺子,说可以看一年收成的好坏,这个风俗一直流传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