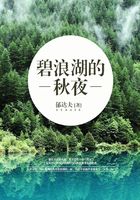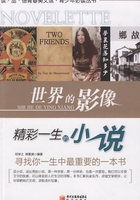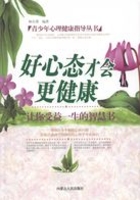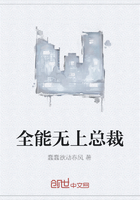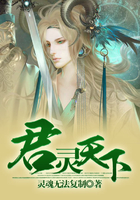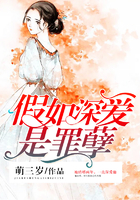我家是1935年前后搬到大门陈家屯的。我们的远祖原居山东省登州府荣城县,大概在清朝嘉庆年间,远祖只身逃荒到东北,落户在绥化县东北地屯。从那时起,到我父亲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大约百年有余,可谓农耕世家。但自己没有一寸土地,都是在人家的土地上流血流汗。我爷爷那辈共有哥七个在一起生活,后来遇上荒年,实在无法维持,就分了家。分家时爷爷已经去世,奶奶李氏带着我父亲哥仨,听说讷河这个地方地广人稀,日子好过,就决定到讷河寻找生路。全家人携儿带女,一台马车拉着仅有的一点家当,从绥化东北地屯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走,才到了讷河。先在祝家粉坊屯落脚,住了三年。听说大门陈家对耪青户比较宽容,遂有意挪动挪动。所谓耪青,就是从陈家租地,自己独立耕种,到秋向陈家交粮。一般情况都是四六分成,但陈家是倒四六,即四成交给东家,六成留给自己,而且还不计较场院底子剩粮多少,所以一些流离失所,没有地种的农户,都愿意到大门陈家来耪青。而且陈家势力大,盗匪不敢轻易光顾,相对比较安全;屯里还有学校,只要年交粮一斗,小孩子就可以上学念书。所以又托熟人崔国良引线,把家搬到了大门陈家屯。开始没有住的地方,暂住在陈家看场院的窝棚里,后来搬到后街的一个土屋里,再后来又搬到陈家大院西侧的一所三间草房里,一直住到解放。这些房子都是陈家盖的,入屯之户,只要租他家的地种,房子白住,不收房租。这也是许多耪青户愿意到大门陈家屯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土改”以后,家家分得了土地。我家也拿到了政府发给的地照,有了自己的土地,种地劲头更足了,父亲老哥仨个,一刻都没有歇着的时候,起早贪黑,从春到秋,忙完地里,忙场里,一天总有活干。粮食多了,日子越来越好。
我出生后就没有见到过爷爷。听父亲说,爷爷张有钧特别勤劳,年轻时给人家扛活,干活不惜力气,不顾性命,四十多岁,因伤力过度咯血,故去了。在我记事的时候,家里只有奶奶,大爷(伯父)大娘和三个女儿,父亲母亲和我们大哥仨,老叔和老姑还没有结婚。全家13口人,在一起生活。
我还依稀记得奶奶的模样,慈祥可亲,脚很小,走路有些不稳。她在世的时候,我一被父母责打,奶奶就护着我。家里大小事情多由奶奶拿主意,决策干练,办事果决,深受晚辈尊重。可是没过多久,奶奶就去世了。记得时间是农历五月的一个热天把奶奶送走的,葬在屯后南北垄地的北头,现在推算当在1943年左右。奶奶去世后,家里家外的事情就由父亲张罗,先是打发老姑出嫁。我本来有三个姑姑,大姑夫家姓李,丈夫叫李海,腿脚有残疾,外号“李瘸子”,在本屯居住,生一子名李占元。二姑夫家姓王,丈夫叫王凤洲,因读过私塾,人称“王三先生”,一辈子务农,在祝家粉坊屯住,生一子三女,子叫王福年。老姑此时还没有结婚,照那时的标准,年龄已经很大,经媒人牵线,嫁给大门郑家屯的尹大贵,做了填房。出嫁的衣物,箱柜和当用品,都由家里操办,一应俱全后,完成天作之合。婚后生一子一女,子叫尹相春。接下来是叔叔的婚事。叔叔张振清1923年生,到1945年已经23岁。这在那时的农村来说,已经是很晚了。家里人着急,父亲四处托人,找媒人,看了许多人家女子,最后选中了友谊屯张绵海的妹妹张景春,在经过一番争争讲讲的口舌后,财礼总算定下来,于当年顺顺当当把婶子娶到家。第三年,婶子就生下了四妹张淑琴。
这时我的堂姐也都大了,二姐张淑芳1930年生,17岁就出嫁了。丈夫是在学田乡和庆村老安家屯住的马汉波,因系父母包办,婚后感情一直不和,1950年“新婚姻法”公布后离婚。回家后,精神郁闷,于1952年患肺结核去世,仅活了23岁。生一女,被马家人送给讷河北门外一户纪姓人家。大姐张淑清,1927年生,比二姐出阁晚,嫁讷河东孔国乡双发屯李希增,也是填房。李家是地主成分,大姐因病于1962年去世,所生一女一子,都长得非常标致。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不了红卫兵的歧视,女投井,子上吊自杀,两人都二十多岁离开了人世。
早在“土改”之后,因原来的住房已经破旧,父亲决定另盖新房。房址选在后街离井沿最近的地方,我听父亲不止一次说过,是为了挑水方便。那时农村家家都吃井水,白天在地里劳动一天,晚上回来不论怎样累,再不愿动弹,也得挑满一缸水,以备第二天使用。不然第二天做饭就成了问题。这个房址,离井大约有四五十步。打好地基后,没用两天大框就起来了,因为有屯邻帮忙,人多千活快。可是剩下的零活就相当费工夫了,足足用了很长时间,才有了眉目。为了省钱全买的是杨木柁檩,土垡子墙,砌完后还得用泥抹上。我虽然很小,一天到晚也在现场忙活。天快要凉了,才搬进去住,冬天冷得不行,后墙挂上厚厚一层霜,屋里像冰窖一样。第二年,因墙干透了,就好了许多,不那样冷了。房子是三间,中间是堂屋,两头住人。东屋南炕是大爷大娘,西屋南炕是我爹我妈,北炕是老叔老婶。南北炕中间靠山墙有一万字炕相连,北炕烧火时,烟从万字炕里头流入屋外的烟囱。这烟囱坐在地上,很像一个以前烫酒的硕大酒壶。早晨一起来家家炊烟缭绕,特别是冬天,满屯雾气腾腾。这时的龙泉屯,已由一趟街变成了两条街,看上去很像一个“二”字。
在两个姐姐出嫁以后,我记得还有一次分家。伯父感到分开过好,就提出分家。记得当时我家请了许多人:有崔国良、李大脚、关校长、李凤山等屯邻。在家里炕上喝着开水,抽着旱烟,往一起说和,持续了五六天,没达到目的。最后由关校长写了一份分家单,当时我小,不懂得是怎么回事。后来看到这个分家单,上面写得很细,从院里的车马农具,到屋里的缸瓮,以及各种小东西和房子都做了分割。事后只有大爷和大娘,搬到后街东头的一个小马架里住了。就在这一年(1948年)冬天,大娘因受惊吓,得了大出血,没治好,去世了。大娘娘家姓傅,是富裕人家女儿,1906年生,享年43岁。大娘继奶奶作古之后,我们小孩又少了一个护着的人。大爷和大娘对我们都非常疼爱,有好吃的给我们留着,有好玩的给我们买来。他们也生了三个男孩,但都在很小的时候夭折,一个没有站下,所以拿我们特别为重。在大娘去世的时候,为打幡之事,大爷曾提出把我二弟凤祥过继给他为子。父亲二话没说,当即同意。我清楚记得八岁的二弟,由父亲帮着,打着灵幡走在送葬队列前面的情形。可是后来,也没有明确的过继仪式,也没改口,但在思想上,全家人都是承认这个事实的。因大娘去世,大爷和他的小女儿——我的三姐,刚刚十多岁,两个人无法再顶房住了。没到半年,大爷又搬了回来,归到一起,仍住东屋南炕。可是,疼爱侄儿的大娘,却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至于我叔叔,虽然有了分家单,但压根就没有另立门户,一直和父亲在一起过。分家重合之后,因为有了土地,老哥仨干得更起劲了。连年粮食丰收,有了余钱,又在井沿附近盖了一个粉坊,每年秋天土豆一下来,就开始拉磨漏粉。这时家里养了两头大犍牛,四五匹马,一台钢轴车。牛拉磨用,马拉车、种地用。所产的粉条,都送到讷河城卖掉,家里不愁吃不愁用,并略有结余。生活宽裕了,干点什么,老哥仨合计来合计去,买地吧,地多了将来会不会像陈家一样被分掉,那样就白忙了,这条路不能走。想来想去,何不给孩子说媳妇,一旦娶到家,谁也抢不走。那时我虚8岁,订的是日本屯(后来改叫和盛屯)陈洪生的二女儿,小名叫二丫;二弟凤祥订的是本屯崔国良的孙女、崔永江之女,乳名二孩子;三弟凤家订的是永发沟子北老桑家姑娘,眼睛有点毛病。我们仨,相差都是两岁,女方又比我们各大两岁。当时的观念是说大媳妇,可以早点娶到家里干活。就这样我们仨的终身大事,在父辈的“扔把笤帚占一个碾子”的思想指导下,精心而又草草地定了。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公布以后,屯里凡是这么小订婚的,都纷纷解除了婚约。我家父辈规定:女方不提,决不许我们先提。结果只有桑家提出解除婚约,三弟被解放了。但父亲相当不高兴,曾和我商议,要去桑家理论。我劝父亲不要去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父亲还是去了,把桑家人说了一顿,才算完事。我和二弟长大后,按父辈要求,如期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