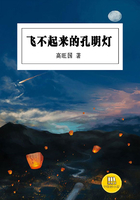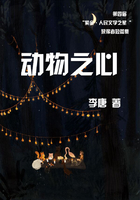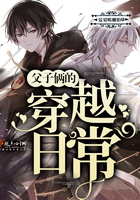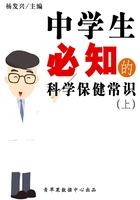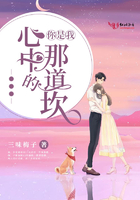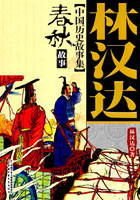他突然将她推开,接着感到一阵眩晕,烛光像波涛一样在眼前晃荡:你太……
她跌坐在椅子上,并不惊吓。她冷冷地笑了笑:太怎么了,太贱还是太骚?
你太难为我了……父亲尸骨未寒,你怎么能……他浑身战栗着,背过脸去。如果不是怕把风声闹大,刚才他会照着那血红的嘴唇一拳砸过去。
叶家难得出这么个孝子呀!她说,不过,二少爷……
别说了!
怎么,你都不许我这个继母说话?你不是很孝顺吗?
我求求你,别说了……
她站起身,在他的面前来回踱了几步。过了会儿,她又说:二少爷,其实我不说你也该明白,脸皮重要,脑壳更重要,你珍重。她准备出门。
你……他失声叫道。
我该休息了。
她回头看了看他,对着他的脸轻轻吹了一口气,就迈出房门:莲子,给我打洗澡水!
他目送她下楼去。楼道上没有灯光,黑洞洞的。她有节奏地踏着松木的台阶,似乎在刚才莲子一脚踏空的地方现在这个女人也停顿了。他感到她回了回头,对他露出一副得意的笑脸……他仿佛被黑暗中射来的两柱锐利的目光灼了,连忙把身体移到了门里,掩上门,额上汗涔涔的。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他想自己毕竟太书生气了,太幼稚了。自以为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谁料有眼睛早就盯上了他。这样事情会弄糟的。会不会是虚张声势?这女人闯江走湖见多识广,而且胆量很大。也许是捕风捉影,趁机要挟。一个几乎寸步不离罐子窑的姨太太能知道多少外面的事?除非有耳目。是谁?他首先想到了老大。难道叶千帆会同这女人串通一气来暗算我?他们不是正为家产私下摩拳擦掌吗?是假象?如果不是老大又会是谁?六指?莲子?还是专门在外面安插了别的什么人……
这时候外面响起了狗吠声。他想,老大回来了。于是他用毛巾擦了把脸,随便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坐下来。他估计老大要来这屋子。果然,没一会儿工夫,叶千帆敲门了。
见你这儿还亮了灯火,就来坐坐,听你说说外面的事。叶千帆说。
他递给兄长一支香烟,他已经想好这出戏该怎么唱。
叶千帆摆摆手,说早戒了。他说:外面想必一定很热闹吧。
他自己把烟点上,安到烟嘴里:还是先谈谈家里的事吧。
叶千帆点点头,说:也好。如今父亲走了,太太来的日子很短,对家里的事还不完全了解。你难得回来,兄弟间是该好好计划计划……
关于家产?对此我不感兴趣。
不,也不仅仅是家产。
大哥,他吸了一口烟:我们是不是先把有些事情弄清楚?
叶千帆看了看弟弟:哪些事?
这个家不明不白的事太多了……叶之秋站起身:父亲是怎么死的?一年前谁向父亲打的黑枪?
良久,叶千帆说:这正是我要追查的!
一只手突然按在我的肩头,我吃了一惊。陈士林像一只猫似的进来,我一点也没发觉。他拿过我的笔记本,看看我刚写下的,也就是以上那一小节,笑了起来:
“真有你的。早知道小说可以这么弄,我也能写。”
“这活不难,不过也不轻松。”
“你干吗不去写诗?”
“我没写过诗。倒是写过诗评。”
“写诗不累。一张香烟皮在厕所里也可以写出诗来,说不定还是了不起的诗!”
“你是不是写过诗?”
“律诗倒是也作过。我喜欢填词。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如今没工夫倒腾这玩意儿了……”他突然又问:“你这到底算历史还是算小说?”
“当然是小说。这是我的副产品,也许可以看作对历史的一种补充。”我说,我觉得他是有话要说的,既然他看了我的笔记,知道了我个人的判断,他自然会有一个态度。诚然陈士林不是目击者,但他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介入了那个大院的生活,他至少会有一种感受,比如二少爷是不是那种风流倜傥的公子,大少爷是否高深莫测暗揣杀机如此等等吧。
“如果你写小说,将来发表的时候,我建议把人物的名字都改一改。”他说。
“你是怕我伤害了谁?”我说,“这个我会处理的。”
“不是担心这个。”他变得有些忧郁,“我总觉得,叶家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你以为是怎样的?”
“你别又套我的话。”他拿出香烟点上就抽,“叶家,怎么说呢,又平静又复杂,我说不好。这是真话。你说叶之秋和唐月霜有关系,我看不是这么回事。当然我也没有什么凭证。我随叶之秋回来后,唐月霜常领我到窑上玩,待我很好。这女人是很高雅的,脾气有点躁,虽说是大地方人,可与乡下人打得也火热。叶念慈死后,她是注意同二位少爷的距离的,没听到什么闲话。有一次,她晚上叫起来,说是看见鬼了。大家都跑进她屋里,大少爷还提着枪,并没见到什么。以后一个时期,她就让我睡到她那儿。要是这女人有什么名堂,又何必在身边安一副耳目呢?我那时懂事了,男女的事是知道的……”
“你对叶之秋的印象怎么样?还有叶千帆。”我说,“上次你说,你上船的那天夜里,二少爷去了岸上。后来船娘也不见了。”
“是那样的,这又怎么了?”
“你还说,你看见他偷偷捏了一下她的手,她似乎还骂了他。”
“对,我想你要是遇见一位漂亮的媳妇,没准儿你也会这么做。”他回答得非常从容。他咳嗽两声,抽痰,叭的一下吐到窗外,然后继续说:“我娘在的时候,我问过她,从前是不是还有别的相好?娘就笑了,她说姑娘家就像一朵花,身边蝴蝶儿飞来飞去是常有的事。不过男人想吃豆腐就不能怕烫嘴。这种汉子就很稀罕。我娘是很烈的。”
我笑了笑。这个陈士林真是很会说话。不过我觉得这种心理也很正常。人的感情往往会把简单的事弄复杂,又可以把复杂的事处理得简单。我不打算就这个问题逼下去。我问陈士林,找我是不是有事?
“那女人请你吃饭。”他说。
“你是说秦乡长?”我说,“就免了吧,你替我说说,谢谢了。”
“我看还是去吧。”他说,“人家好歹是个乡长,你得顾一下面子。”
我还是不想去。我知道这餐饭一吃,秦贞便会给我派活。
陈士林把我从椅上拽起来:“你不是想调查郑海吗?她舅舅可是郑海的老战友!”
我一惊:“她舅舅是谁?”
陈士林说:“糙坯子的大恩人,行署专员林重远。”
林重远我是知道的。在那次有关党史资料整理的座谈会上,我们认识了。他实际上是一个副专员,分管农业和乡镇企业。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很有学识。不过面相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要衰老一些,至少是花甲开外。也许是这个原因,他始终戴着一副精致的变色眼镜。他的口音很怪,你没法分辨出他是哪儿人。他说自己是南腔北调,工作调动又很频繁。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到这个地区任职才八个月,这之前他在大西南那边工作。由于他的干练,加以资历的优厚,工作的局面很快打开并且颇有起色,在不长的时间里林重远的威信日益提高。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新来的专员而不是副专员。
造成这种错觉的另一个原因,是林重远与郑海的关系。在我接触的有关人士中,一般都是把自己看作郑海的部下的,唯有林重远以“战友”称谓。显然,这个词的分量很重。但是在那次会议上,他并未做权威性的发言。我记得他是最后一个到会的——他的会太多,不容易错开,只能兼顾。他的到来使会议的规格得到提高,同时也活跃了气氛。在听完主持人有关会议前期情况的汇报后,他清清嗓子,开始发言。他的口才相当好,措辞准确,富有文采,而且透露出他的知识渊博。我特别记住了他顺手拈来的阿诺尔德·汤因比的一句名言——“历史学家在社会里生活和工作,其职责一般只说明这些社会的思想,而不是纠正这些思想”。他说,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也应该这样。因此,他希望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回忆、整理、研究郑海的事迹上,扬其精神,勉励后人,不要只纠缠细枝末节,因小失大。这种语气给人的感觉实际上含有战友与首长的双重身份。以致原定的有关负责人总结性发言也临时取消了。主持人说,林专员的指示很重要,要认真贯彻。会议提前半天结束。
对这样一位颇具儒将风度的领导,我是敬佩的。利用午饭后的空隙,我找到了他。我向他表明自己对郑海的兴趣,也说了有可能撰写一部文学性作品的设想。他的兴致也很高,说是“值得一写的”。接着他侃侃而谈,跳跃性很大。透过变色镜我仍能感受出他的眉宇间显示着对峥嵘岁月的追思之情。我对郑海的面貌印象便是由此获得的。另外就是,他说抗日战争时期,郑海主要从事地下工作;真正组织武装力量同顽固派周旋,是抗战胜利后,一直坚持到大军渡江。我问他是何时认识郑海的。他不假思索地说是一九四四年秋。他又说大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组织上的安排,他进了军政大学当教员,从此与郑海分手,但“通过几封信”。至于郑海的死,除了表示遗憾与悲痛,他一无所知。同时他也不否认郑海的死因有可疑之处。但他说:“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们对任何事情的判断,要用科学的头脑,不可感情用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深谈。他说下午还要赶往省城出席另一个会议。在握手的时候,林重远表示以后可找机会再谈,并欢迎我去他家中做客。我说想去罐子窑走一走,也许当地的老人能回忆些什么。他扶了扶眼镜,说:“如果有什么困难,可直接找当地政府,无论是县镇还是区乡。就说是我介绍下去的。”然后,他再一次同我握手,上了一辆灰色的轿车。
我这次来罐子窑,原想事先给林重远通个电话。后来一想,觉得不太合适,惊动的层次太高,也不利于我的调查。但我实在没有料到,秦贞竟是林重远的外甥女!看来,我要享受这餐筵席,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了。
中国人的客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往往少一支烟会把一个人得罪,多一杯酒能使一个人腿软。人与人在吞云吐雾杯来盏去之间进行交流或者交易。即使是一个机器人,我想也是不会拒绝热情的。眼下这位秦乡长的忙忙碌碌,便让我很过意不去。热情消融了她留给我的无知与浅薄的印象,更有趣的是,我对这位女同志产生了敬重之感,尽管只是一瞬。我觉得,秦贞并非像陈士林所讲的那样蠢。她不笨,甚至是比较精明的。她不属于那种小事马虎大事不糊涂的女人。应该说,她对生活的关键部位——无论巨细,都把握得很有水平。就拿这餐饭来说,依她的职位随便拉到哪家馆子都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她不这么干。她让司务长按要求去采购新鲜的原料,吩咐厨师把这些洗好切好,然后她亲自上灶掌勺,说是烧几道家乡风味的菜肴让我尝尝。这些菜全摆到她个人的房间里(她的家安在县城,像许多区乡干部一样,她一般是周末回家看看,下星期一早晨赶来),使你觉得是在她家里做客,你怎能不感到亲切?
她的烹调技术我以为不错。菜很对我的胃口,也就是说,我吃了不少。我是从不喝白酒的,她就让我喝了两杯红葡萄酒和一杯啤酒。陪客仅陈士林一位,他喝白酒。秦贞只喝了一杯白酒,以后便是始终陪我喝甜酒。实际上,她的酒量很大,陈士林不说我也能感觉出来。在整个喝酒过程中,她不谈工作,也不向我暗示什么,只说一些带有恭维性质的话,说我年轻有为呀,认识一个作家很荣幸呀,倒还真顺耳。奇怪的是陈士林一语不发,只顾喝酒,居然把一瓶酒喝去了三分之二,若不是秦贞将酒瓶一把夺过去,他肯定能喝光。
“够了,”秦贞说,“你别又给我惹事!”
陈士林眯着眼笑了笑:“那就留着我回头喝。”
秦贞瞪了他一眼,同时踩了一下他的脚。可她没想到,这一脚踩在我的鞋上。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慢慢将桌下的脚收回。
秦贞一面收拾一面说:“看你那脸色,像鬼一样的。总有一天酒会送了你的命!”
陈士林把香烟在桌面上笃了几下,依旧笑着说:“酒是送不了男人命的……”
“行了行了。”秦贞不耐烦地制止道,“你回去吧。明天把这个月的生产情况给我报来。”
陈士林懒懒地站起身,划开双手打了个哈欠,用京剧里的叫板喊道:“苦哇……”就离开了,出门时对我挤了挤眼,也不知是什么意思。
等门关上后,秦贞给我泡了一杯很香很漂亮的茶。“你来一趟不容易呀,”她有点疲倦地说,“工作进展得怎么样?还顺利吗?”
“也谈不上什么工作。”我说,“搞我们这一行的,需要常下来走走看看。这地方我很喜欢,以后我还会来的。”
“那太好了。希望你对我们的工作多指导。”
“秦乡长你别客气。”
“你就喊我秦大姐吧。”
“那好,秦大姐。我会给你添麻烦的。”
“这么说就见外了。有啥要求,尽管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
“我这次来,”我喝了口茶,说,“原是想了解有关郑海的情况……”
“郑海?你是不是想写他的传记?”
“这还谈不上。不过我想了解他。”
“这方面的情况,你应该去采访一下我舅舅。他们是老战友。”
“我同林专员有过接触。他给我提供了一些情况。以后我还会去拜访他的。”我稍停了一下,又说:“我想秦大姐也许知道点什么,比方从你母亲那儿……”
“我母亲不知道这些。”她把头发朝后拢拢,“她一直在北方工作。”
“那么你舅舅……”
“其实,林重远不是我的舅舅。”她笑了笑说,“他是我母亲在军政干校的同事,处得很好,喊我母亲叫大姐。所以,我们就称他叫舅舅,他们家的孩子叫我母亲作姑姑。从小就这么叫下来了。”
“这倒蛮有趣的。”
她给我添水,往下说:“小时候,他一来,我们就缠着要讲故事。他就说郑海,什么送情报呀,杀汉奸呀,伏击呀,突围呀,可神了!我们就问后来呢,后来怎么样?那个郑海死了吗?他说郑海能死吗?直到我来这地方工作,才知道舅舅是骗我们的。我理解他。我想他们的感情太深了……去年,清明时节,舅舅到这儿来了。说是检查工作,实际上可以说是专程来给郑海扫墓的……”
“郑海墓?”
“墓还在,挺远的,在青云山顶上。不过损坏得很厉害。那天是我陪他去的,找了半天才找到墓址。舅舅当时流泪了,说在他任职期间一定要拨专款把墓陵重修一下,而且立碑。谁想到这桩事还挺麻烦,一直没法落实。”
“你是说经费?”
“不,经费没啥问题,我舅舅自己就能批。问题出在,应该说还是在郑海身上,谁叫他名声这么响?结果,现在都来抢了。三省都说郑海主要活动在自己的地盘上。墓址有了分歧,相持不下……”秦贞一口气说了这些,喝了口水润润嗓子,叹道:“人哪,真有意思。”
“是的,有意思。很有意思。”我说。
所谓“寻根”的文学实在是热闹了一阵子。直到累得精疲力竭,才陡然发现两手空空。作家的劳作实际上成了理论家打笔墨官司的材料。我们姑且对“寻根”不做是重振雄风或者是玩物丧志的评估。然而这种现象仍是十分有趣的:先亮出旗子,而后去做。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小说家扛着旗子行动的情形是多么的生动!
诚然我们不能肯定,文学的寻根和政治的认祖是一码子事。前者多少还是一种艺术的探索,尽管也似乎含有一丝艺术之外的目的,而后者则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实用!姓岳的一口咬定岳鹏举,姓包的死活拽住包孝肃,姓赵的也自然要认赵匡胤而绝不会去找赵高的。于是或修家谱,或筑宗祠,以种种善良手段把自己与有用的先人扣在一起,一并万古流芳。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个千古留下骂名的孙殿英实在是太愚蠢了。
——作家手记
像往常一样,大少爷叶千帆闻鸡即起,在院子里练习剑术,然后再去河边遛马。这剑原是一对的,谓之青霜与白雪。父亲在时,每日晨昏父子便进行对练。父执青霜,子持白雪。寒光交错,犹如二龙争珠。父亲的剑法是极好的,抽带提格劈截洗撩,无所不精,真可谓身与剑合、剑与神凝。他不是父亲的对手。如今“青霜”已逝,“白雪”空留。但是,在父亲的棺木即将合上的一霎,他改变了主意。他把属于自己的“白雪”留在父亲的腋下,带回了“青霜”。
这个早晨在叶千帆眼中是猩红色的。他倚在老槐树下,看着曙光一层一层地漫开,这才开始舞剑。他隐约感觉到手中这柄青霜剑的分量沉重了。当寒光掠起,他识出了猩红色。他暗自惊诧。但他没有停,相反,他加快了节奏。他看到剑的光影像一团飞腾的风火轮,呼啸着,然后他蓦地从这呼啸声中听到了一声清脆的枪响,他的手腕麻了一下,“当啷”——青霜剑落到一块青石上。他清楚这是个错觉。昨夜他失眠了,疲劳现在才真正从身体上显露出来。他拾起剑,用食指和中指试了一下冰凉的锋刃,坐到同样冰凉的石凳上。
大少爷,你用茶。莲子走过来,把蓝花盖碗放在圆形的石桌上。
叶千帆没有吱声,还在仔细试着锋刃。
莲子把剑拿过来,装进鞘,准备送回大少爷的屋子。这时候叶千帆说:
就挂在树上。
她不明白大少爷的意思,但也没问。等她把剑挂好,叶千帆又说:
那孩子醒了吗?
还睡着。
可说梦话?
半夜说,现在睡沉了。
梦里说些什么?
他说……他一直乱说。
说什么?
说……说他怕手指头。他说他没吃人。
叶千帆用碗盖将茶叶撩开,呷了一口热茶。
大少爷,还有事吗?莲子说。
叶千帆把茶盖上,说:叫醒那孩子,让他给我牵马!
莲子正欲离开,忽然自楼上一个窗户飞来了唐月霜的声音:
莲子,让那孩子到我这儿来。
叶千帆并没有回头,对莲子摆摆手,然后去马厩牵来大白马。莲子从自己屋里搬出马鞍,装在马背上,又把马鞭递给大少爷。
楼上唐月霜又说:大少爷,过会儿到我房里来一下。
叶千帆默默点点头,翻身上马,两腿一夹,白马一声长嘶小跑着出了院门,向河边奔去。此刻太阳业已升起,然而长水仍是青灰色的。水面上有一层薄薄的乳色的水汽,由于昨夜后来刮起了大风,两岸的芦花纷落在水上,像雪一样随水东去。白马沿着河边悠悠前行,不时停下来吃饱含露水的青草。叶千帆在马背上沉思着。他还在想刚才莲子说的那孩子奇怪的梦呓。手指头?他觉得害怕手指头是很可笑的,同这个孩子的来路一样不可思议。这个小东西为何要拽住叶家的船?真是偶然?他的脸色倏然阴沉下来。他想他可能了解了那个幼稚而荒唐的梦境:自以为吃下的不是人肉,但吐出来的是人的手指头。孩子受骗了。突然,他脑子里像被电流击了一下,晕眩以致使他差点儿从马背上滑落。难道果真存在着一种感应?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头!他仿佛于这弥漫的晨雾里看见了父亲临终前艰难竖起的两根手指头……
白马一声长嘶拽断了他恐怖的思绪。他勒住缰。接着他吃了一惊——
河的那边,叶之秋正冷峻地注视着他。
艾宾浩斯在其著名的心理学著作《记忆》的第七章的开始,就宣布:“所有的观念,如果听其自然,都会逐渐遗忘。”他认为:“只有经过有意识的艰苦的努力才能想起它们,还常是只能想起一部分。除了确有一些特殊的例外,再过了更长的时间,连一部分也就想不起来了。”但是,他继之又指出:“这些被遗忘的片段,有时又突然出现在心中,特别是在梦中,并且具有很多的细节和很大的鲜明性;很难看出来,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在间隔的时间内它们又如何隐蔽得那样好。”
这份历史上关于记忆的第一份实验研究报告对以上现象的分析,援引了亚里士多德、海尔巴特以及路德三派的观点。艾宾浩斯认为这些解释虽有不同,但并不完全相互排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心理的印象在其强度和巩固度上不能同实际生活中的知觉相比,但在知觉完全或部分地消失的场合,表象的优越性就是无限的了。早先的表象被后来的表象所重叠与掩盖,因此早先的表象便难以得到重现。但是,如果有意外的有利的环境条件,就能把掩盖物揭开,使从前的表象重现——不管经过多么久的时间,仍不失其原初的面貌以及存在的鲜明性。然而在海尔巴特及其支持者的学说里,我注意到一个新的概念——晦暗——的引入。这一派认为:较旧的观念是被新的观念压制而沉没。随着时间的消逝,它们内在的清晰性和意识的强度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伤,观念间的联结和连贯的观念也将逐渐变弱,以致分化,重新组合,变得晦暗。如果这种倾向得到一定的支持与加强,使压制着的观念同样受到压制,便会使被遗忘了的观念重获新生。不过,路德不同意遗忘只是一般的晦暗化过程。他在著名的《形而上学》中指出:“对于一件复杂事物的观念在我们的记忆中变得不明确了,并不是因为它还是完整的,各部分都存在的,只是好像被意识的微弱光芒所照耀;而是因为它变得不完整了,它的有些部分完全丢失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尚存的那些部分之间的确切的联结,一般说来,也消失了,只有在思想上可以想到它们之间从前是有过某种的结合;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想到这样或那样的联结都是同样可能的,而不能做最后决定。这个范围的大小就决定这个有关的观念的确切程度。”
——作家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