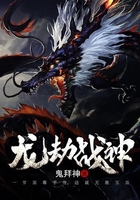关桃学生意的洋布店叫协隆绸布店。十四岁的关桃做了学徒,开心得不得了。店在吉祥街上。吉祥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街,一头与法大马路交叉,另一头接洋泾浜路。上海有名的大马路大多是东西走向的,从东边的黄浦江边向着西面迤逦延伸。法大马路和洋泾浜路就是有名的大马路。
吉祥街上没有行道树,几根电线木头树立在路两边。吉祥街有二十几只门面,每只店面都从二楼挑出店招幌子伸到马路当中,店招上大书各家业务,风一吹,五颜六色,飘来荡去,闹猛,撩人。路的一侧,南洋药房、周吉甫医师、协隆绸布店、欧阳齿科、汪裕泰茶庄、乾昌吉林人参一路过去;另外一边,白金龙香烟仁丹、新乐唱机、荣昌祥、天丰绸缎局、王顺泰号呢绒、光华眼镜、汪泊其牙医一路过来。吉祥街上的房子不中不西,一间一间挤着,中间山墙合用。房子大多两层,黛瓦,一楼粉墙,二楼窗口下的外墙用木板子罩起来,挂着招牌。这里的住家没抽水马桶,灶披间里暗龌龊,用煤球炉烧饭炒菜。不做店铺的沿街底楼住家都有两道门,一道板门,一道半高的栅栏门。板门往里开,栅栏门往外开,天气暖和的日子,住家会把板门打开通风。
走出吉祥街就是不一样的景象。法大马路比吉祥街宽阔许多,两边房子是钢筋水泥的,或者清水砖砌起来的,每一间都是精心设计。法大马路与吉祥街交叉的路角子上有一栋四层楼房,墙壁上有几块很大的广告牌子,最上头的是先施白兰霜,下面是美丽牌香烟,美丽牌香烟牌子边上,勋爵牌香烟广告做得更大,像是两家人家有意别苗头。法大马路两边有宽阔的人行道,各种装潢富丽的商店,梧桐树整齐排列,两边的树枝在天上勾搭起来,很暧昧的样子,天暖和起来时树叶由稀疏变得茂密,把整条路遮盖得严严实实不叫行人感觉一丝太阳的毒辣。法大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电车“当当”响着,载着各种体面人去往城市的四面八方。
协隆绸布店两开间门面,一半是玻璃窗,一半是玻璃门。玻璃窗和玻璃门外头还有门板。每天早起,学徒要卸下门板准备开门。附近有好几家做布料生意的店家,竞争激烈。做布料生意要学很多东西,从棉布到呢绒,从真丝到织锦,各种花色,各种门幅,长长短短好几百样。但法兰西外滩和十六铺码头的人流,电车“当当”轧过马路的声音,样样挑拨着年轻关桃的神经,痒兮兮的,好像他天生就应该属于这座城市。
关桃上过学,又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出两年,店里的账就好像长在他脑子里了,老板不知道的布料他知道藏在哪个角落,老板没想到要补库存的东西,他早早提醒要进货了。有一次关炳生去看儿子,老板很客气,特意拉了炳生到老正兴饭店吃中饭,流露出喜欢这小家伙的意思,关炳生很开心,吃多了一点酒,有些酒水糊涂,脚高脚低回龙华,过一座石桥时居然掉进了河浜里,还好天暖和,没出什么大事。
账房吴先生的算盘在关桃刚来时噼里啪啦很是爽脆,但两年后却显得有一些迟疑,倒不是年纪大了,而是小家伙脑子太好,打起算盘飞快不说,脑子比算盘更快,好像账房先生没什么大用场了。刚开始吴先生还会有意无意为难关桃,但后来吴先生不敢了,怕关桃和师弟顺礼联起手来捉弄他。这顺礼不知道为什么唯关桃马首是瞻,有时师傅讲话也会先去看一眼关桃的面孔。
关桃快满师那一年嘴唇上已经长出胡子,喉结大了,公鸭嗓慢慢变得浑厚,身体一下窜得老高。
有一日老板让关桃去十六铺接一批从外地发过来的货。走出吉祥街来到法大马路,一部电车开到站头上,车站上一个女孩和关桃四目相对,只一眼,又羞怯地把眼神移开。关桃觉得那女孩好美,像他孃孃一样美。电车正上下客,关桃再要多看一眼时,女孩不见了。车门口的人拥作一团,关桃的眼睛搜寻着,却看见一个小偷正从一个女孩的衣裳袋里夹出皮夹子,来不及多想,他大叫一声:“有小偷!”那个和关桃一样年纪的小偷吓了一跳,皮夹子落在了地上。
关桃不知道,小偷多半是有一两个帮手的。扒手除了练三只手的基本功之外,对偷窃时的各种情况是有应对办法的。好比现在,关桃身边已经围拢了三个人,都是和关桃差不多年纪的男孩。关桃还没觉察到危险,一只拳头已经打了过来。关桃的脸被夯了一拳,后背被踢了一脚。车上车下的人都叫起来,但没人敢上来帮关桃忙。
关桃猝不及防,差一点跌倒。他只注意到小偷回过头来恶狠狠看他的眼神,并没想到小偷还有帮手。如果一个人,关桃从小是打架的好手,被逼急了,一般不会输,但现在关桃面对至少三个对手,他有几年没打过架了,对结果没把握。好在关桃没跌倒,站稳了。身后不远处正好是墙壁,他退了两步,确保后背不暴露给对手。被打中的脸有些胀痛,他的野性被激醒了,头微微地低了下来,柔和的眼睛变得锐利,凶光毕露,两个拳头收拢捏紧,鼻息里却像有一缕馨香飘过,使他的头脑反而变得安静,所有人的动作在眼睛里好像都慢了下来。他看清楚有三个对手,没其他人围上来了。外围站着的是刚刚惊叫的人,他们自动地往后退了一点,好像要给这几个人留出格斗场。
“噢哟,小赤佬管闲事要吃苦头了!”
“是额呀,巡捕房也拿三只手没办法的,睁只眼闭只眼,这种人不好惹的呀!”
“三吃一,作孽了。”
关桃盘算着形势,决定不纠缠,因为没有人帮他,纠缠在一起对他可能不利,他还要去做老板交待的事情,他要打开一个缺口迅速脱身。他已经来不及想那个好看的小姑娘这件事情了。
趁着三个人还没紧紧围拢,关桃向着左边最靠近他的那个人用左手打了过去。这应该是打他一拳的那个人。打架要以牙还牙,你打到了我,我不还回去,声势上就输了。如果那个人躲闪,关桃要看清楚他躲闪的方向,然后右拳打上去。如果那个人不躲,也出拳向他打过来,他就向外躲闪,拔腿就跑。
那个人本能地向关桃的右手方向躲闪了一下,关桃看得清楚,挥出右拳狠狠朝着那人的左脸打上去。关桃看到自己的拳头打在了对方的脸上,对方的面颊肌肉和牙齿撞击后,嘴巴张了开来,眼神痛苦,身体倒了下去,血和着唾液从嘴巴里飞出来。他想从这个缺口跑出去,快速脱离这个是非之地,但一只袖子被另外一个人拉到了,“嘶啦”一声脱了线,他只得借势转过身来,一只脚踢了过去,不偏不倚地踢到了那人的裆里,迫使那个人松了手。关桃的动作一气呵成,快到不可思议,他看准机会快速脱身,听到后面有人“沓沓沓”追着他跑,他听出来那只是一个人的脚步声,索性停下,返身向追赶他的人冲了过去,那人见状,回头狂奔逃跑。确信对手不再追来时,关桃转进一条弄堂,一条弯曲的弄堂,其中又有一些更小的支弄。他停止奔跑,透着粗气,惊魂未定地环顾四周,想起了自己的正事。他从弄堂里穿出去到另外一条大马路上,看到了几个巡捕,正威严地举着长棍子向不听从命令的黄包车夫打过去,黄包车夫躲得飞快。关桃想,巡捕也只会欺负老实人。一个巡捕向他看过来,关桃想起自己衣衫不整,怕被他拦住了问话,耽搁时间,连忙转了头向十六铺走去。
到十六铺时,送货人因为等得太久忙其他事情去了。关桃有些慌,老板还等着他拿回布料后再分送出去呢。
关桃回到店里时老板已经等了很久。平常去接点货来回也就不到一个钟头,今天却花了两个多钟头,脸上有一只青皮蛋,衣裳脱了线,很明显是在外头打了架回来的。这是两年多来的头一次。
老板黑着脸问关桃:“小赤佬跑到啥地方打相打去啦?”
关桃只好如实将在车站上看到小偷的经过讲了一遍。
“你要死啊,小赤佬,这种人你也好惹的呀?!你晓得这些人是啥人?他们有没有跟着你?小赤佬你是要害死我?天还没热就热昏了。他们要是在这里寻到你,我这个生意还做不做?你爷娘养你这么大,要是没命了,寻我要人,我啥地方寻去?”
这一天老板不让关桃吃夜饭,要罚这个惹是生非的徒弟,让他记得上海滩的闲事是不好管的。
关桃和师弟顺礼住在绸布店铺面上的阁楼里。阁楼矮,勉强能让已经慢慢长大成人的关桃低着头走路。这屋子住起来没有乡下自己家里舒服,夏天很闷热。除了忙店里的事情,学徒还要帮着老板娘做家务。抱小囡,倒夜壶,扫地拖地板,无一不是学徒的工作。但关桃喜欢这样的日子,倒也不觉得苦。师弟徐顺礼身材不高,圆脸上长着一副柔和的眉眼,小小的鼻子,嘴唇薄,嘴巴还小,几如樱桃小嘴,薄薄扁扁的头发,人畜无害的样子。关桃有时想,这应该是个女孩子的长相。顺礼刚来时有些口吃,着急时口吃更加明显。他的脸上总挂着讨好的笑容,但这笑容却不是由于学生意的训练形成的。有时候这笑容里还有一点畏葸,吓丝丝,好像要随时躲避天上落下来的灾祸一般。关桃不喜欢师弟缩头缩脑的样子,但也理解他,觉着他作孽,因为师弟是小老婆生养的。
这天夜里七八点钟,关桃躺在床上饿得实在难过,师弟还在追问:“师哥,你真的一个人对打了三个人吗?”
“不是我对打,是他们三个打我。”
“但是你打倒了两个人对吗?你,你怎么会这么厉害!”
是啊,他怎么会这么厉害?关桃自己也不明白,他本来只是想快点脱身的。他一拳打在了那个人的脸上,看清楚那个人表情的每一个细小变化,由气势汹汹到痛苦不堪。大概是他真的被激怒了,他平常根本打不出那么快的拳头。
“师哥,你学过拳脚?”
“没有。”
“我才不信,没、没练过拳脚,一个人可以打三个人?”
“真没有。唉,你怎么讲话又口吃,又要被师傅骂了。大概是今朝那三个人都没力气吧。哎,顺礼,不要饭泡粥了,有没有吃的东西,我现在没力气了。”
“没呀,师哥,一、一点也没。”
“你为啥不藏一点呢?亏得我平常对你那么好!”
顺礼委屈地讲:“师哥我是对你好、好的呀,可我真没有吃、吃的。”
关桃听得吃力,不过知道顺礼没骗他。顺礼的口吃其实已经好多了,刚来时更加严重。现在讲话已经基本顺了,但今晚表现得不大好。做学徒的没多余钞票买零食的,但关桃真的很饿。他叹了一口气,想,今夜只能饿肚皮了。
扶梯上传来声音,好像有人在爬上来。关桃和顺礼都觉得奇怪,这个时候不大会有人来的。一个女孩的脑袋从地板上冒了出来,是秀珍,邱老板的大女儿。秀珍在地板上放了一碗饭,饭上面盖了些菜。放下饭碗,秀珍就下去了。关桃忙过去端起碗来,“稀里哗啦”狼吞虎咽般吃了下去。
此后几天关桃老走神,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大约他还在想前几天打架的事情,有些后怕。关桃两眼定定地看着前头,有时对耳边的声音无动于衷。终于有一日,老板在他头上敲了一只毛栗子,他猛颤了一下,茫然地看着老板。
“小赤佬想啥心事啊?叫侬几遍听不见的?”邱老板既是老板,也是关桃的师傅。
邱明远不高不矮,圆圆的额角头很亮,圆得好像用圆规画出来的。额角头上是逐渐稀疏的头发,脸有些瘦,对客人常挂着巴结的笑,眼珠子很灵活,会看三四。他穿着长衫,一把软尺像是长在脖子上的。但他的眼睛比软尺更厉害,一眼就可以量出客人的深浅。
邱明远一家就住在店面楼上。邱老板祖籍福建,是第三代上海人。上海移民潮很早就已开始,1853年,小刀会起事,其中大部分会众都是来自福建、广东的流民。历朝历代,流民最狠!流民就是流氓无产阶级,革命最彻底。本地人很少无产阶级。江南文化中,无产者是脱底棺材,被认为是好吃懒做的结果。小刀会会旗一举,本地人跟着倒霉,老上海城中街道俱焚,死人无数。那一次的灾难加上太平天国发起的数次战事,使得江南富庶之地空村百里,很多人为了保命不得不逃进租界。邱老板的父亲是福建人,但不是小刀会的,也在那个时候进了租界。小老百姓,活着是最要紧的。现在的邱明远对生活还是相当满意的,连吉祥街这个名字也让他满意。
邱明远有两个女儿,大的秀珍,小的秀琳。福建有些地方重男轻女,女人做重活,男人享福。邱老板生在上海,但没想过要让女儿多读些书。邱老板和太太为了要一个儿子相当用功,但十年没出成绩。关桃刚做学徒,邱太太肚子就开始大起来,几个月后,三十六岁的老板有了儿子,邱家终于有后!
关桃不到一年就满师了。他浓密的头发覆盖在柔和瘦削的脸上,由于不常洗头又不好好梳,像个鸟窝一样扣在脑袋上,左额头的头螺已经看不出了,眼珠子乌溜溜的,透着聪颖。学生意之后,他的脸上也常会漾着一份笑意,使略有些岁数的女顾客格外喜欢他。
秀珍比关桃小一岁多,齐肩的头发常梳出两条辫子来,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秀珍皮肤白里透红,五官单个看有些平淡,但搭配起来妩媚俏丽。她脸上曲线起伏不算大,但身体曲线日渐明显。秀珍穿着上海家常的女孩衣裳整天忙来忙去,平日帮着娘缝缝补补,给一家人和伙计学徒洗菜做饭。春日里草长莺飞,豆蔻年华,少女心忽忽萌动。
一日黄昏,店铺关门,关桃将一排门板上好,到楼上准备吃饭。秀珍手里抱着弟弟,忽听得邱太太叫,让去厨房端菜,秀珍就喊关桃过去接手弟弟。关桃伸出手去接,左手在下,右手略近秀珍胸口。忽然间,四目相对,面颊“腾”一下红艳似火。关桃的右手不小心抵到了秀珍胸脯,那个隆起并且酥软的胸口。关桃感到莫名的心跳和窒息,身上好像烤火一样热。
吃夜饭时两个人都很沉默,也不看对方。关桃快快往嘴巴里塞饭,着急吃完的样子。老板照例小酌着,觉察出了异样,骂一句:“吃那么快做啥,强盗抢啊?”
关桃不响,放慢了吃饭速度,看了一眼秀珍,秀珍也略抬眼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吃饭,脸泛起红晕。
关桃回到阁楼上,躺在床上。阁楼上低矮的小窗对着马路,传来喧闹的市声。关桃听见远处刹车的吱吱声和江面上老牛般的汽笛声。他忽然觉得身上盖着的棉被太厚了,热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想起隆起的胸口,透气也有些粗了,一股热力向着周身扩散,他感觉下身异样的紧。这是一股来自自己身体的蛮力,不断地向外扩张,膨胀,弄得他好像要炸开来了一样。
秀珍也没睡着,十四五岁的少女,多少懂一点男女之事。她翻了一个身,一只脚踢到了睡在里床的妹妹。瞌睡懞憧里,秀琳咕哝了一句:阿姐,你又踢我……
第二天清早,街上老早就响起粪车嘎吱嘎吱的声音。平常日子,此刻的关桃是不会醒的。春天,又是发育的年纪,男孩子总也睡不醒。但这一天关桃早早醒了,外头的每一样声音都钻进他的耳朵里,让他没办法再睡。他听见不远处的老盛丰卸下了门板,捅开了炉子,揉面摔面的声音传过来,他好像看见那里的伙计阿勇只穿了一件贴身短衣,额头汗津津的;油条下锅冒起一片油泡,味道发散开来,钻到关桃的鼻子里。他饿了。
天光熹微,小窗户开始亮起来时,关桃听着顺礼均匀的鼻息声又睡着了。但来不及做梦就该起床了。关桃得早起下到店堂里打扫整理店面,做一天营业的准备,然后卸下门板,一块一块迭好,开门迎接客人。
邱太太的声音传下来,照例是骂秀珍懒,不知道早点起来帮爷娘做事情,不知道照顾好弟弟。这时候邱太太应该在厨房间准备早饭,睡眼惺忪,头发乱蓬蓬,斜襟衣裳上头的几粒盘钮没扣好。其实早饭就是隔夜泡饭,酱瓜咸菜,没多少可做的,但邱太太每天早上都觉得不大开心,大概是为没有舒心睡懒觉的命运觉得委屈,也或许这个年纪的女人总会变得唠叨。邱太太18岁嫁给邱明远,本来以为嫁给老板就可以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没想到这些年来每天总有那么多的鸡零狗碎等着她。她那张原本还算好看的脸在镜子里逐渐走了样,好像精心化好的妆容糊掉了,手背上细碎的皱纹像微风拂过的湖面上的水波纹般触目惊心。半世人过去,好日子遥遥无期。
远处法国兵营里传来军号声,上海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