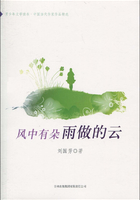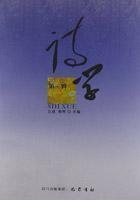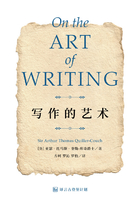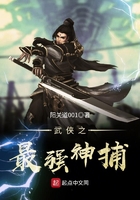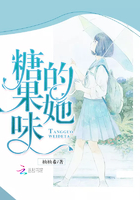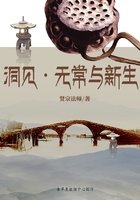春节期间停工,与父亲闲聊,说起乡下老屋门前,当年的人声鼎沸早已不见,掐指一算,人口已三去其二矣。
惊觉,当我在江南重建庭院时,西北老家正在消失。
其实,杭州西部农村,也曾经或正在经历这样的人口变迁,只不过,相比中国西部,更有生机罢了。
由于一百五十年前“长毛”的屠戮,杭州西部形成了多宗移民杂居的格局,方言、风俗、地理均不同。那支“本地人住城镇,安庆人住高山,平阳人住丘陵,河南人住田畈,苏北人在港滩”的歌谣,至今仍是现实,一个明证。
虽已一百五十年过去,但各自的界限仍然清晰无比。各宗保持着各自的社交圈子和当初占有的资源,虽历经改造,仍封闭而有效。大宗仍然势重,小宗不得不小心翼翼。
一个例证是,施工期间,总有各种工作以外的意外发生,比如沟通问题或安全问题。后来有人跟我讲,工地上,最好是一个本地人配一个外地人。有外地人在,本地人使不了坏;有本地人在,沟通很顺畅,毕竟工地上有许多当地的地理、地质条件的特殊情况,外地人确实弄不明白。
除了以各种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隔绝之外,官方对民间社会引导的伤害,亦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在宋代,包括定都杭州的南宋王朝,都禁止官员向皇帝告密,以防止政治伦理的败坏,包括一些私人书信,绝不能成为呈堂证供。
但在某个时间点,为了大规模地监控人民的行为和观点,告密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手段。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人们之间没有互信,信任关系无从建立,每个人都孤立于世。现在这种境况虽然好一些了,但由于官方追求快速得到一些政绩,告密仍然被派上用场。比如哪户人家多盖了半个平方米的房子,谁家地界出去了一米半米之类,皆被民众用来报复仇家,而官家对这种告密行为大开绿灯,甚至鼓励有加。
相比城市,农村的社交平台单一,人际矛盾更多,远不似城市那么简单,哪怕兄弟之间,也有彼此举报不得安生的。
有些事情的做法,就不得不依着乡间成法,而不是按照事情本来该有的样子去实施。
正如三十年前,我家老院,是村里不批建,一些友善的村民帮着父亲一夜间拾掇起来的。慢慢地,一间房就变成了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正好是两户人家中间的一块菜地。北方盖房不似南方讲究,两家直接共享一堵土夯墙,屋就建起来了。
可能有人会奇怪,两家何以能共享同一堵墙?陕甘一大怪,房子半边盖。因为缺少大型木料,陕甘人民盖房不用人字梁,而是直接用椽檩搭个半坡,这样可以省去人字梁。于是,两间背靠背的房子,中间是同一堵墙,外面看去,倒似是一大间人字梁的房子。
但实际上,单从外表也能马上看出来那不是一间大房子。秦地盖房,极讲规制,比如客房,那是正面的主屋,屋顶得有兽脊,比院内其他所有房子要高出一头。其次是厨房,一般是西厢房,这屋一般也住人,尤其是冬天,必须烧炕,否则冷得待不住。北方的炕,既是热炕,又兼壁炉的功能。再次是小夫妻的卧室,一般是东厢房;如果孩子多,厢房可能会隔成几间。南边是院门,一般不盖房。
房子如此密实,只因人口稠密,出路又几乎没有。除了个别当兵离村的,大家都在这里打庄盖房,娶妻生子,世代轮回。
本来,我也要经历这样的人生,却阴差阳错成了出局者。其时,我家贫困,父亲看中的人家不愿将姑娘许配与我订娃娃亲,既然老大无婚约,老二也没法有,于是弟弟也无婚约。兄弟俩攀婆娘没攀上,一门光棍儿指日可待。
这在乡下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几乎所有的女孩都有了婚约,不早点下手,就意味着光棍儿一生。
除了订婚约,还得打庄,一个儿子得打一处新庄,这件事基本上会耗尽一个父亲一生的心血。待老大成婚分到新庄,一大家子就像蜜蜂那样分家另过,老头儿老太太就跟着小儿子在老庄终老。
印象中,村里日子稍微好过的那几年,新庄一个接着一个,大家都搬离了老庄,住到相对偏远但宽敞的地方。
我高考那年,考完后在家收麦子等待放榜。挑麦子过山湾时,被山坡撞翻到沟底,心中恼怒,干脆躺在沟底看无边的阳光。路过的村民看了,直叹“这娃要是考不上大学,可怎么办”。
还好,我们兄弟和村里的一帮小伙伴,都先后离开了这山村,不再有打庄娶妻的压力。
岂料,不用在老家打庄了,跑到江南却依然逃不过盖房修院的命运,可见人生都有定数,若有喜乐躲不过,若有苦恼也躲不过。
在我们离村的这二十年里,似乎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除了进城工作的,还有长辈随孩子进城的,又有人因孩子在外地读书而进城租房居住,又有人在外地打工。总之,曾经最热闹的我们那一片,现在连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都不到了。有些院墙已然坍塌,有些院墙,如我家的,几乎倾倒,我们也懒得去修理。
春节期间,同在外地工作回家过年的小学同学换了一张头像,是一条两边长满尺长野草的小道,问是哪里,却道是门前。
要知道,二十年前,这条道是官道,重车、牛马碾压之下,根本不可能有草,现如今,这道上仅容一车通过,哪还有官道的气派?只怕是赶羊道还差不多。
那日弟弟说,他老了就回村去种地,美气得很。我说:“看这样子,到你退休的时候,估计地里的路都不通了。”结果母亲接过话去:“现在已经不通了。”父亲说,他前一年回老家,沿原来的小道骑车进城,结果那路早已荒废,衣服被两旁的野草刮了个乌漆墨黑。
我说,若如此,弟弟到时只能坐直升机进村了。
弟弟说他要种果树,要种土豆。母亲说,到时候真种了,那也是给野兽种的,因为别人家可能都不种了。我小时候还见过狐狸从地里逃走,夜里经常驱赶偷鸡的黄鼠狼,地头经常有黄鼠狼的窝;父亲小时候还见过狼。但后来,就连黄鼠狼都见不到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荒山都被开垦种植。
而这些年来,撂荒的耕地越来越多,原先保护起来不让猎取的野兔已经泛滥成灾。以前总是没长大就被砍来当柴烧的沙棘,现在长得树一般粗了。小时候,我经常在沙棘林里捉蚂蚱,若是沙棘树一般粗,想来人根本进不去,更说不定里面有蛇。想想,那村一定会被野兽一步步侵占,重新成为它们的领地。
有个数据说,到了2050年,中国人口只剩下10亿,然后继续减少。不论是总人口减少,还是中国人口的城市化速度加快,农村的废弃是一定会发生的,只是不知道是哪些村。有预测说,50%的人住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以及武汉、重庆和成都等长江流域的大都市,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口流出,就不会有任何疑问。想想刚刚过去的2015年,连哈尔滨这样的城市人口都下降了,我们村的人口下降,难道不是早就该发生的吗?
而且,人口流出一旦成为趋势,就会加速。村里的建筑本来就是泥屋,要是一年无人居住、维修,马上就会被雨水泡出毛病;再加上无人居住的房子多半会成为让人看着心里发毛的“鬼屋”,这村子里的人只会加速流失。
人没了,地图上还会有这个村子吗?
另一方面,我又赶紧在各种地图上标注了“止溪”这个地名,让它赶紧生长起来。
一个地方的存废,果真是因了人的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