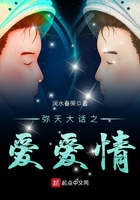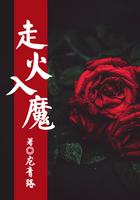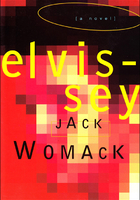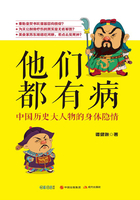母亲说,我自小人长得矮,老远根本看不到,但只要隔着河湾听到歌声,便知我放学归家。
那并非因为爱好唱歌,只是半夜走在荒梁上,十几里内没有一个人影,有的只是树影憧憧,有时似兽猛扑,有时似鬼嚎叫。大人点着烟一路走去,或者咳嗽着口水吐一路,因为鬼怕烟火和口水。小孩无法,只好唱歌壮胆,企图吓退猛兽和野鬼;唱着唱着,就长大了,学会了低声细语说话,唯恐惊着天上人。
2015年,大学入学20周年的纪念,班上一半男女,齐集西子湖畔,重温那时歌谣。猛地发现,我仍然没学会那些歌。因为长在乡下,除了《十五的月亮》《渴望》之类的主题曲,真正会唱的没几首。进城后,不论班上集体活动还是KTV里,除了国歌拿得出手,其他都没几首可以唱的。倒是在凤凰古城的酒吧里,趁着酒兴,吼过几嗓子花儿,斗败过另一伙唱歌的酒徒,双方尽欢而散。
那花儿的词,也是老掉牙的,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想花下求爱,便是“姑娘十七我十八,姑娘缠我我缠她,缠得姑娘不回家”;若是分手发狠,便唱“你是牡丹开败了,开得再好不爱了”。唱毕,必是朋友未笑我先笑。
所以说,我不是一个会讲故事和笑话的人,最常见的是,故事或笑话讲完了,别人还在等下文。大家都不笑,大家都很尴尬。现在脸皮厚了,懂得添油加醋,对自己冷嘲热讽,便能增添一些氛围,倒也其乐融融。
就如“我是个多么腼腆的人啊”这句话,特别贴心的朋友当然知道这是发自肺腑的真话,酒肉朋友便当是我自嘲,于是又一阵欢笑。世间人物,便这样真真假假,自我安慰,一日新似一日。
可那歌终究是不会唱,每到这个时节,窘得不行。
直到在村外找到了一块地方,我发现,这里蛮适合“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的我。
这首歌,是我读小学时,读初中的邻居陈福全哼哼时我听会的。
其实这个地方是意外之处并不情愿的收获。
那是一个夏天,双溪的气温比城里要低2至6摄氏度,躺在岳父二十多年前建成的老宅里,一边说话一边叹气,就像夏天散热的狗那样,毕竟是夏天。家长突然说,老头儿想翻盖老房子了。以前一直在翻新,我以没有结婚为由拖着,现在看来是拖不过去了。村里除了那几家有特殊情况的,都建了新房,我们现在连孩子也生了,不建说不过去了。
我说,中国农民就这个德行:好不容易积攒一点财富,建个房子,再欠一屁股债;花20年还债,再赚点钱,回来拆了老房盖新房,周而复始,无个穷尽。若老头儿是这般心思,何不动员他做点其他物事?
家长说,这房子卫生间都漏水了,要么大修,要么重修,这么差的格局,成本差不了太多,莫若重修。
我悠悠地看了一眼亲爱的家长大人,口出莲花:我们终究是不常住这里,所有花在这里的钱,都会沉淀成不用的死钱,明显我们不是这么有钱的主。那么,如果真的要盖,就得考虑后续,比如说,我们盖的房子要有共享价值,可以成为朋友们喜欢的乡下一方田园,否则,我们投下去的钱,可能会成为一堆建筑垃圾。
书生迂腐,总有宏阔之见,这话也不例外。但那时,正当我在家长心目中形象最为高大之时,对于此议,家长毫不迟疑地表示了支持。
什么样的房子是有共享价值的?要么靠山要么靠水,当然最好两者兼顾。若两不靠,则几同废地。且一定要有无遮拦的视线,否则,又是建筑丛中挨挨挤挤,环境甚至不如城里。
作为一个好热闹的人,单纯盖一座房子,像本地村民那样生活在这里,第一,不现实,毕竟要工作;第二,无趣。我的一处乡下院落,一定要有高朋相聚,才有住在乡下的味道。
虽然不喜欢孔子那老头儿,但他的某些情态也可心。《论语?先进篇》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我才不管他是五六人还是六七人,反正是一帮人,沂水里冲个凉澡,舞雩台上吹个凉风,冷歌几首“咏而归”,可也。
要实现孔子的世俗生活,得有一高台可乘风,得有一水池可游泳,得有一处可读书,方称得上浴、风、咏。
这三样,便是我建屋的标配。
突然想起来,家长是杭州悠泳俱乐部的成员。她的游泳水平相当之高,无论横渡钱塘江还是游海岛,都不在话下。她向往城市生活,若在乡下有这么一个泳池,会否也是她的“泳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