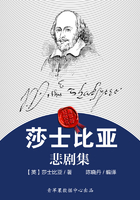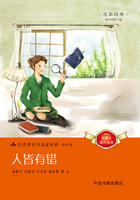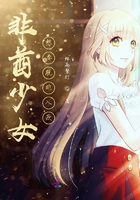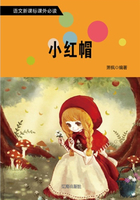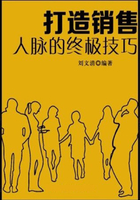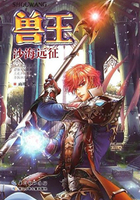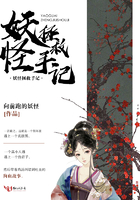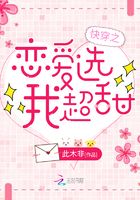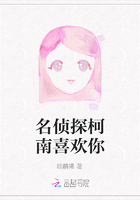走在杭州的街头,平素色彩单一的林荫道,一到秋季,姹紫嫣红,在秋雨中滴着水珠,透着一股腐败和艳丽交织的气息。
若是在西北乡下,此时当是一幅秋风秋雨萧瑟的场景。土豆已经入窖,荞麦已经开花,蜜蜂在赶着采最后一茬花蜜。
我就在这样的现实与梦境中,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尤其是当互联网技术给了我们支撑时,这种时空交错就更为直接。故乡的小曲、故乡的劳作,曾经令人那么恐惧和厌烦,此刻却因“乡愁”而显得温情脉脉。
《射雕英雄传》中,大金王爷抢了牛家村的惜弱,怕她思念故乡,将整个牛家村的旧居搬了来。
所有远行的人,怕是都在复制一个故乡。文成公主进藏,带了种子、工匠,无非也是要在拉萨仿制一个大唐长安,甚至一应器物、作派、腔调,无一不是在模仿。
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在这半个多世纪的狂飙突进后,突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有些事,一地鸡毛;有些事,会心一笑;有些事,且让它去;有些事,不能忘怀。
当我们出行既远,怀旧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罔顾的事实。但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怀旧是一种病。
既然“怀”,那一定是温馨美好的。就像一个失去了母亲或者远离母亲的人,哪怕是母亲的责骂和殴打,也是一种不能忘却的爱。有些故乡被美化,有些乡村被美化,有些人情被美化,只记优点而忽略不如意,除了意象,想象与实际完全脱离,还美其名曰“礼失求诸野”。
这些年,多少人在表达自己的乡愁,我将他们通通归结于两种境况:要么在城市生活得不易导致了对母体的依恋,要么吃饱喝足了找点情怀。尤其是后者,往往带着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心态,一面俯视乡村,一面怀念已然干涸的小溪——以前下河摸鱼、力逮泥鳅黄鳝,何等欢乐。
正如我弟弟讲,他要回到故乡去养多少头牛、种多少苹果树之类,每讲到这些,我总免不了与他争辩。父亲就来说我:“他也就是一说,让他回他也不会回去。”
有多少人,心口不一若此?只怕也不少。
让我对这个问题重新认识的,是在台湾。而且台湾年轻人的“还乡团”,远远脱出了乡愁的范畴,而将乡土文化留存、乡村建设、人的现代化等结合起来,为乡村文明复兴提供解决方案,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不是为着满足自己内心的那点小情怀,而是本着文化自觉,企图挽救族群、区域文化,为在千篇一律的全球化、城市化过程中,保留文化的多样性,是在做一件社会事业。
我在台湾游历时,也曾短暂地了解过这一活动。台湾年轻人最初的动力来自台湾少数族裔大学生对其民族文化传统的中断的担忧,直接的促进力,则是工业化已经完成的经济背景。在这一背景下,进城潮流渐渐变换为下乡潮流: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大学毕业生,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开始关注文化建设;而受城市困扰的市民,也开始寻找乡下的“世外桃源”。在这两者的合力推动下,台湾的乡建具有了文化和经济的双重身份,即有文化特色的乡村建设和旅游业。
但他们的问题与我们的同在:村里都是老人,连服务员和演员都招不齐。如遇重大活动,得联系周边同族村寨合力举办。农村的空心化,是两岸共同的困境。
若在大陆,已经支离破碎的村庄和人口,如原子一般存在,如何能组织起来?
一个地方是否兴盛,要看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如何;一个行业是否兴盛,要看对优秀年轻男性的吸引力如何。以此观之,大陆的乡建,也许才要起步,却马上碰到了人口断崖式下滑。
现在的问题是,城市都缺乏年轻劳动力了,农村还要夺一把?
都说现在中国的光棍儿多,可为什么剩女还那么多?原因很简单,城市对农村、南方对北方、东部对西部形成了资源的虹吸,女性资源都被强者占有了,所以,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乡村的弱势,也许会因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反动”而形成资源上的逆向流动,但大的方向绝不会改变。
这也是我一直不敢对城乡之间的优劣下断语的原因。
五六年前,在《南风窗》工作的朋友陈统奎,在其故乡海南发起了社区营建活动,也称为大学生回乡行动,得到了海南省委书记的支持,这个活动同样肇因于台湾的大学生乡建运动。
陈统奎在海口市火山口地质公园里面盖了几间房子,和弟弟一同操持。我去看时,他与其他“海南仔”无异,拖鞋走得吧嗒吧嗒。但他家里有一间房,是图书馆,我有幸把自己的《阳坡泉下》塞进了其中一面书架。
走在园子里,他能讲出每一棵树的来历,以及它们好玩的地方。哪怕是一口破铁锅,也能派上用场,且有一段祖辈的故事。
我没有他这样的雄心壮志,却有这样的爱好。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工作在城市,却一直没有与农村断绝联系,这使得在我身上“怀旧”的特征并不明显,若去乡下,是相对理性的选择,既不时髦,也不老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