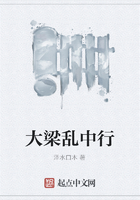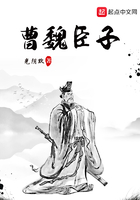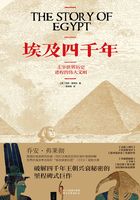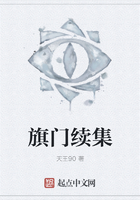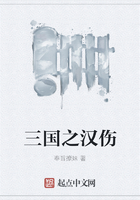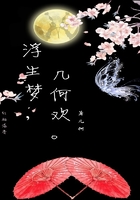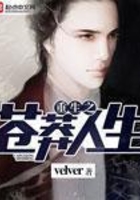江南三月,草长莺飞,杂花生树,满街都是踏春看景的行人。坊市的商铺经过一番油漆粉刷,已全然看不出曾遭火焚的迹象,六部衙门也在重新起造,据说将造得更高更大。乱世已去,盛世重来,丽日和风之下,往日的种种幸与不幸都被人抛诸于脑后,一切似乎再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从闽地传来的消息说,招降李得天和黄世英的事如今进行得很顺利,但是让吴王烦心的是讨逆将军方镇川没有对骠骑将军许成龙采取行动。
早在上皇禅位,新帝登基之时,许成龙便拒不上表称贺,朝廷欲征召骠骑将军班师,许成龙也置若罔闻,不肯奉诏而行。许成龙此举不仅是小看了吴王,而且也是在羞辱朝廷和少帝,唐觉之奏告皇帝,欲将许成龙列入了周氏逆臣一党,削官夺爵,并要天下军民共讨之。
但是年少的皇帝这时候却发话说,许将军不是对社稷有功的功臣么?当年朕曾听上皇念及此人的名字,所以印象颇深,既然许成龙是功臣,怎么又会是逆臣呢?
唐觉之因此格外费劲的向皇帝解释,功臣未必就不会成为逆臣!持功而骄,功高震主的事史上常有,许成龙不肯奉皇上的诏书班师回朝,那就是不奉王命,自然是心怀鬼胎,包藏祸心,另有图谋,因此才要天下军民共讨之。
年少的皇帝仍觉得难以理解,反驳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承运六年时,舅父身在南阳前线督师,因战事紧,也是不肯奉诏回援京师,群臣因此交章弹劾,上皇便引此句为舅父开脱。许将军或许另有原因,舅父不可轻易讨伐。
唐觉之于是放弃了说服皇帝的想法,频频下令方镇川进击许成龙,只是方镇川为保存自家实力,轻易不肯用兵。方镇川是怕二虎相争,让吴王从中得利,所以姑且听从其父之言,按兵不动,划疆自守,不理会相国唐觉之的一再课督。
唐觉之也料到方镇川心里必有他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手下的那些士卒现在是他所能依仗的本钱,他当然不想早早花光这些本钱,对此曾经身为将帅的唐觉之自己也是深有体会,因而只能暂时容忍,方氏父子再有异志,所求不过节度封疆而已,而许成龙和周如喜对太上皇始终心怀忠诚,其心志并不在于节镇封疆,这让唐觉之如何敢掉以轻心?
吴王转而将希望寄于为匪作寇的李得天和黄世英两人,他从京师派出使者,几经辗转周折方才与李得天、黄世英有所接洽,吴王谕示他们,只要能够取得许成龙的项上人头,便可以封侯伯,为节镇,自王一方。
有了吴王这样的谕示,李得天与黄世英都颇为振奋,闽地的情形因此而益发显得奇怪。本来骠骑将军许成龙已经停止了对李黄两股山匪的进剿,但是李黄两股山匪如今却蠢蠢欲动,想要抢先吃掉官军,成为替朝廷立功建勋的反正之臣。
而许成龙身在闽地,心念京师,去冬今春在南都发生的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牵扯了许将军的注意力,面对当前变幻莫测的时局,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做出自己的抉择。
谁也不能否认许成龙对于上皇的那颗赤胆忠心,只是上皇已经禅位,满朝文武如今都效忠于新帝,他不知道上皇现在还需不需要他的这一腔忠诚?
监军周如喜当然是喋喋不休的企图说服许将军挥师京门,诛除奸佞,拥上皇复辟。只是许成龙觉得率军回师京门,诛除国贼奸佞,单单凭一己之力,似乎并无太大的把握,但假如中原的方大用和齐鲁的唐会之都有此心的话,许成龙自己自然不会落于人后。为此,许成龙曾经去信给方镇川,约他相与勤王,然而方镇川并无回复。
许成龙有些失望,既然不能兼济天下,看来唯有独善其身了,这对于一心想报答上皇知遇之恩的许成龙而言,抉择无疑是艰难和痛苦的。也因此许成龙不眠不休的思索了好几天,以至于整个嘴边一圈都是内火烧出来的燎泡。南乡郡主心疼夫君,劝他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地既不能留,不妨往他处去,若日后有机缘,再图报国恩,岂能引颈受戮,妄为他人所笑。
听了这话,许成龙终于豁然开朗,力不如人,当先求自保,然而闽地地窄,难以施展,放眼望惟有南进一途,或能存身。许成龙于是率士卒由八闽挺入南粤,一路攻城拨寨,势如破竹,只十来日,便攻取了岭南大郡番禺,周如喜虽然大失所望,却不能不随军南行入粤。
许成龙驻节番禺,又连续占据周边七府三州之地,所到处粤人归服,豪强俯首,心中方觉有了倚靠,这才上表于南都的朝廷,为自己以前的不恭请罪,表示愿辞右相之位,但求改任岭南节度,若皇上俯允,将谨守臣节,世镇南疆。
吴王唐觉之见到许成龙的上表,在应允其请还是下诏讨伐上拿不定主意。张成义则以为,天下由乱复治,殊为不易,岂可再起烽火?许成龙既然愿意尊奉朝廷正朔,拥戴吴王当国,吴王大人大量,不妨与他捐弃前嫌,彼此各安其命,各自保全富贵。
吴王事实上也并不敢轻举妄动,京中皇帝尚幼而上皇犹在,人心未能尽服,此时若出师征战,谁来经略江南,掌控朝廷?不如就此与许成龙握手言和,各镇一方。于是唐觉之干脆拜许成龙为岭南节度大使,允其假节开府,自置官属,岭南的租税财赋,朝廷得其四,而许成龙自留六,每年于春秋两季按时献纳呈贡既可。至于罪臣周如喜的处置,朝廷还是装模作样的做了一番文章,免其死罪,予以贬窜,谪迁为琼州司马。
安抚了许成龙,唐觉之以李得天、黄世英反正归顺为由,授李得天为漳泉镇抚使,以黄世英为南平守备,又令方镇川驻守豫章,节制八闽。
内忧消解,外事上却突生口舌。正月刚过,唐会之遣人使东胡,将南都帝位更迭之事告知也里温,希望东胡大汗速派贺使,赴南都面圣。
三月间,胡使赴京来贺,以两国先前曾经约定,东胡大汗尊江南的皇帝为兄,而自为贤弟,但东胡屈身事兄,上下对此早已不忿,如今江南的皇帝退位为太上皇,而太上皇既为皇帝之父,那么东胡大汗与江南新天子彼此当为叔侄,东胡居长为叔,江南居卑为侄……所以原先江南皇帝所馈赠我东胡大汗之礼物,今后应改称孝敬,并且孝敬之礼自当多于馈赠之物。江南若不应允,东胡兵马将倾国而至,为太上皇讨要公道。
一开始,东胡的使臣态度蛮横,寸步不让,吴王心里颇为烦恼,要江南的皇帝以子侄礼敬事东胡的大汗,真乃天大的笑话,朝廷对此自然不能松口,唐觉之因而指派张成义与胡使商谈。
张成义与胡使连谈了三天,双方各自妥协,江南的皇帝和东胡的大汗各有天命,理当相互尊崇,累世通好,所以弟兄也好,叔侄也罢,均弃而不论,当然也不须提馈赠与孝敬等语,江南的皇帝每年以银五十万,绢二十万,茶盐各五千担换取东胡大汗良马百匹,镔铁千斤,羊皮二千张……会谈毕,双方画押换文,各自欣然。
事后唐觉之告诉少帝和唐太妃,胡使虽来势汹汹,却被我三言两语驳得哑口无言、面目无光。臣明告东胡,皇上和大汗,一在南一在北,各有天命,治化万民,并行不悖,岂有尊卑长下之分?然本朝尚有太上皇在,皇上若与大汗并尊同贵,而上皇之尊更在皇帝与大汗之上,胡人不识此理,不料为臣所算计。至于银绢茶盐之物,乃是开互市通有无,并非朝廷白给,所换之良马、镔铁、羊皮皆江南所缺,借此可各得其利。
唐太妃很赞赏吴王唐觉之和太保张成义为国的忠勇辛劳,但是吴王和太保都身居高位、享受尊荣,礼无可加。唐太妃便礼下于偏庶,传下懿旨,将唐觉之的侧室林氏,封为凤阳郡夫人,张成义的侧室倪氏封为寿春郡夫人。
内政外事一切都安排周详,唐觉之把许成龙的上表和朝廷将予封授的诏书以及胡使来朝的详情细故进呈给了长庆宫的上皇。
上皇览过书奏,终于不能保持平静,这最后一点渺茫的希望也由是破灭,上皇心中未免酸涩,因此对跟在身边的王守礼说:想不到满朝文武都是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之人!
上皇的无限感慨,让王守礼唏嘘不已,这才几天的功夫,上皇眼看着又老了许多,背时常佝偻着,说话也有气没力的,闲时连书也看不下几行。
而汪皇后听说此事,两鬓的白发自然又多添了几根。但是汪皇后却没有因此消沉下去,许多年以前,她母亲曾经殷殷关照过的话,又在她心头浮现。“忍着,孩子,千万要咬着牙忍着……”忍吧,把一切全忍了,除了忍,她也没有再好的法子。
所以当陈太后携着皇孙胜来紫微殿看她的时候,汪皇后已经能够神色平和地说话:日子总得这么过下去,由洛都到南都,那么艰难不是都捱过来了……
汪皇后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分明还有泪光在一闪一动,陈太后轻轻叹了口气,拉着她的手说:凡事总得要想开,现在的情形既不是太好,也不算太坏,能捱出来就好了!
汪皇后点着头,一手却把胜儿搂在怀里。
江南佳丽地,花开四月天。
地处城南濡沫坊,日益门庭冷落鞍马稀的宁安长公主府,这天忽然来了一大帮子人,领头的老者自称是武安侯、太保张大人家的管事,因为奉了太保大人的侧室、新封的寿春郡夫人倪氏之命,特此前来迎请贵府上的二夫人姚氏过往一叙。
听得是炙手可热的武安侯张家的人,公主府的总管吃了一惊,赶紧去回禀公主与驸马,两人也同感讶异,姚璎珞除了一个姐姐嫁在京师,此外并无亲故,这位寿春郡夫人何以指明要二夫人姚璎珞前去面见?
陆怀有些不放心,亲自到厅堂上去见那管事,张府的管事笑嘻嘻地说:回禀驸马爷,敝府的倪夫人与贵府的二夫人原是在兖州时的旧相识,义结金兰,情同姐妹,贵府的姚夫人只要前往见过了我家夫人便知根由……
陆怀心中狐疑,回到内室跟公主与姚氏商量,太保张大人如今是吴王的心腹,朝廷的新贵,手握生杀予夺之权,咱家是宗亲贵戚,虽不惧他,却也没必要轻易开罪,因而主张让姚氏去见上一面。姚璎珞却有些发慌,因为听说这位张大人是个色中饿鬼,京师的夫人仕女往往宁愿绕路,也不肯从宣和坊太保府的前后门走过。
但见姚璎珞畏畏缩缩的,宁安公主便出了个主意:不妨让保义夫人陪她同去,保义夫人是朝廷命妇,太保那里怎么着总要以礼相待,另外再多派些家丁仆妇的跟着也就是了。
陆怀当下连声称妙,姚璎珞闻后也心下稍安。
为了不使张府的来人小瞧,宁安公主府上也派出了浩浩荡荡的一队仆妇随从,骑马坐轿,吆五喝六的往宣和坊去了。
宣和坊的太保府此前便是昌国公周如喜的府第,周如喜成了罪臣后,家产被朝廷抄没,府第自然也就归了太保张大人。
只是保义夫人原先并不知道这些,当她所坐的轿子被抬进张府的大门时,她先是感到吃惊,以为下人们认错了路,走错了门,待奴仆们道出原委,保义夫人先是一怔,继而一叹,忽然就明白了佛经中所说的“无常”是个什么意思。
端坐在轿子里的保义夫人现在眼睛都不用朝外面看,就知道轿子是一路抬往内宅的爱莲堂去的。京师里她平素走动得最勤的,除了禁中大内和宁安公主府,便是这韩夫人的太宰第了。想当初,她在这爱莲堂里不知陪公主和韩夫人吃过多少次茶,聊过多少回心。眼下当她再来此间,爱莲堂一如往昔的清幽雅致,门楣的两边也仍然张挂着那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联对,然而周府却变成了张宅,当家招待的主妇也由韩夫人换作了倪夫人。
除了才进张府时这些细微的感触,真正让保义夫人吃惊的其实还在后面,如果说二夫人姚璎珞是保义夫人眼中稀世罕见的美人,那么寿春郡夫人倪氏则是比二夫人姚氏还要美上三分的大美人,所以当寿春郡夫人倪氏从爱莲堂的内室袅袅颤颤的走出来时,保义夫人和二夫人姚璎珞都一齐呆住了。
“世上怎会有生得如此齐整的人物?这般的花容月貌,就是宫里的娘娘们也没一个能比得上啊!……”保义夫人看着姗姗而来的寿春郡夫人,心里尚在抒发感慨之时,她身边的二夫人姚璎珞“哎呀”一声,忽然抢身上前,抱住了倪夫人又哭又笑。
这又是保义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切就好象变戏法似的,寿春郡夫人倪氏在她面前摇身化作了姚夫人的姐姐姚琉璃。
保义夫人知道二夫人姚氏有个姐姐,听说是嫁给了济阳侯方镇川做了侧室,只是没想到,原本是济阳侯方镇川的侧室姚氏如今却成了武安侯张成义的侧夫人倪氏。
姚璎珞自然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姐姐,她呆了片刻,便揩着眼泪,破涕而笑:姐姐怎么会在这里?可知我找你找得好苦?都以为这下再也见不着姐姐了!
姚琉璃微微的皱着眉,轻轻的叹一声,道:我又能去哪里?落花随着流水,飘到哪里便是哪里……
姚璎珞见状,心里忽然涌出许多话要问,但也不敢多问,只是说:只要姐姐一切仍好,我也就放下这悬着的一颗心了。唉,我只是担心这事要是给姐夫知道了,只怕不会甘休。
姚琉璃脸色一变,喃喃的说:我已是张大人的人了,你以后少在我面前提到方家的事……
姚璎珞怔了一怔,叹息一声,说:男人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为了这瞒天过海之事,姐姐改名换姓,差点连妹妹都不认了。
姚琉璃怒道:胡说,京中就你这个妹子,我能连你都不认么?你、你道我是心甘情愿的么?京中大乱,人心惶惶,禁军抄家搜人,若换了你到那种情形中,又能怎么做?
姚璎珞叹道:姐姐今后便死心踏地跟从张大人了么?唉,倪夫人,这名字生疏得很,怎么叫都不亲切。
姚琉璃苦笑一声,淡淡地说:方家我是没脸面再回去了,不跟张大人我又能跟着谁?是跟你回公主府,还是落发去做姑子?哼哼,既然身陷绝境,总要绝处逢生,所以我从那日便成了倪氏——寿春郡夫人倪氏。我的小名不是叫做阿璃么?这倪夫人便是阿璃、便是我姚琉璃。如今,你我在此见面,认与不认,妹子递句话便是,也没什么觉得为难不为难,亲切不亲切的。
姚璎珞低头沉吟了半晌,却抬头说:阿璃是我的姐姐,倪夫人当然也是我的姐姐。
姚琉璃眼睛一红,却微笑道:我就知道我家的阿璎总是心向着我的。妹子且留在这里陪我说话,我已叫人去置办酒宴了。这位就是宫里出来的保义夫人么?今日有幸见过了。刚刚咱们姐妹见面,保义夫人只怕有些摸不着头脑吧,一时情切,便忘乎所以,慢待了夫人,夫人切莫怪罪是幸。
果然是个妙人儿,话说得面面俱到,让人听着心里舒服,保义夫人忙道:二位夫人能够姐妹相逢,妾身心里也同感欢喜,只怕有妾身在此妨碍了二位夫人互诉衷肠。
姚琉璃笑道:保义夫人真是实成人,我家阿璎自小姣惯,所以还指承夫人能够多多看顾。
保义夫人欠身道:夫人这话言重,妾身实在不大敢当。
保义夫人这一天陪着二夫人姚璎珞在张府里一直呆到天黑,这要不是公主府里有人来接,只怕还会呆得更久。
自然在回到公主府后,张太保新纳的寿春郡夫人倪氏原本是府中二夫人的姐姐、先前做过济阳侯方大人侧室的隐秘内情也被众人所知晓。
宁安公主听说了此事,临晚就寝时特意把保义夫人叫来问话。公主有着跟常人一样的好奇心,她想知道藏身在张府的这位寿春郡夫人,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她的第一个夫君济阳侯方镇川?
保义夫人歪着头,想了一想,然后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表情对公主说:依我看,人总是会念着旧情,倪夫人大概也是如此吧。不过既然改嫁了张大人,又获了朝廷的诰封,应该是不会再有二想了。
宁安公主听了这话,拧起眉头,冷笑一声:什么倪夫人?朝三暮四的贱人!和那个张成义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哼哼,还寿春郡夫人哩,朝廷的诰封岂能及于侧室偏妻?现在果然是礼崩乐坏,伦常颠倒,一切都越来越不按规矩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