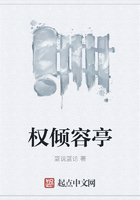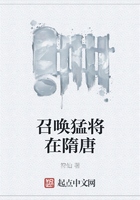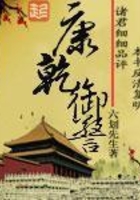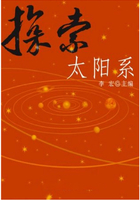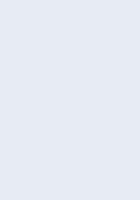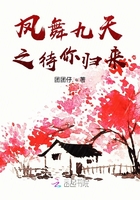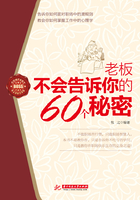四月的朝堂因为有了清明节这个慎终追远的日子而显得格外的喧嚣吵闹。因为年少的皇上要到太庙向列祖列宗致祭,礼部和太常寺将预先安排好的种种仪轨,在朝堂上一一奏告。
这本是惯常的朝会,待有司所奏事毕,群臣即散朝各归衙署,然而就在吴王挥手准备宣布散朝之际,终于有人站出来公开向吴王诘问发难。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以忠直闻名天下的谏议大夫尚质。
尚大人这回抓住了皇上要到太庙行礼致祭的问题,在朝堂上侃侃大谈人子之孝。尚质说:既然陛下倡言孝道,将诣太庙祭奠列祖列宗,却何以不亲率群臣往长庆宫朝见太皇太后和太上皇帝?
这话题朝堂上一直列为禁忌,上下都是讳莫如深,不想尚大人今日拿忠义孝道出来说事,这自然有好戏可看,朝堂上一时鸦雀无声,群臣在讶异之余,却不能不佩服谏议大夫尚质的忠勇与胆大。
对此吴王张口结舌、吱唔以对,但是尚质大人的倔脾气这回又发作了起来,他不依不饶非要吴王给个答复:皇上年幼,全赖丞相掌摄国政,此事我若不问丞相又能问谁?慎终追远,所以民德归厚,臣料二圣亦倚门而待皇上,若两宫和谐,上下同心,这天下也才能太平长久。
唐觉之只得托辞说:上皇潜心静养,不欲多问外事,故免内外朝贺之仪,此亦是太皇太后的慈谕懿旨,故臣等不得不遵尔。
尚质便说:上皇固然潜心静养,不问外事,皇上和诸臣却不能不尽臣子的忠孝礼仪,事亲以孝,事上以忠。丞相身为百官之长,尤当有督率倡导之责。
唐觉之铁青了脸,动怒道:太皇太后及二圣既然早有圣谕明旨,尚大人此言,若非是想离间父子君臣?此乃皇上家事,太皇太后及太上二圣尚且不问,身为臣子者又何敢置喙?
尚质却也不惧,抗声道:既食君禄,当忠君事,身为谏议大夫,不能规谏君王过失,不能议人所不敢议,尸位素餐,人云亦云,其与傀儡摆设何异?尚某不才,既然充任此官,自不敢不尽心尽职!
沉沉一潭死水终于为一粒石子所打动,从而泛起微微的波澜,朝堂上这时也如水波般有了些微的荡漾,臣子们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小声附议,太师陆正己和太傅陈从圣也都频频点头,以示赞许。
吴王唐觉之的脸色这时候已经由青变黑,太保张成义见势不妙,赶紧居中转圜,长声说道:丞相请息怒,尚大人亦请回班归位,臣以为,上皇虽免内外朝贺,然人子臣下之礼自不能不遵,此事须待皇上祭告太庙之后,召集群臣共议大礼,早日订下这赴阙朝觐之仪,则伦理亲情,尽得其宜。
陆太师、陈太傅都点头称是:太保此言甚是,国朝以忠孝礼仪教化万民,皇上尊崇太皇太后及太上二圣,礼当率先垂范,日后当集众成议,早日订此大礼。
唐觉之强捺住性子道:姑从此言,待皇上清明祭祖之后,着礼部详加研议,颁定大礼。
原以为尚质大人问完了此事,便会罢休,岂料尚大人这回有备而来,一事问完,跟着再问数事:少师方大用、节度大使唐会之还有骠骑将军许成龙如今各拥重兵,节镇在外,请问丞相,难道忘记了前唐五代的藩镇之害?至于闽地之匪,朝廷变剿为抚,然而匪性无常,若再有反复,丞相将何以制之?再者去年京中大乱,禁军二营起而生事,不听王命,火焚宫室,罪孽滔天,丞相非但不予惩处,反而加官进爵,列位公卿?此三事,尚某难解疑虑,不得不问之于丞相。
唐觉之终于安坐不住,站起身喝叱:尚大人,你话太多了!唐某进位相邦,受命摄政,天下事无非攘外与安内,所以凡事自有一番权衡安排,且都禀呈于皇上和娘娘,得其恩谕首肯,若是不论大小轻重,凡事皆付诸公议,未免众口嘈杂,使天机尽泄。不过今日尚大人动问,不妨在此细释一二,以解众人之疑。方少师和唐节度受上皇所命镇抚一方,皇上即位,自然仍沿其旧;闽地之匪既已弃械投诚,朝廷当允其改过自新,以尽其用;禁军二营,已蒙上皇恩赦,且有拥戴今上之功,所以加官进爵,以为酬报。尚大人虽蒙恩起复,到底任事不久,心中存疑,在所难免。今日唐某特在此讲明,日后不得再有事端……诸位若无余事,还请各回衙署。
这一日的大朝会,年少的皇帝端坐于丹墀之上,虽然始终未发一言,不过在退朝之后,坐在大辇上的皇帝还是对身边的内侍随从们说道:尚大夫居然一点也不怕吴王……
内侍尚没有说话,受命为帝师的弘文馆大学士陈广陵在一旁说:尚大夫为人忠直,实为陛下的良臣,臣不敢不言贺。
少帝歪着头说:前唐五代的藩镇之害,朕曾听先生论史时讲过,尚大人是说本朝也有这样的事么?
陈广陵道: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尚大人乃是提醒皇上不可掉以轻心,以至于养虎成患,由尚大人此言便可见其人忠直,其心耿耿。
少帝皱了皱眉,又说:依尚大人之言,莫非要朕亲往长庆宫朝觐二圣?陈先生,朕、朕可否不去长庆宫?
陈广陵一怔,忙道:陛下何以出此言?陛下为上皇之子,何以不朝上皇?此大礼也,亦是为人处事的忠敬孝义之道!倘若陛下不能身先垂范,将何以教化臣民百姓?
少帝低着头,若有所思的说:朕听人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皇,所以王不见王,王若见王,必生灾殃,此前圣母娘娘即如此说,舅父亦如此说,宫中都是如此说。
陈广陵摇头道:父子君臣,忠孝礼仪,天地之纲常,圣贤所教导,推己及人,由上而下,乃万世之法宪,虽万乘之尊,亦当遵从就范,陛下岂可不前往朝觐?那些闲言碎语,无源无本、无根无据,陛下读书知礼,岂可不遵古圣先贤之教而听信谣传……
陈广陵对这位天子门生,不厌其烦,谆谆施教,然而年少的皇帝对此似乎还是有些犹豫。皇帝如天中之日,本应该是至高无上的,象圣母娘娘、太夫人、吴王还有宫里的近侍随从都是这么说的,皇帝该不该去觐见上皇呢?觐见或者可以免除,真要想有所致意的话,也可派钦使前往长庆宫觐见二圣,钦使奉旨成行也就等于皇帝亲临……
但是少帝看着陈广陵敛色正容的样子,这些话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去。
皇上率群臣赴长庆宫朝觐上皇之事,朝堂上当时虽然未有定论,但在清明节之前,项城郡王唐会之之妻、由南安郡夫人晋封为安国夫人的陈氏也给唐觉之出了一道难题。
安国夫人当面向吴王提出要进宫探望女儿和外孙,她并用唐觉之曾经说过的“弟妇乃自家人,去留随意,当无拘束”的话来堵他自己的嘴。
唐觉之无奈,只得允其所请,但是却又让唐太妃指派身边的近侍宫婢寸步不离的跟从在安国夫人左右,所以即使陈夫人和唐媛想借此传递消息,应该也无机会。
安国夫人和唐媛的见面是在原来的太子东宫青华宫,母女俩已有半年未能相见,这回甫一见面,便都流泪痛哭不已,只是有永寿宫派来的侍者在一旁盯着,到底十分的不自在,这心里想说的话母女俩始终也说不出口。
但是借着跟母亲见面的机会,太子妃唐媛也提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马上就是清明了,她希望能够前往佑圣寺为已故的慈圣皇太后和元献皇太子追荐冥福。
对于女儿的要求,安国夫人自然满口答应下来,这天一出宫门,陈夫人便前往吴王的府第想要他亲口应允。
可惜吴王不在府内,吴王的侧室、新受封为凤阳郡夫人的林氏将陈夫人请入内堂用茶。这林氏虽是侧室,却受命主掌府内的一应事体,身份几乎等同于正室。这都是因为当初唐觉之随驾巡狩,自家的正头娘子和老太师都留在洛都府上,不想靖王篡权夺位,朝廷随后播迁于金陵,一对夫妻从此南北睽隔,各自一方。此后靖逆再窜于长安,将洛上旧家都一体挟裹而去,如今竟连原配夫人的生死也渺茫难知,所以这林氏虽甚得宠爱,却因正室虚悬,便始终未能立为继室。
而陈夫人跟唐觉之先前的正室娘子之间的妯娌关系并不合洽,皆因唐觉之这一房是长房嫡宗,而唐会之这一支却是疏宗弱枝,身份不同,地位不等,所以两家疏于走动并不亲善,直到圣上到了南都,唐会之因护驾有功,入值中枢,且任为左相,两家才开始彼此接近。侧夫人林氏也是唐觉之在南都时才纳入唐门的,所以在陈夫人面前,便不敢妄自尊大,陈夫人却也不因此看低了林氏,加上两府庆贺吊问,时相往来,妯娌之间常能见面,自然关系就越益亲近。
陈夫人在唐府只略略的坐了片刻,便把自家的来意跟林氏说了,当然一说起女儿守寡,陈夫人便会伤心落泪,林氏少不得要宽解安慰,陈夫人求托的事,当下就满口应承下来。
陈夫人趁热打铁的说:要是王爷不准,少不得还来府上叨扰!王爷一日不准,我便坐等一日,总要得他个准信才回。
林氏说:这也未必是什么难事,夫人且放心,等王爷回来我自言之。
待到吴王归府,林氏果然将陈夫人的来意详说了一通,自然也相帮着说了一些好话。
唐觉之低头未语,唐媛是自己的侄女,安国夫人是自己的弟妇,说来也是自家人,如今清明在即,唐媛要为亡故的先夫追荐冥福,唐觉之似无不允之理,不过对于长庆宫的任何举动,唐觉之总是心存戒备,当下便要叫人往太保府去请张大人。
林氏劝他说:王爷总摄国事,何须事事皆问旁人?太子妃不过是替先太后、故太子做场法事而已,王爷到时候多派些人手随行护持也就是了,难道还怕她有什么异动不成?
唐觉之道:凡事总要小心一点为好。况且这其中的干系,你妇人家懂得什么?
林氏失笑道:王爷既这么说,莫非打算关她一辈子?依妾身看,凡事见好就收,该紧时紧,该松时松,这才是正道。再说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宜王早薨,这一死百了的,想争也争不得,太子妃弱质女流,子尚年幼,又能对王爷有多大妨碍?王爷便放一放又有何妨。王爷要是执意不允,陈夫人那儿怕是不肯依,从此天天上门厮缠,王爷既打不得又骂不得,到时候吃不消受不住了,自然还是会应允的不是?
林氏一阵紧言慢语终于打消唐觉之心中的顾虑,不过吴王仍是关照了林氏的兄弟执金吾林重阳,要他随从护持,以备万一。
因着母亲陈夫人的大力协助,在锁闭于宫中五六个月后,元献太子的未亡人唐媛终于获准前往佑圣寺行香奠祭。唐媛此番能够成行,这对于长庆宫的老老小小来说,是相当值得重视的一桩大事。
太皇太后和汪皇后都召太子妃来问,这婆媳祖孙三代如今可是一条心,都在想是不是长庆宫的门禁将因此有所松动。
只是一番猜测和臆想之后,还是不太搞得清外面的情形,尤其是听了唐媛说起其母陈夫人进宫之事。“那日母亲进宫,左右才不过二三个时辰,而永寿宫派来的人始终如影随行,连如厕都跟前跟后的假献殷勤,想趁机问个事,说句话,实在是万难……”
陈太后有些恨恨的说:陈夫人既然得已进宫,长公主、公主何以不能进宫?
汪皇后却叹息道:外锁内闭,消息难通,究竟如何,或许还得再看一看……你此番出宫,到底要多留些心眼,但有机会便设法打探,外面情形如何?朝臣竟置上皇而不顾不问么……
唐媛说:儿臣明白母后的意思,自会想方设法打听明白……
陈太后也关照说:凡事当见机而行,不可使外间生疑!这回既能出宫,总归是件好事,务要小心谨慎。
元献太子妃的鸾驾由春华门驶出的时候,天街上早禁了一切行人,车驾所过处且还设有步障,使内外皆不得互视,而金吾卫随行的校尉们更是密密层层,全然一付如临大敌的模样。
佑圣寺里一切仪轨均作好预备,太子妃一旦驾至,钟鼓齐鸣,梵音呐唱,其声盈盈于耳,寺里的尼僧也都鱼贯成列,出来参拜贵人,自然如磕拜佛祖菩萨一般恭敬无二。
奠祭之暇,住持尼师面谒太子妃,请其稍事休憩,用些茶点。当下唐媛移玉驾,迈莲步,前往佑圣寺后院的精舍。
然而住持尼师将唐媛引至门前,自己却未进去,只是躬身说道:娘娘请入内休憩,容贫尼暂先告退。
精舍里早有人在,是一女尼,光头缁衣,容颜清瘦,见唐媛至,便合掌问讯:施主别来可好,贫尼元妙这厢有礼了!
唐媛先还不识,过后方醒过神来,一时惊愕莫明,指着她道:你、你、你被逐出宫,原来竟是在这里?
元献太子妃唐媛万没料到自己会在佑圣寺的这间净室里见到逊位出家,落发为尼的元妙上师周鸾。
周鸾苦笑道:贫尼遁入空门,存身于此方净土,亦可谓不幸中之万幸。
唐媛定了定神,方才叹道:你现下可好?用度可缺?这里的尼师可敢亏待渺视?母后还时常提起你哩!唉,现在回想当年,竟如隔世似的——皇上内禅了,太子爷也去了,这争来争去,还有什么可争的?你我都是苦人儿罢了……
周鸾神情悲伤,凄然说道:过去的事,贫尼再不敢想起,贫尼只日日诵经,夜夜参禅,除为慈圣皇太后,为太子爷祈求冥福,更为太皇太后、太上二圣及诸贵人祝祷千秋万寿!至于贫尼,阅经观世,但觉天道无常,悲苦相继,此生既然无望,但求来世不入轮回……
唐媛默默看她一眼,低声道:你来见我,当有话说,此刻无人,不妨直言。
周鸾脸色一黯,忽然流泪道:贫尼听说胜儿亦随施主来至寺中,故而敢请一见。贫尼身在空门,诸事皆可抛却,惟有母子连心,睡梦里都盼望能见得一面……
唐媛叹息道:此事不难,你先等着,待我叫人抱胜儿过来,让你母子见上一面。
唐媛当即传尼师,吩咐与她,须臾奶娘将孩子抱来,待入房见了周鸾,自然也是一呆,双膝一软便要跪拜,周鸾连忙止之,只将孩子抱住细看,这孩子却有些不识娘亲,身子后仰,手推脚蹬,周鸾益发伤心,泪流满脸,呜呜咽咽,那奶娘也是悲泣不能成声。
见过了自己的孩子,周鸾拭泪说道:这孩子父亡母出,尚望储妃娘娘能够多多看顾。贫尼既入空门,内心早不存他想,只望吾儿能平平安安,无病无灾,便是心愿。
唐媛道:胜儿和捷儿吾当一般看待,上师当不必萦怀挂念。
唐媛说完这话,便叫奶娘抱走孩子,当净室里单剩二人时,唐媛却道:今日见到上师,实在拜天所赐,快拿纸笔过来,吾当留书于父母,他日你若得便,可转呈于吾母。
周鸾忙道:贫尼居这里,远离宫禁,却也清净,纸笔案上皆有,贫尼早有预备……
唐媛起身将取纸笔,却又回头,皱眉说道:此事甚密,千万不可让外人知晓。
周鸾咬牙切齿地道:储妃之愿便是贫尼之愿,储妃之事亦是贫尼之事,贫尼出家,拜谁所赐?中心藏之,何日敢忘!贫尼日夜祈祷,便盼着云开雾散,日月重光!
唐媛道:吾不信你,还信何人?当下作书一封交给周鸾,周鸾自是稳妥的藏在隐秘之处。
时辰将近申刻,元献太子妃返驾还宫,执金吾林重阳事后回禀于吴王,只说一切警跸皆里外三四层卫护,所以别说是人,连鸟也飞不近太子妃的身子……
吴王赞许道:小心使得万年船,若能事事如此,方不至于忽生变乱,措手不及。
光正元年的清明节过后,朝廷终于议订了皇帝朝觐二圣的大礼,但是永寿宫的圣母娘娘以种种理由坚决不肯同意皇帝亲往长庆宫去面圣,最后乃是派出少府令李润代替皇帝前往长庆宫朝谒二圣。
而上皇觉得轻慢,也执意不见李润,汪皇后倒是命传见,可惜上皇也不许她见。上皇说:岂有此理,儿子不来,倒让外人来,何以不来?无他,无君无父、非忠非孝,所以心中愧怍!朕是上皇,难道受不得儿子前来朝参拜谒?既然权在贼手,自家做不得主,那么不来也罢!
最后收拾这僵局的仍旧是陈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当然也有不满,所以她没好气的对李润说:回去寄语皇帝和唐娘娘,皇帝不来朝见上皇和老身也就罢了,何以大长公主及长公主皆不得进宫侍亲奉孝?是谁大胆拦阻?此事皇帝和太妃若作不得主,试问天下究竟是何人作主?你替吾传话于皇帝,既然读书受教,老身到要问问,这尊尊亲亲,到底何谓尊尊亲亲?
这是长庆宫里诸多怨气的一次爆发,对此情形,李润唯唯诺诺,只能磕头,不敢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