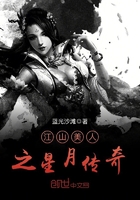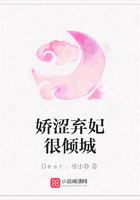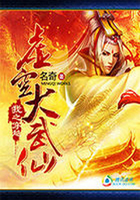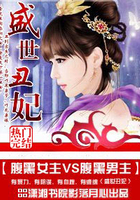谥号议定,皇帝诏告天下,朝廷便着手准备孝献帝和孝献后合葬山林的奉安大典。在献陵灵寝开工动土之际,汪皇后亲临祭享,奠酒致哀。这是她送别晟儿的最后一程,所以执意要来此巡视,此后身为逝者的长亲,出殡入葬都将不再参与。
奠酒上香,诸礼皆毕,太常寺的乐舞生舞起八佾,唱起挽歌,哀婉绵长的音调混合着燎炉里纸帛焚烧时的袅袅青烟,弥漫飞升,让人有一种恍惚迷离的感觉。
充担山陵营建大任的昌国公周如喜带着工部、礼部、钦天监、太常寺、光禄寺的一班官员,恭请皇后娘娘巡视钦天监勘定的万年吉壤玄宫所在。面对晟儿的长眠之地,神色惨淡的汪皇后木然伫立了良久,俯身时将自己佩戴的一串佛珠放置于将来安放梓宫的宝床之下。
回到专供自己起坐休憩的帷账,汪皇后心情凄恻,晟儿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难舍难忘,静坐了片刻,汪皇后从怀里拿出那个被她视若珍宝而精心收藏的锦囊,那里面装着她的晟儿早年骑马阅兵时跌折的一颗牙齿,还有晟儿郁郁而逝后,自己在盖棺装椁之前亲手剪下的一缕头发。她低头看着手中的锦囊,眼眶里蓄满了眼泪,将滴未滴,即使千般不愿,万般不舍,她也要和自己的儿子诀别了!
慢慢地,她把装着晟儿发、齿的锦囊紧紧贴在自己的面颊上,从宫里起驾便未曾开口言语的汪皇后,这时候想要说些什么,只是双唇颤抖,喉头哽咽,万语千言,难以表述。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是晟儿出阁受学后背熟的一句话,汪皇后犹记得当年他站在自己面前,摇头晃脑,大声诵读的样子,当汪皇后头脑里回想着这些场景的时候,结蓄多时的眼泪顿时如雨点飞溅,她攥着锦囊的手,此刻也移到胸口,让它贴靠着自己的心房。
“我的儿呀……你就这么丢下娘了……”汪皇后暗哑着嗓子喃喃而言,一语未毕,皇后以手掩面,痛痛快快地大哭起来,强忍了三年的悲伤今朝终于渲泻而出。
哭过之后,揩干眼泪,心情略微平复的汪皇后叫御府监何知书传旨起驾。在登上凤舆之际,皇后忍不住回头,凝望了最后一眼,虽然曾经的创伤还会时不时地隐隐作痛,但已不再撕心裂肺般的让人难受。她能够为故去的晟儿所做的事情,如今都圆圆满满地做到了,想必晟儿的在天之灵在享受祭祀供奉的时候,亦当晗首而微笑。
孝献帝的两个儿子,皇孙捷和皇孙胜也跟随他们的祖母前来叩拜祭奠,这让幽居在春华宫的太子继妃非常的不安。说来京师有资格随从皇后娘娘陪祭的内外命妇们,就只有两个人没有到场。一个是卧床告病的燕国长公主,另一个便是故太子的未亡人萧媛。
萧媛现在的身份有些不尴不尬,宫里虽仍视她为太子继妃,但跟孝献帝似乎又隔断了关系,象这次皇后娘娘兴师动众地前往巡视山陵玄宫,只派人来接走了皇孙胜儿,却对自己是否偕子同行只字未提。
萧媛明白,自从家族诛灭,亲朋故友,云离星散,身为唐氏的余孽,没被牵连治罪已属万幸,即使被众人厌憎嫌弃,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宫里人本就习于趋炎附势,捧高踩低,这下更是理由十足,要不是玉霄长生殿的陈太后及时出面给予关照,亲自熬了粥汤送来,又命胜儿端到自己跟前,强令自己吃下,萌生死志的萧媛本是没有勇气腆面苟活于人世的。
由轻生到怕死,只是一个转念。萧媛看着胜儿跪在面前,奶声奶气地央求自己,心头百感交集,当下捧起碗来,一口一口啜吸起热粥。她想不管以后多苦多难,那怕从此都要夹着尾巴低头做人,只要母子能够守在一起,她也心甘情愿。至于被禁锢、被弃置、被遗忘,于她而言,都变得无足轻重,反正她也无家可归、无人可依、无处可去,再说囚系于这深宫禁苑之中,闭耳塞听,足不出户,既免了每日的晨昏定省,笑脸逢迎,更不必事事皆要看人脸色,猜人心事。
只是今天,皇后派人把胜儿从自己身边带走,萧媛心里空荡荡的象是丢了魂,静坐呆立,两不适意,头脑里胡思乱想,一会儿抱怨命运不公,一会儿哀叹自己命苦。自从被周鸾抢去太子妃的名份,便桩桩事都不如人意,而且这恶运似乎从未远离,由始至终一直徘徊于周遭,夺其位,亡其夫,灭其家,只剩孤儿寡母,彼此扶持,相互依偎。
思虑一起,萧媛便不敢往下深想,心念动时就得赶紧打住,不然整个人又会陷入幽远深遂的哀痛里,七兜八转,越陷越深,直至灭顶。
萧媛的不安源于害怕,她怕皇后就此把胜儿留在中宫抚养,让她们母子隔绝,就象隔绝她和孝献帝一样。
汪皇后应该是动了这样的念头,萧媛怎么说也是出生于凶逆之家,如今其家籍灭,肯定会心存怨怼,皇孙胜跟在她身旁,从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下,或将因此而含怨怀恨,亦未可知。到不如未雨绸缪,将他养在自己身边,挑选一些敦厚稳重的内侍嬷嬷指引教导,使之明伦理,入正道,以免将来惹是生非,招祸引患。
回到宫里,汪皇后让何大监去告知萧媛,说要把胜儿留在中宫抚养,这样两位皇孙正好彼此作伴,萧妃也可潜心静养。
宁安公主其时陪侍在母后身边,闻言觉得不可。自从父皇复辟,她见多了家族蒙祸,骨肉分离的人间惨事,心中深有感触,当下劝谏道:萧妃跟前只有胜儿,若将她母子分离,恐怕不能独活,况且胜儿长大,念及此事,又怎能不生怨心?如此一来岂不荒废了母后这番拳拳之心。
汪皇后想了一想,觉得这话有些道理,只是让皇孙胜跟从她母亲,总归有点不放心。宁安公主见母后沉吟,又说:母后不妨指派信得过的内使嬷嬷们,让他们跟从服侍胜儿,若有什么事既来禀报,岂非两全其美。
拜别母后,宁安公主携着胜儿去往春华宫。萧媛见到儿子,当即搂住,不肯松开。宁安公主跟她说起母后曾想留置胜儿于中宫抚育,自己好不容易说服母后,把胜儿送还过来。萧媛闻言,千恩万谢,泪水涟涟。
宁安公主叹了口气,劝告说:这也是上天开眼,不忍看你们母子分离,这往后打起点精神,好生把日子过下去吧。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庄王昱没有去孝献帝的陵寝祭拜,按理说他是汪皇后名义上的儿子,既然母后有旨要他前去祭拜兄长,于情于理总该去上一趟。但是陈太后以庄王受了风寒,不宜出门为由给挡了驾。
孝献后的猝然薨逝,不仅震惊朝野,更让陈太后和汪皇后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对于孝献后猝死的原因,虽然最终归咎于唐氏的余孽下毒鸩杀,但到底真相如何,婆媳两人似乎心知肚明,皇后尽管不再提及此事,但梗在心头隐忍不发,并不等于凡事无动于衷。
汪皇后现在对陈太后的一举一动都保持警惕,太后的赐食自己不尝,也不许皇孙捷尝。汪皇后以此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同时也是对太后娘娘所作所为的一种告诫。
陈太后对此浑似不在意,想赐食的时候照赐不误,王宁妃陈康妃这些人因此大饱口腹,分沾了不少意外的恩惠,毕竟太后娘娘身边的食官膳夫,称得上是国中第一,平时就算想花银子都还吃不到嘴。
对于万年吉壤奉安之处的选定,皇帝自然十分重视,只是忙于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等一干大事,一时竟抽不出身子来此巡视,皇后愿意代他而行,自是求之不得。所以当钦天监勘定了玄宫吉穴所在,皇帝立刻指派了周如喜充任山陵使,不但负责晟儿献陵的营建,还包括皇帝生母慈圣庄肃皇太后敬陵的修葺,以及忠悯恭恪皇贵妃张氏圆寝的修造。
福妃张氏被追册追谥为忠悯恭恪皇贵妃,归葬于青龙山皇陵,说来正是顺应了朝廷拨乱反正的春风,她家那些受牵连遭流放的族人向朝廷申冤诉苦,请求恤典。
皇帝听到有司奏报,想起自己囚处长庆宫时,感于张氏的忠勇,曾赐予过“忠悯”的谥号,此谥乃是私谥,当时并不为外朝所知,如今重践大位,临朝御宇,当此鼎新革故,百废俱兴之际,应当郑重其事,崇以名位,赐以哀荣,所以皇帝正式下诏授予册谥,特意在“忠悯”之外又添上“恭恪”二字,务使张氏的淑德懿行得已光大。同时放还其家人,按例封赠赏赐。只可怜张福妃的三族早已夷灭,其尸骸亦已不知所踪,皇家的浩荡天恩只能落在这些远房族亲的头上。
皇帝还借这道诏书,开宗明义,诰谕天下:御政之首,重在鼎新革故,此即拨乱反正,澄清宇内之道。天下臣民应体仰朕意,身体力行,使天意人心,合于一统。
圣旨一出,天下遵行,官府民间,至上而下,把鼎新革故、拨乱反正之事搞得热火朝天。举凡带有少帝“光正”二字之文字物件,都在禁毁、删削、修正、涂改、丢弃、隐匿之列,旧日蒙冤负屈之人,平反的平反,昭雪的昭雪,起复的起复,封赠的封赠,对那些遗留漏网的奸党余孽,则是一路追究,严惩不贷。
后宫里,王宁妃常把张福妃追册追谥的事拿来当作笑谈,明讥暗讽忠悯恭恪皇贵妃到底福禄浅薄,非但生前自己不能受用这些封赏,还连累爹娘至亲惨遭杀头灭门之祸,到是便宜了那些平日里八竿子也打不着的远亲族人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皇恩国禄。
跟王宁妃的没心没肺相比,陈康妃最近几天可谓忧心如焚。她的父亲陈大学士陈广陵因为担当过庆庶人的帝师,死后受赠崇国公,且被谥以“文忠”,这助纣为虐的昭彰罪迹,自然难以洗脱。如今更因皇帝诰谕,要鼎新革故,与民更始,有司对甄别忠奸,以论奖惩之事,不敢掉以轻心,当下将陈广陵列入附逆伪臣的名录,且排位第一,论罪仅次于元凶首恶的唐氏诸恶,其人虽已身故,但有罪未惩,势难服众,所以在削除封爵,追夺谥号之外,下一步是否平毁坟茔,曝尸示众,查抄其家,籍没入宫,尚须待廷议而定。
本来陈广陵谋逆不道之罪已经盖棺论定,不需要廷议既可毁坟曝尸,抄家籍没,然而陈康妃的祖父前太傅陈从圣,朝野上下皆视之为忠贞耿介之士,受到仕人百姓一置的推崇赞许,二陈系属父子,查抄陈学士家也就等于查抄陈太傅家,这当中究竟如何区隔?
最后廷议以陈太傅之忠贞并不能抵消陈学士之卑劣,这一父一子,泾渭分明,高下立现,所以褒忠与贬奸,可以并行不悖,因此奏请皇上,先将陈广陵从陈氏宗谱中除名,然后查抄其家,罪臣之眷属家人,亦当籍没入宫。
陈康妃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身子瘫软,几近晕厥,整个人就好象被突如其来的寒流给冰封冻结住了。所谓坏事变好,好事变坏,翻转沉浮,颠倒起落,全都由不得自己,竟仿佛狂风中的枯叶,只有晕头转向,无所适从。
本来还在为皇上复辟而欢喜雀跃的陈康妃,这一下子慌了心神,一时也不知道该向谁去求告,只是连忙派人往家中打探,都说府中已进驻了官差,老太太和诸亲六眷并奴婢小厮皆被看管锁拿,里里外外音讯难通。陈康妃经这一急一吓,身子撑持不住,顿时病倒在床头。
等到康妃身边的云萝姑娘急赤白脸地来请宁妃娘娘前去开解劝慰,王宁妃才知道外面烧起来的这把火竟然烧到了陈康妃的父母家人身上。那可是了不得的事!如果真以附逆之罪追究拿问,一旦查抄籍没的话,那陈康妃的生母嫡母连同家人岂不都要罚入内廷的浣衣局中,为奴作婢,遭人轻贱?
王宁妃大惊之下,急人所急,帮着陈康妃出谋划策:姐姐先不要急,廷议虽说有了结论,到底还要皇上诏许。只要皇上开恩,就能消灾免祸,姐姐得赶紧去求皇上才是。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是呀,这事只有皇上才能救得,自然去求皇上才是正理。只是怎样哀恳求告,皇上才肯法外施恩,赦免其家?再说皇上现在事多人忙,后宫妃嫔等闲也见不上一面,连一面都见不上,又谈何开口求告。陈康妃愁眉不展,心结难解。
王宁妃旁观者清,当即又替她出了个主意:姐姐不是写得一手好文章,见不到皇上,姐姐不妨写个折子递上去。皇上要是看了,随便批上几个字,姐姐这一大家子人不就有救了!
事情紧急,刻不容缓,陈康妃强撑病体,提笔作文,她要学汉时的缇萦上书救父那样救母脱难。只是一握笔管,想起母亲被羁押看管,身为儿女者却无力救助,心中酸涩难言,泪水长流而下,洇湿了案前的浣花笺纸。
这份表奏,陈康妃写了撕,撕了写,总怕词不达意,未能尽表其心。只要母亲金氏能够平安无事,她情愿降为宫婢,投充使役,以赎母罪,祈请皇上法外施恩,格外成全。
写成表奏,陈康妃赶紧去求内廷令王公公,等见到王守礼,陈康妃一叩三拜,长跪不起。这等大礼,王守礼不敢收用,赶紧让过一边。陈康妃这就献上细软珍玩,请王大令代呈书奏。
王守礼安慰她说:娘娘孝心可嘉,上意必会动容,老奴亦会设法周全。
陈康妃心中稍安,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皇帝最近日理万机,几无闲暇之时。从承运八年内禅囚废到昌德元年再御宇内,权力失而复得,自然格外珍惜重视。以前皇帝还常有疲懒怠政之时,现在则事必躬亲,每天召见臣工,批览章奏,下诏宣谕,忙得不亦乐乎,每当看到臣子们在自己面前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必恭必敬的样子,皇帝才会有那种乾纲独断,舍我其谁的舒心快意。
王守礼收人礼物,替人消灾,安排手下内侍把康妃娘娘的书奏置于皇上的手头,可惜陈康妃呕心沥血所作的这些情恳意切的文字,皇帝并没有加以留意。他在批阅章奏时,看到封皮上写着“臣妾康妃陈氏叩首拜呈”,就顺手搁在一边,转而拿起朝官外臣们的奏折批阅。不想这头一件便是政事堂初步拟定,只待皇帝签批,以便有司遵照执行的敕谕,其中谓已故大学士陈广陵背恩弃德,附逆从伪,罪大恶极,应毁坟曝尸,籍没其家,妻孥入官,以示惩戒……皇帝一览之后,并无异议,当下轻提朱笔,批了一个“可”字。
皇上批阅过的书奏照例先转内廷中书缮写归档,再下发政事堂遵照颁行。王守礼特意留心了一下,发现其中并没有陈康妃所呈的奏本,反而御笔诏准了对陈广陵毁坟曝尸,籍没其家的敕谕。王守礼这就去问侍候皇上笔墨的内监,才知道皇上已把康妃的书奏转给了皇后处理。王守礼情知不妙,一边赶紧让人通报陈康妃,一边让内廷中书把皇上批答好的奏折暂时留中不发。
陈康妃的书奏转到汪皇后这里,汪皇后看了之后,凝神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皇上的用意。康妃为救其母,愿意降身份,执贱役,以此赎罪,允或不允,当由皇上裁夺。而皇上对此非但无所表示,反把书奏转到中宫,虽说六宫之事归皇后总摄,但这明明是外朝政务,并非内廷庶务,岂是皇后所能置喙。
正要使人去问,便有人来报,说陈康妃摘去簪钗珥珰,素服前往内廷慎刑司领罪。
汪皇后闻言,失笑道:咦,这是要唱哪一出?
紧跟着管领慎刑司的内监公公也来禀告皇后:康妃陈娘娘忽来衙署领罪,说要代母受罚,可是未奉旨意,慎刑司实在不知如何是好?百般劝解康妃娘娘,陈娘娘总不肯听,特来请皇后娘娘令旨定夺。
汪皇后道:知道了,下去吧,这事本宫也作不得主,你们且先劝劝康妃,叫她心平气和些,一切须待皇上旨意。
慎刑司的管领内监愁眉苦脸,诺诺而退。
结束与宰辅们的会面,皇上准备传午膳了,趁这空当王守礼向皇上禀报康妃娘娘的事,其中很巧妙地把陈康妃的孝心善行大大地恭维了一番。
皇帝有些诧异,这时方想起来陈广陵是康妃的父亲,联想到康妃呈上的书奏,大概也是要为母家求情,只是自己已经诏许了政事堂的上奏,朱批既已出宫,恐怕来不及追回。
王守礼察颜观色,见事有转圜,赶紧说:老奴适才查点了一下,皇上批好的折子尚在内廷中书那里誊写抄录,暂未下发到朝堂。
皇帝“哦”了一声,淡淡说道:康妃的家事,王大令这回可是用心了。
王守礼吃了一惊,“卟嗵”一声跪倒在地,连批了自己几个嘴巴子,磕头道:老奴该死!老奴多嘴多舌,罪该万死!
皇帝一笑,道:起来吧,朕随口说说而已。陈广陵卖主求荣,辜负圣恩,实无可赦之理。康妃心念家人,出乎人子之孝,朕心亦悯。不过国法人情须得两顾,批好的折子照旧下发,你这就去知会宰辅们一声,康妃之母可免连坐,留一处闲院令其居住,以全康妃的孝道。快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