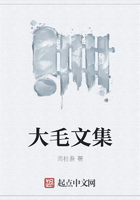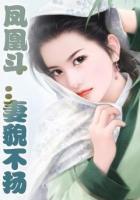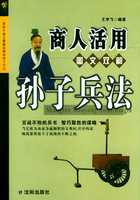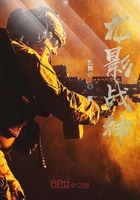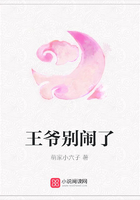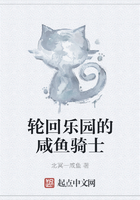有道是风水轮流转,才刚肆虐过江南金陵的血雨腥风,转眼就降临到东胡燕京的上空。跟金陵城早先的情形一样,随着大丞相宋有道被下狱论罪,汗王身边的族人亲信同声同气要求汗王对充塞朝中的奸党佞臣予以整肃。
胡汉自古不两立!胡人对于大丞相宋有道为首的汉人降臣占据朝廷的要职高位自是怀恨已久,这要不是汗王也里温起用他们为官作宰,东胡的汗账王庭哪里轮到他们夸夸其谈、指手划脚——他们真要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治国之道,堂堂的天朝上国也不至于丢掉燕赵秦晋,龟缩于江南一隅。
正是这帮降臣把汉儿的委靡之气带入东胡,使得人心涣散,所以丢盔弃甲,丧师失地,也就不足为奇。
是以东胡的这番整肃力度空前,着意在“清内奸,逐邪臣”,以复我赫赫武威,长驱而直捣江南。
宋有道下狱之后,其身边幕僚心腹亦都连坐,胡人百般搜求大丞相通敌的罪证,鞠讯之下,有人熬刑不住,往往胡乱招供指认。
以宋有道之位高权重,自有许多门下党羽甘愿充当走狗爪牙为其效力卖命,因此顺藤摸瓜,牵扯出一大群汉人降臣构成所谓的朝中“奸党”。
被逮入狱的汉人官吏越来越多,其卖国通敌的证据自然也越来越足,那些尚未受到牵连波及的在朝汉官,个个战栗,人人惶恐,生怕不测之祸从天而降。
身陷囹圄的宋有道因有汗王的特旨,虽置身囚室,仍受优待,每日照常供奉酒馔,亦未见大员提堂讯问,刑求取供,因此仍想着自救图存。他一次次上书汗王,替自己申冤辩白,恳求汗王顾念自己追随帐下,积有微劳的份上,能够网开一面,放归乡野,终此残年。只是前后数番上书都如泥牛入海,又听看守自己的人说,朝中正在清除奸党,大狱里人满得都装不下……宋有道情知不妙,胡汉对立,势同水火,稍有不慎,便能蔓延燎原,此皆毁国乱邦之源,汗王岂能听之任之?
忠君忧国的宋有道仍想上书奏谏,提笔之际,心乱如麻,想想自己所行所为,不免掷笔长叹。天有灾,国有劫,人有难,自有缘故,奈何!奈何!
宋有道的狱中上书,汗王也里温每篇都看过,其所言所奏,汗王亦深有同感,只是如今汗王在胡汉之间身处两难之地,所以在如何处置宋丞相及一干汉臣的事,汗王迟疑不决,一直拿不定主意。
他并非不想保全宋有道及一干汉臣的身家性命,当初将其人其党打入大牢,原不过是因丧师失地而迁怒他人,假以时日,仍想将其放出,虽不能官复原职,但可赠以荣衔,备位左右以听取进言。
“小不忍则乱大谋!”汗王的耳边至今还会想起宋有道常拿来告诫自己的一句话。当年宋有道举城而降,投归到汗王账下,让也里温不胜欣喜,视之为张良萧何一样的人物,不惜封为王爵,授以丞相。
汗王的宫账,旁人不得入,惟丞相随时可进,因汗王常要与丞相一起探讨治国理政的王霸之道。与身边那些粗鄙浅陋的族人不同,也里温识得汉字,读过诗书,少年时又曾往来于汉地,对此间富庶繁华深为叹服艳羡。如今胡人出关,并在燕冀之间辟地建国,汗王以为此乃吾胡受上天眷命之象,当趁汉室衰微之机,一统宇内,代天抚民,合夷夏为一家。
宋有道虽对汗王的志向击节赞赏,但对汗王所言汉室衰微则不以为然。他列举史实,并一再强调,汉室虽衰而未败,若有明主良臣,未必不能中兴,况且汉人之衰,并非因胡人强而导致,而是汉人治理不当、内乱频仍,这才让外人有机可趁。否则以汉地之人力物力,只要善加利用,自然是四夷来朝,天下宾服的局面,哪还有戎狄当道、以夷变夏的可能?马上得天下易,治天下难,汗王若不能善用治道,使民心归依,恐怕亦如前朝旧代入寇的戎狄夷蛮,只能建一时之功,无法立万世之业。
丞相直言不讳,汗王潜心细思,果然是这个道理。胡人远处边陲,幕天席地逐水草而居,不识稼穑,不知农桑,虽据有汉地亦不能治理,自己入主汉地,欲立万世之业,当收揽民心,为吾所用,这以汉治汉之术,自是离不开汉人汉臣的辅佐。
此后除军务之外,一任国政悉委大丞相宋有道,而宋丞相亦不负汗王所托,尽心尽力,督率一帮汉臣大力推行汉法,举凡张官设吏,治民理政,征收赋税,抽丁派役,大小事项,俱能打理得井然有序。
胡人在坐享其成之余,对自己任用汉臣一直心怀不满,时时加以攻讧诋毁,却不知汗王本意是要驾驭胡汉,使之合成一家,如若彼此同心同德,致力于开疆辟地,一统天下,长而久之,定能植根中土,化胡为夏。可惜胡汉之间,言语不通,风俗各异,既不能化胡为夏,也不能变夏为胡,强要撮合到一处,反而让嫌隙更深。
将宋有道下狱待罪,原是汗王应付族人的缓兵之计,然而一着不慎,却让风波愈演愈烈,实在大出汗王的意料。
正如宋有道在呈给汗王的上书里说: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果不其然,断狱审案所收集到的人证物证都一一指明王廷里在确隐藏着奸党,其人其心始终向着江南。
正是这些非我族类,别有二心的汉儿窃据朝堂,把持国政,欺上瞒下,祸国殃民,他们假意归降,暗作内应,向江南的蛮子通风报信,汗王不察,听其所为,这才搞得东胡国力衰微,战守无策,连遭丧师失地之痛,因而上下声讨,神人共愤。胡人为此聚拢宫帐,整日里喧嚣闹腾,促请汗王诛奸党、逐汉臣,早下决断。
眼见自己融合胡汉,化为一家的愿望成为泡影,也里温思前想后,下令召集东胡的八部大人共议此事。席间诸部大人皆称可杀,也里温别无他法,只得把宋有道及一干汉臣抛出去当做靶子,于是曾被汗王寄以厚望,委以重任的宋有道最终坐实了这“里通外国,图谋不轨”的罪名。
一旦找到病根,自然要出手施治,汗王也里温当即同意将宋有道等一干奸党逆臣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并悬首示众,其亲族连坐,家产籍没。
槛车过街之时,宋有道微闭双目,端坐车中,状如老僧入定,虽有沿路胡人投以菜叶烂瓜,宋有道不摇不动,恍若未觉;而其余人便没有这般好定力,一个个痛哭流涕,声嘶力竭地高呼冤枉,监斩的胡人不甚其烦,遂命人用麻核将他们的嘴塞住,使之不能开口叫唤。待到刑场上人头一一落地之时,周遭围观的胡人兴高采烈,大声拍手叫好,都道这下奸党铲除,汉儿失势,咱们胡人的运道必然蒸蒸日上。
斩决之后,有人来禀报汗王,当说到宋丞相从内使宣旨,到坐上囚车,再到受诛伏法,始终未发一言,也里温闭目摇头,长叹一声,道:“丞相可惜了!”
宋有道的姐姐,归降东胡被封为秦国太夫人的宋太皇太后,受此惊吓,一命呜呼。其儿媳降封陇右郡夫人的庄宗皇后见势不妙,忙带着不满四岁的儿子落发出家于奉圣寺。虽是如此,仍然难逃劫难,胡人以为这些从长安迁来的昔日帝室皇族与世家高门,与江南的汉人皇帝同源同脉,若再容留其于燕京城中闲住岂能让人放心,因此亦要杀之而后快。
也里温以降人既然归顺受封,杀之不祥,弃之可也。下令将他们放逐到边塞苦寒之地,让其自生自灭。
朝中的汉臣奸党至此被清扫一空,胡人们大功告成,朝会聚议之际,高谈阔论,把酒言欢,这议来议去都觉得放马江南,征讨天下,眼下正合其时。
放马江南,征讨天下既然已成定论,为防止辖下汉人暗助敌人,致国中不稳,大汗更采纳族人的意见,颁下限汉之令。诏令称胡人为国人,呼汉人为民人,朝官五品以上此后一律选用国人,地方守令亦当由国人出任,汉民只许充担从官佐吏,军中百户长以上,亦悉由国人管领,其下编列民人为奴仆军户,承担粮草夫役一应杂事。
诏令一出,民众哗然,东胡君臣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却不知牵一发而动全身。燕冀之地,汉民十居其七,当日燕京城中杀戒大开,民众本已惶惶不安,等到限汉防汉之令一出,人心再不肯依附于东胡,于是南边边郡陆续有豪强大户携家带口,冲关出境,逃奔中原。
而河东的解州,当地民众齐心协力,杀死了守城的胡人官兵,率其地来投献天子。解州之后,晋地边郡如今人心思归,都愿意投诚报效,其中暗通款曲者,不计其数。
对此,太宰张成义窃喜不已,一切皆在自己的盘算之中。胡汉离心,官民相背,不正是朝廷吊民伐罪,光复河山的大好时机,当下一边招降纳叛,一边厉兵秣马,同时上书皇上,奏告东胡驱汉虐民的种种劣行,以及河东州郡争相献地来投的赤忱忠心,更言明胡人将要南下犯我,要朝廷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
征北将军方蜀山虽说领有澶、相二州,仍苦于地小力微,施展不开,眼见边境骚动,民心归附,自然也不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当即挥师出击,不日就将周边的磁州、魏州收入囊中。
磁州魏州既然克服,邯郸便成半围之势,顺此一路北上,燕蓟赫然在望,部下劝其一并拿下邯郸,然后进击燕蓟,直捣黄龙,方蜀山思忖之后以为不妥,但云:此太宰所行事,非某家所为也。
情势牵动人心,连长安城中自尊自贵,安享齐人之福的方大用这时都有些坐不住,思量着要不要进兵晋阳,分一杯羹。
“据太宰所奏,东胡欲举国南侵,朕觉得这一战怕是不可避免!文武之道,张驰之间,如何权衡利弊,进退自如,难矣……”皇帝在与宰辅们会商研议的时候,轻轻发出一声喟叹。在场的宰辅们也都是一脸凝重。
树欲静而风不止。皇帝并不希望这个时候轻启战端,因为一旦战端开启,朝廷内外、举国上下都要被牵扯其中,皇帝现在的心思以稳定大局为重。自从复辟以来,局面虽然初定,然而百废待兴,一切尚未走上正轨,贸然与东胡决一死战,实在没有太大的把握。
但是皇帝亦明白,从把胡人逐出三秦,到拿下上党三郡,东胡那边已经退无可退,让无可让,接下来必然要与之正面交锋,只是太宰希望朝廷正式下诏伐胡,光复燕冀,皇帝和庙堂诸公都认为此事尚需留有余地,眼下还没到倾尽人力国力,与东胡一较高下的地步。
太保周如喜体察上意,奏称说:凡事没有十足的把握,那么谨慎小心总不为过。朝廷应责成太宰坚固城池,相机行事,东胡未动,我亦不动。
左相戴有忠说:上党三郡在手,凭险据守,洛都中原可保无虞。唯有齐鲁一线,与敌接壤,需防胡人从中突破,朝廷应该谕令征北将军方蜀山加强戒备,严守要冲,不让胡人侵入。如胡人硬攻河洛,亦可在侧翼配合太宰的行动。
右相陆正己也进言说:长安的方太傅虽与洛上的张太宰不合,但同为一朝之臣,大敌当前,理应捐弃前嫌,维护大局,只要胡人越境犯我,即发兵征讨晋地诸郡,驱胡逐虏,复我家邦。骁骑将军方镇川,驻节江陵,万一太宰不能御敌于国门,当死守襄阳江陵一线,力拒胡人长驱直入,进而威逼我京师江南。
皇帝听了宰辅所奏,脸色虽霁,心里却仍有隐忧,当下说:长安方太傅,前时由洛都转赴长安,其意不惬,其情不快,亦是难免,朕当亲自写信,予以抚慰。大敌当前,君臣应同心合力,一旦胡人越境犯我,当下诏讨伐,以复我河山!
殿阁深深,帘帷重重,陈太后打坐调息,吸清吐浊,气入丹田,流转周天。这龟息养生之法,乃徐神医所献的方术,陈太后视之如宝,日日勤练不缀,自是耳聪目明,元气充足,精神健旺。
自把体仁阁改名为玉霄长生殿,陈太后便开始了大刀阔斧地修葺改造。原先周娘娘咏经礼拜的佛堂,名唤“妙法如意宝境”的地方,如今改作供奉长生大帝君的仙阁,陈太后将之称为“南极紫枢洞府”,其后又另辟一处庭园,树以假山,挖以池沼,遍植花木,散放鹿鹤,丹房净室,错落有致,珠帘绣榻,纤尘不染,亦起名曰“清净无为福地”,此神仙洞府、无上福地便是当今皇太后清净自然、意守无为的修身养性之所。
每日礼敬过长生大帝君,陈太后总会在此处呆上一会,有时打坐调息,有时潜思静想。
虽说皇帝复辟,日月重光,陈太后独尊宫闱,是天底下第一洪福之人,但因为孝献后周鸾的事,她跟皇后之间不意生出许多芥蒂。汪皇后来此晨昏定省时对她就没有以前那么唯唯诺诺、毕恭毕敬,陈太后看在眼里,虽说内心有点不悦,到底还是容忍了。
周鸾的事她的确做的有些过了,没想到过犹不及,更生事端。想想当初要是袖手旁观,再怎么闹腾应该也闹不出这人命惨祸。所谓后退一步万事宽,得饶人处且饶人。过去的事就此揭过不提,太后和皇后之间本当是亲亲热热的一家人。
虽说陈太后想要息事宁人,只是没承想,好事不易成双,坏事却是接二连三,继上次安国夫人自缢身死,其家抄没,这一次又轮到大学士陈广陵,因附逆从伪,罪迹昭彰,被平坟毁碑,籍没其家。
陈太后听说此事不免叹息,虽然自己出身的颖川陈氏与陈从圣的广陵陈氏并非一家,但既然同姓陈,自然有渊源。所以陈太后跟故太傅陈从圣以前是联过宗的,而陈从圣只此一子,是故陈学士家的败亡,陈太后心有戚戚,当下便过问起陈广陵的家眷。
“吾记得陈学士的夫人朱氏,好象曾封为崇国夫人,出身于官宦书香之家,说话慢言细语,行止温柔娴雅,要论人品学识,别的国夫人、郡夫人都赶不上她……”
内侍说:陈氏满门家眷,皆因罪连坐。除了康妃之母金氏因有皇上特旨而奉旨闲住,其余人等,有封诰在身者,如陈广陵的妻子原崇国夫人朱氏,因坐夫罪,被褫夺冠服,罚往浣衣局为奴;其下无封诰的一律由官府插标发卖,所得银两,归入内帑,家族子孙因朝廷顾念老太傅生前的忠义而免于诛戳,都流配边关,编为军户。
陈太后一怔,皱眉道:果然不幸,遭此祸事!想那康妃之母本是妾室,有幸蒙恩闲住,反而正室朱氏受罚入宫为奴,其子其孙都流放边关,编为军户。堂堂诰命,沦为奴婢,子孙星散,家族沦亡,想来真是生不如死。
内侍禀道:未有恩旨,当从国法。老奴听说,朱氏亦想效法唐时宰相元载之妻王蕴秀,宁愿乱杖打杀,不肯入宫为奴,所以朱氏是趁其昏厥拿绳索捆绑而来,入了掖庭仍一心寻死,只是被人日夜看守,无法遂从心愿。
陈太后叹了口气,说:昔日安国夫人遭难,吾不曾施以援手,致有其举家败亡之惨,如今崇国夫人的事,吾当出手干预。唉,原都是好人家的女子,谁承想大祸临头,命薄如斯!
因派出身边谒者到掖庭传下懿旨,将陈广陵的妻子,原崇国夫人朱氏从籍没入宫的罪妇名录里除籍,令其在玉霄长生殿皇太后处供役,以便教习太后跟前的宫婢。
召来朱夫人后,陈太后又使人传陈康妃。嫡母与庶女见面之后,各自涕泣,不忍叙家族分离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