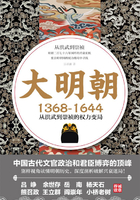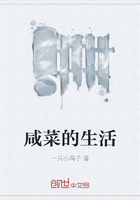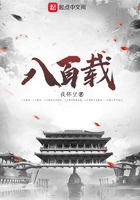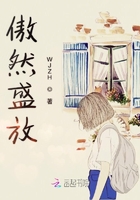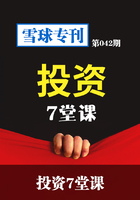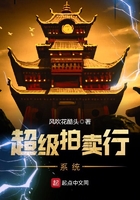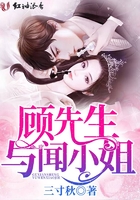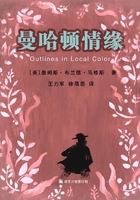象陈太后修葺改建体仁阁那样,宫里也在大力清除属于光正年代的痕迹。表面上看,自皇上复辟之后,宫里的一切几乎原样照旧,只是若拿今日跟昔时比照,整个后宫禁苑分明少了许多欢声笑语,多了几分沉沉暮气。
三年的光阴虽然转瞬即逝,但仿佛是从恶梦中惊醒一般,慌张、心悸、迷离,其间又夹杂着庆幸与释然,让人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天地翻覆,世事更张,几乎就是这睁眼闭眼的功夫,好在宫里的贵人已经习惯了应时而变,哪怕为此变来变去,变得越来越不象曾经的自己。
这其中改变最大的要数中宫皇后,以前她是个谨小慎微,事必躬亲的人,宫里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牵动皇后那颗敏感不安的妇人之心,所以她需要那些耳报神来通风报信。
再说皇后也喜欢过问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琐事,这让她觉得自己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能够使奴唤婢、当家作主的人。要是有什么事漏报了,或是她不知情,皇后反而会疑三惑四,仔细加以查点盘问。
进入昌德年后,一切跟以往大不一样,那些曾经的耳报神们都匿了影踪,皇后娘娘已经不屑于关注这些鸡毛蒜皮的细琐小事。整个后宫内廷已经没有能够危及她的人了,再盯着宫里这块旮旯方寸之地就显得狭隘可笑。
天下的事原本多得很,多到需要她去时刻留意,身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应该把眼光放得高远,因此除了皇上和太后的事值得她去操心费神,此外就只有养育在身边的皇孙捷和时不时进宫侍亲的宁安公主,尚还挂怀,别的人或事她几乎连问都懒得问。
只是宫里不能无人管事,内廷令王公公因要侍奉皇上,实在没那个精力再去管后宫的杂事,所以事无巨细,最后就都汇总到宫正监何知书那里,再由何大监分别轻重,择其详略,一一禀报给皇后。
晨起时分,趁着皇后梳洗的空当,何大监照例把昨儿宫里的情形说上一通,若皇后娘娘没有喻示或是懿旨,这一天就算是上下安和,万事顺遂,若皇后于某人某事有所交待,那何大监就得赶紧忙乎起来,以便把娘娘的旨意迅速贯彻执行下去。
“太后娘娘昨日传下懿旨,将陈广陵的夫人朱氏脱去贱籍,拨入太后娘娘的玉霄长生殿里充当使役……”见皇后没有反应,何大监跟着又说:“听说太后娘娘还要朱夫人担当庄王殿下的管教嬷嬷,比照太后宫里的女史发给俸钱……这个朱夫人既然获罪受遣,除了执贱役,供使唤,担当皇子的管教嬷嬷,怕是不太适合……”
汪皇后“唔”了一声,说:太后那个阁子当真热闹的很,庄王、长公主都养在里头,萧元妃也时不时地赶去侍奉。这回又把朱氏召进去,朱氏虽有才识,到底是个犯妇,不过这事虽说有些不妥当,只是太后已经明传了懿旨,那就说不得什么了。
何知书拱手道:娘娘说的极是。自从孝献后崩了,老奴对于太后宫里的事自然格外上心,事无大小,皆来禀告娘娘。
汪皇后点了点头:太后年事已高,如能颐养玉体,潜心修道,不再问俗事浊务,宫里自然会太平清净。怕只怕清净惯了的人忽然心血来潮,凡事想要插一下手,唉,太平不易,清净难得,无事方安!
说完了太后那边的事,何知书接着禀报皇上的动向:王大令这几日频召太医,说是御体违和,起卧不宁,太医已经给开了方子服了药,只是仍未见好。
听何大监说起圣躬违和,汪皇后不觉皱起了眉头,皇上现在又搬回到长庆宫同庆堂去了,每有军国大事,皇上都爱呆在那里召见臣工,赞画戎机。而同庆堂亦是皇上的福地,这些年来,前后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之事最后却都能转危为安。
汪皇后叹道:皇上怕是老毛病又犯了?听说胡人意欲南下,一场大战怕是难免,皇上日夜忧心于此,神思焦虑,御体自然撑持不住。唉,天下未靖,烦心事真是一桩不少。
何知书肃然道:皇上惮精竭虑,日理万机,江山社稷,百姓臣僚,宫里宫外,亦无不仰仗着皇上……前些日子娘娘曾吩咐,要老奴筹办复立皇太孙的嘉礼,如今一切都已筹备妥当,只等娘娘示下。
汪皇后沉吟未语。原想把晟儿议谥改葬的后事给办妥之后,借着拨乱反正的东风,接下来就该是皇太孙捷儿的复位嘉礼,这其中皇孙胜亦要恢复原来的丰王位号,而皇子昱则要改赐康王的名号,眼下这一步看来是赶不上了,当下摇了摇头,说:当前军务要紧,皇太孙嘉礼的事不妨先缓上一缓。皇上那里若有情况,立即来告禀本宫——对了,先问问太医,皇上的御体到底要不要紧?传话给王大令,侍候在皇上身边,凡事要多用些心。
何知书躬身施礼,正欲告退,皇后却又叫住他,说:我往太后那里问安,发现太后精神健旺,玉体甚佳,身子也一日好似一日,听说是侍疾的徐神医教了什么打坐吐纳的功法,你也打听打听,若真有灵效,到不妨让皇上也试试。
诚如皇后所言,长庆宫同庆堂的确是皇帝起居安住的福地,每有军国大事而迟疑难决,皇帝必定会呆在同庆堂深思琢磨。
自从复辟重祚,皇帝虽日夜忙于政事,精神劲头却一直饱满充足,而太宰张成义出京督师,更是让他松了口气。一山难容二虎,要想乾纲独断的君上与手握重兵的权臣之间保持如鱼得水,两相融洽的景况,实在是难上加难。所以太宰省时度势,自愿从中枢抽身,使君臣各有空间回旋,其用心良苦,皇帝亦心知肚明。
只是其后太宰督师,先是将方大用由洛上驱往三秦,跟着又挺兵拿下上党三郡,轻启战端,一意孤行,让皇帝和朝廷头疼不已。现在东胡在处死丞相宋有道等一班汉官降臣之后,其与国朝决裂的态势已经明朗,下一步大举南侵必不可免。太宰能否抵挡得住?江山社稷能否安固?天下大势最终趋向何处?如此种种不能不深思细虑,皇帝虽日日与宰辅们会商共议,然而焦虑无解,心难自安。
戴有忠、宪原等人皆说,宋有道等汉官降臣,引狼入室,为虎作伥,实在罪该万死,如今东胡将之铲除,可算是自断其臂,与我大有助益。胡人南下侵我,若无此等内奸国贼为之出谋划策,治民理事,胡人必不能在汉地久呆,所图不过是一路劫掠,满载而回。所以此战我方大有胜算,不妨放手一搏,尽逐胡虏,永绝后患。
右相陆正己虽被罢了太师,但因拥戴皇上复辟之功,仍在中枢为相,对于戴相和忠义郡王的看法,陆相颇有异议。仅就国计民生而言,连年征战不休,生民苦困,度日艰难,此番用兵,虽迫不得已,但朝廷恐怕又要额外加税增赋,不然财用断难维持,一旦缺粮缺饷,前方将如何御敌?盘剥太过,百姓如何承受?
陆相此言,太保周如喜深有同感,他因此劝告皇上:战事一起当不知延绵至何时,若不能一战而克,胡人必长久为寇,时时袭扰,年复一年,而朝廷受此牵扯,更不能用心于国事。眼下皇上重祚,天下初定,须卧薪尝胆,积蓄力量,所以安内和外仍为至重,待他日国力充足,人心可用,自当一鼓作气,驱胡逐虏,复我山河。
骠骑将军马行原则认为:胡人南侵犯我,已经势在必行,面对胡骑将至,大敌当前的局面,宰辅诸公仍在大谈内安外和岂非笑话?当务之急乃是凝聚共识,列阵克敌。此战既不可免,如何战而胜之,以至于永绝后患,才是朝廷皇上所需关注的至要所在。若能象汉之驱匈奴,唐之破突厥一样,建立赫赫武威,百姓们只要捱得一时之苦,便能长享百年太平之福。
臣子所言,皆有其理,但是皇帝毕竟不同于臣子,皇帝应该要比臣子们看得更长远,这样才能够驾驭臣下,使之效命。
皇帝为此又单独召见了陆右相和周太保,所谓往事历历,皆成镜鉴,皇帝现在对于那些手掌兵符之人不大放心,而一旦战事起,这些人有恃无恐,只怕更加坐大,难以节制。遍视朝中,惟太保周如喜是其母舅,右相陆正己系属姻亲,又都是洛都的旧家大族,在他们面前,皇帝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担忧。
“太宰轻启战端,意在依仗兵威,挟敌自重,朕对此并非全无所知。此战既不能免,太宰督师征战,虽君命亦可不听,其若肆意妄为,不惜将战事扩大,吾等君臣亦只能听之任之。此战若败,轻则胡骑长驱而下,江南涂炭,生民遭殃,重则社稷倾覆,江山易主。如若上天庇佑,太宰战而胜之,朕只怕太宰志满意得之余,或又重蹈唐逆的覆辙……”
周如喜劝慰说:圣上复位,顺天应人,上下欢欣,此国家中兴之象!胡虏屠戳降臣,凌虐汉民,尽失燕冀人心,由此亦可知天意所在,如今靖伪唐逆,先后诛灭,巴蜀三秦河东诸郡,弃暗投明,归入麾下,天下大势渐趋一统,皇上乐享太平,何忧之有。
陆正己听出了皇上的弦外之意,当下说:当国之臣操弄兵戈,究非国家之福。太宰督师征战,若不受君命,一意孤行,的确无人可制。臣以为圣上可派元勋重臣作为监军,镇守营阵,一来能代充耳目,沟通上下,必要时亦可宣达皇命,节制诸将。
皇帝颐然:朕亦有此意,当遣王守礼为监军使,代朕阅视,激励前线将士。
陆正己道:圣上,若以王大令为监军使,恐怕多有不妥。王大令虽是圣上信重之人,不过依国朝旧例,内官供职后廷不治外事,若因此生出龃龉,诸将士不奉令旨,不听号令,反而坏了大事。
皇帝一怔,皱眉说:虽说内官不治外事,当前用人之际,朕能起用者寥寥可数?且代朕阅视,当以朕的心腹股肱为任方能称心,二位卿家,目下谁能为朕当此大任?
周如喜闻言一惊,赶紧推辞说:臣居太保,虽奉朝请得已议政,只是建言献策,聊备顾问,手下既无衙署,亦无部属。监军使奉旨巡阅,代天赏罚,权重责大,自非臣等所能担荷。
皇帝不语,把目光又转向陆右相,陆正己不慌不忙,从容说道:出而监军者,须是圣上信赖之人,且身份贵重,地位尊崇,又不涉私恩旧怨,遣之宣达皇命,才能为将士信服。环视朝中,臣以为忠义郡王宪原可当此任。郡王皇室宗亲,参知政事,代掌宪台,为人忠厚谨慎,钦命监军,自然让人心服口服。
皇帝思忖,宪原果然适合此任。以其皇叔之尊,宗室之亲,的确能做到宣威布德,如朕亲临,当即拍板定案。
太宰若有监军制约,当不至于胡作非为,延误大事,皇帝权衡再三,终于决心放手一搏,这也是为情势所逼。
宣命之前,皇帝亦召宪原入宫,与之促膝长谈,皇帝说:或战或和,取决于东胡,寄语太宰,凭险固守,不可轻战!遇有大事,太宰和郡王须请旨定夺,不得轻忽。
宪原信誓旦旦,表示此行将不负皇命,务使大功告成。
陛辞之际,宪原请皇上降旨宣谕方大用,若战事一起,率其部强攻三晋,挺兵燕下,则两翼齐下,一举将胡人逐出旧土。
皇帝说:皇叔此嘱,深得朕心,洛上此行,于国至要。朕以禁军一营为皇叔亲卫,如有不法,皇叔可代行天罚,便宜行事。
根据皇上的旨意,朝廷以忠义郡王宪原出镇洛都为监军使,同时饬令太宰张成义督率上下,严防死守,不让胡人有机可趁;又责令前线的方蜀山、后方的方镇川等部,同心协力,听从征调,以御此强敌;同时策命太傅、三秦经略安抚使方大用,遥授其为晋阳留守,开府假节,伺机转攻三晋,挺进燕冀,共逐胡虏于外荒,光复我汉家河山。
此外皇帝另有密旨赐给了岭南的许成龙,要他率军北上,屯驻于杭越吴郡之间,若前方顶不住时,可驰援京师,以备万一。
至于反正归顺的涪城郡王赵思诚,朝廷也分派了差使,除了让他保境自守,还要其额外增加贡赋,以补充国用。
军情紧急,郡王宪原不敢担搁,赶紧启程,到任之后巡视州郡,抚慰军民,查点军备,忙得不亦乐乎。之后更和太宰张成义一起联名奏告朝廷:挖濠修城,屯积粮草,操练人马,凡此种种,都已准备就绪,辖下军民人等枕戈达旦,严阵以待,必不负圣上之厚望。
其后长安的方大用也上了谢表,表示恭奉圣命,不甚惶恐,愿杀敌破虏,再建功勋,以报答皇恩。
正如渴睡时有人送来枕头,朝廷授封的策命可谓恰逢其时。在他看来,占据的地盘总是越大越好,如能攻取晋阳,拿下三晋,则秦晋之间合成一体,左拥雄关,右踞峻岭,成王成霸,只在自己一念之间。眼下趁着朝廷与胡人决战之机,自己不妨从中多捞好处,如此方不愧负这上天的厚赐!
不过张成义强夺洛都的一箭之仇尚未报得,方大用又岂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所以须得让东胡与张成义先行动手,待双方各有折损,精疲力竭,才是自己出奇致胜的大好时机。
接受了朝廷策命的方大用,不顾朝廷不得轻启事端的诫令,玩起了一出“先礼后兵”的把戏。他致书燕京的汗廷,要东胡让出三晋,退回关外,则胡我之间尚能互通友好,不然太宰张成义将督率将士,东出太行,直下燕冀,驱胡逐虏,复我河山。
方大用绞尽脑汁,想出这个诡计,将朝廷谋划的方略泄露于敌国,企图将祸水南引,让东胡与朝廷彼此对阵搏杀,这样他就可以按兵不动,坐观南侵的胡骑与张成义所领的官军一决死战。一旦双方缠斗,相持不下,自己出兵晋阳,收复三晋就少了许多掣肘,顺势而下,直捣燕冀也未必不能成功。
接获方大用书信的东胡君臣果然暴跳如雷,江南蛮儿简直欺人太甚!本想避开溽暑,待到秋凉之时便放马南下,现在看竟是要提前下手。
与江南的汉人凡事讲究谋定后动不同,胡人一个唿哨,便能抄刀跃马,冲杀向前。管他娘的什么粮草辎重,给养后勤,这一路杀向江南,还不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要地有地?单是这么一想,便连七八岁的黄口小儿都是热血沸腾,跃跃欲试。
相比塞外的荒凉寒苦,燕赵之地已经如此之好,更何况眼前还有比燕赵好上十倍、百倍的锦绣江南,对于一伸手似乎就能够得着的江南,胡人摩拳擦掌早想据为己有,可恨都被朝中的一帮汉儿奸臣三番五次地给阻挡下来,如今大汗终于宰了这帮多嘴多舌、阻三碍四的狗奴才,咱们就该伸伸手脚,活动筋骨,跨上骏马,操起家伙,一路杀向江南去。
也里温与众会商,共议南征之事,之后宰马杀牛,共饮血酒,指天为誓。
八部大人各自召集手下人马,老弱妇孺皆编入行伍,胡人更逼迫汉民,充为夫役,每逢征战即驱之上前,担当人墙,抵挡箭弩。
这一次征讨江南,胡人分兵几路,倾巢出动,似乎锦绣江南,已成东胡的囊中之物。
狼烟四起,烽火弥漫。昌德二年,在得知东胡兴兵南犯之际,朝廷终于正式下诏伐胡,诏中痛斥逆胡侵我家邦,害我良民,背信弃义,自绝于天地,号令天下军民,同心同德,驱逐胡虏,光复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