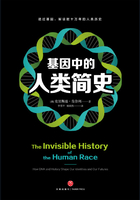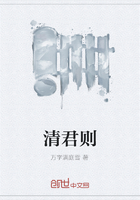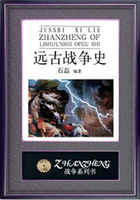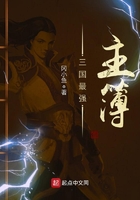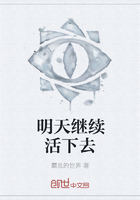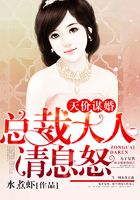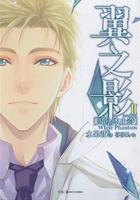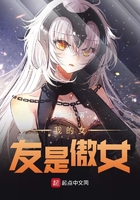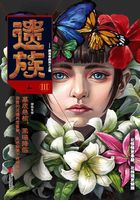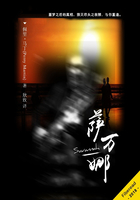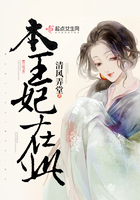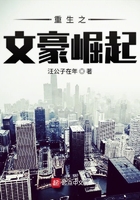皇后是一国之母,但是对自皇上登基的崇文元年就被册为皇后从而正位中宫的汪氏来说,她还远远算不上是一国之母,甚至连后宫之主也都谈不上。
按理说,这事颇有些奇怪,但是想想皇后的上头还压着两位太后婆婆,这事就显得太正常不过了。
汪皇后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她从七岁那年自己的母亲亡故后,就被姨母陈太后(先帝文宗的皇后)接到宫里养在身边。所以她打从记事起,触目所及的就是宫闱里的无休无止的争斗算计。偏偏她又是当年陈皇后的娘家姨侄女,自然而然被某些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剌,必欲拨除而后快!拨了她这根野苗子,既少了一个争夺太子妃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对抚养她长大的陈皇后的重重一击。
有一个时期,陈皇后差点地位不保,有人暗中禀告皇后,说皇上酝酿废后,已经跟几个亲近大臣提过此事。
陈皇后因此惶惶不安,汪氏那时候亲眼见到她姨母陈皇后整夜整夜的叹气,流泪,到了白天却还得象个没事人似的,去文宗的母亲宋太后(孝贞景皇后)的宫中侍奉。
有一次宋太后生了重病,陈皇后竟是一连数月都没有回过自己的中宫,她就宿在宋太后病床旁的小榻上,日以继夜侍候在床前帏下,这番孝心孝行最终感动得宋太后老泪涟涟,唤来了儿子文宗皇帝,执手关照:老身有如此佳媳,何人敢轻言废之。
有了婆婆宋太后的撑腰,陈皇后从而渡过逆境。尽管文宗日后益发宠爱周贵妃,冷落陈皇后,但废后一事却从此绝口不提。
陈皇后苦就苦在膝下无子,只生得一个燕国长公主,周贵妃呢,自嫁入宫中就接二连三的生,可惜都早早夭折,留下的一个独苗苗,就是当今的皇上。
文宗皇帝龙驭上宾,当今皇上即位,生母周氏母以子贵,得已与嫡母陈氏并体同尊,形成两宫对峙。刚当上太后的周氏咄咄逼人,凡事皆不肯居于陈氏之下,陈太后退避闲处,并不与周氏争锋计较。所以这十年下来,两宫太后各居一处,倒也相安无事。
幸而陈太后高瞻远瞩,早早就布下一局妙棋,终使得汪氏安然上位,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虽然这一切,得来纯属侥幸。
当年,为了修好关系,她姨母陈皇后亲自去向周贵妃说亲,希望能将汪氏配许太子,从此永结两家之好,不料周贵妃一口回绝!她以那种鄙夷不屑的口吻回复陈皇后:“既非侯门公卿之后,又非世族大家之女,如此身卑位贱,如何能入得太子的东宫?太后娘娘曾订下仪规,后宫嫔妃当从清华之族勋贵之家选取,严禁私下采选招纳,这禁牌就挂在后宫的宫墙之外,皇后岂是故作不知。”
陈皇后一头碰了个钉子,嘴上虽然不说,心中实是气恨不已,但是解铃任须系铃人,既然宋太后能订立规矩,当然也能打破规矩,陈太后于是转而央求宋太后出面。
面对宋太后,周贵妃还想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子,说汪氏出身微贱,不配入东宫。不想反遭宋太后一顿怒责:中宫皇后的母家之女,有谁敢说不尊贵!
于是便以太后指配的形式,让汪氏和永福宫唐氏,永庆宫李氏,永和宫孙氏一起成为太子的嫔妾之一,而太子妃宋氏因是宋太后的内侄孙女,早被文宗皇帝钦定为太子元配。本来只要宋氏在堂,中宫之位自然轮不到旁人去争,不想太子妃宋氏是个多病殃子,只当了三年太子妃就撒手西去。
四个嫔妾都觊觎这空下来的东宫储妃的位置,花尽心思,用尽手腕,想让太子对自己情有独钟,谁知太子早被姓宋的病殃子弄烦了,无意再立继妃,这事便由此耽搁。直到一年后文宗驾崩,太子仓促即位,大臣上奏陈太后说:先帝驾崩,国之大丧,三年不嫁不娶,太后宜为陛下早立皇后,内安后宫,外抚人心,而治丧立后,两事并举,既合礼仪,亦苻天下万民百姓之望!
册立皇后,乃国之大事,容不得旁人作主。陈太后于是颁下懿旨:中宫虚悬,诸礼难备,先帝在时,曾谓太子良媛汪氏,贤良淑惠,德配中宫,可正坤位!今当奉大行皇帝遗诏,册立汪氏为皇后。
同时再发谕旨,圣母周氏,涎育当今皇上,于社稷宗庙有大功,宜加推崇,尊之为太后!册立尊封两道谕旨,皆布告天下,咸使闻之,其所具之礼由宰相率同有司一并议定遵行。
汪皇后至今仍是钦佩感激陈太后,此计妙极,既与周太后化解冤结,又让自家人当上皇后,仓促之中,生米熟饭,皆赖陈太后一手定局。
汪氏被立为皇后,果然神灵庇佑,于崇文二年生下儿子,这孩子既是皇后亲生的嫡子又是皇上的长子,果真福份极大。汪皇后这下地位巩固,再无顾虑。
皇后临产之时,两位太后都到产室探视,见到初生皇子,陈太后喜极而泣自不必表,周太后也是异常欢喜,忙叫人敬神还愿,皇后虽与自己不是一条心,但生下的这孩子毕竟是自己嫡嫡亲亲的头胎孙子。
汪氏骤得贵子,心中石头落地,侍君事上更见谨慎。同时斋僧礼佛,广做法事,只求列祖列宗庇护,满天神佛保佑,让吾儿平安长大。
汪氏种种举止言行,陈太后固然频频嘉许,连周太后看在眼里,也觉得这汪皇后端庄安详,性情和善,不妒不燥,实在难得。
汪皇后性格纯良为人和善不假,但也并非木头一根,更不是唐贵妃口中的泥塑菩萨!她身在中宫,耳目却遍及整个内廷。试想想当今皇后,未来的太后,别人想投靠还怕投靠不上。所以皇后一个小小的吩咐和要求,众人争抢着去干,还只怕干不好,让皇后娘娘不省心。更何况,事成之后皇后的赏赐每次都厚重得惹人眼红心动。
芙蓉馆的那档子事,汪皇后早就注意到了。皇上整日呆在芙蓉馆,鸾凤和鸣,晨昏颠倒,汪皇后她都了如指掌。呵呵,她不想知道都没辙,总是有那些有心人,暗通款曲变着法子想让皇后娘娘对自己有个印象,于是有关皇上的大事小事,事无巨细,都有人接二连三的往皇后的中宫传报。
汪皇后想:皇上这回怕是玩野了,玩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这档子烂事,本宫倒是由着他去,等皇上玩得过火了,自有人出面制他。
现在汪皇后只要每天看到太子神气活现的站在自己面前,奶声奶气叫几声:母后;口齿伶俐地背诵那些子曰诗云,便会烦恼立消,忧愁顿失……
汪皇后是个精细人,她七岁就进了宫,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地熬下来,傻子也变成人精了!所以这皇宫里主子奴才,上上下下,各色人等的心她都能够猜透摸熟,唯独有一个人,让她从一开始,就在内心深处隐隐的感到敬畏和惧怕。而她怕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姨母早已迁居延年宫的陈太后。
汪皇后至今还能想起她七岁那年的往事,她记得她母亲在病榻上,用尽最后一口气挣扎着告诉她:“我苦命的孩子,你到了宫中要处处小心谨慎,千万不能说错话做错事。你是个外来的孩子,比不得那些天生的金枝玉叶!别人要是欺负你,千万记住要忍着,忍着,忍着啊,孩子!”
母亲殁了,汪皇后被陈太后接进宫中。在一个七岁女孩的眼里,她眼前呈现的世界,简直就是一座天上的宫阙,有数不清的门廊,走道;数不清的殿阁宫室;数不清的男男女女成天就围着宋太后,先帝文宗,陈皇后,周贵妃等几个人打转。而她也要整天对这几个人磕数不清的头,陪无数的笑脸,装十二分的小心。这小时候的印象是如此难以磨灭,以至于一想到宫廷,回映在她头脑里的就是门廊走道,殿阁宫室,男男女女,请安磕头,以及陪笑脸和装小心……
汪氏还记得她入宫时跟姨母陈太后的第一次对话,那是在皇后的中宫承天宫东首的暖阁。那里铺着大片大片牡丹纹理的腥红地毡,有一张百鸟朝凤的巨大画屏,画屏的四周,高高低低陈设着香炉宝鼎,清烟袅袅,异香扑面,熏得人有些昏昏欲醉,陈太后就高坐在画屏下面的金漆蟠龙椅上,用一种没有表情的表情望着自己。那时的陈太后可一点不象现在这样消瘦,她那时的样子很端庄好看,描龙绣凤的衣服花花绿绿的很是漂亮,她高坐在那里默不出声的时候简直就像是庙宇里供奉的天仙圣母,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
到底还是孩子,当时她忽然就被陈太后头上所戴的七宝珠冠给吸引住了,那冠上金龙飞升,玉凤展翅,珠围翠绕,说不出的华美精致,那龙头与凤首都做的栩栩如生,一动一颤,真是流光溢彩,满目生辉。汪氏简直羡慕得不行,她盯着那顶珠冠看得全神贯注,心中在想,要是我也能戴上一顶,可不知多美!
“宫里好玩吗?还呆得惯吧!”陈太后的声音虽然柔和,但是空空洞洞,冷不丁地在耳畔响起,立时打断了她的遐想,也让她浑身的皮肉先是一麻跟着又是一紧。
她赶紧收回眼光,低下头温顺的说:“回禀皇后娘娘,小人喜欢,小人喜欢呆在宫里,能够入宫陪伴娘娘,实在是小人天大的福份!”她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一来这么好的地方,谁会不喜欢呢?二来,她也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地方能让她去依附投靠。
陈太后很满意她的回答,因为陈太后的脸上露出了平常难得一见的笑容。
陈太后微笑道:“我想世上只怕没有人会不喜欢宫廷!哼哼,宫廷,不知这世上有多少人打破了头想挤进来,可惜没门!她们既没机会,也没靠山,所以只能远远的看着,内心里面嫉妒着羡慕着……呵呵,宫廷多有意思啊,高高在上,俯瞰人间,唯有命中有福的人才能跻身其间。说起来你也是个有福的孩子!来,到本宫跟前来,让本宫好好看看你。”
汪氏很是乖巧,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抬头迎着陈太后的目光,恭恭敬敬地说:小人能够进宫侍奉,全赖皇后娘娘的齐天洪福,皇后娘娘的大恩大德,小人一天都不敢忘记。
陈太后点点头,叹道:看起来真是个乖巧伶俐的孩子,日后若能记住是谁提携你,那也就不枉本宫疼你一场。唉,我们陈家向来人丁稀薄,又非世族高门,本宫想要提携一二,也指望不着谁。我那没福气的妹子更是可怜,今生没能享到什么大福,这就撒手西去了,丢下你这孩子,孤苦伶仃的,好在都是一家人,本宫自然会予关照调教,从今往后你就留在本宫身边,燕国公主那儿正好也缺一个陪伴,虽说她脾气有点不大好,你凡事多忍着让着她些,也就是了,待会儿让嬷嬷们带你去见她……在宫中应该行哪些礼节,守什么规矩,嬷嬷们自会教导你的。
汪皇后从此就在陈太后的身边生活了差不多十年,直到十六岁,她被选为太子身边的嫔妾,这才搬离了承天宫,住进了太子的东宫……
说到嫁入东宫侍奉太子,这事全靠陈太后在背后鼎力相助,可就算嫁进东宫,也并不顺风顺水,诸事如意。
她与太子虽说自幼熟识,但是熟识的结果不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而是有目无睹,视若等闲。
这与陈太后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陈太后为此呵斥了她几次,要她跟太子亲近一点,她若能攀附住太子这棵大树,她在宫里才能站稳脚跟。
面对陈太后的训斥,汪皇后没有理由申辩,虽然她心里感到委屈。她对太子当然很用心上紧,随时随地总想往太子爷的身边凑,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太子压根就没把她放在眼里,她以前不过是燕国公主的一个贴身跟班,平时沉默不语,做事谨小慎微,论起聪慧机灵劲儿,万万比不得春水侯家的小姐唐丽云,更何况在唐丽云之上,还有东宫元配太子妃,此外李氏、孙氏,凡事也不遑多让,一月当中,汪氏侍奉在太子爷身边的日子寥寥可数。
许多时候,连汪氏自己都泄了气,她这一生,平淡安稳地做个嫔妃,高高在上,养尊处优,也没有什么不好。
不过有句老话说得一点不假:有福之人无须忙,笑看他人忙断肠!
依仗着陈太后这个得力奥援,汪氏得已入选东宫,这之后顺风借力,更上层楼,成为了当今的皇后,跟着又顺利涎下了晟儿,于是功成名就,一切圆满,这世上再无忧心劳神之事来困扰汪氏。
有子万事足。心满意得的皇后娘娘越发“恩泽广布,温和贤良”,中宫有这样的皇后,自然是众人的福份,没有人不为之赞颂感恩,而皇后汪氏也很受用这样的赞颂感恩,因为她施予众人的恩泽,最终都会变成自己的福份。
回忆层层叠叠,漫无边际。汪皇后省过神来,目光睃巡过眼前的宫室,这里的一切都烂熟无比,其间氤氲的那股让人昏昏欲醉的气息,从她七岁第一次踏入时,似乎就一直存在。这气息一度令她不爽,只是没想到她最终也会与这些气息混同在一起。
皇后的内心深处,其实很讨厌回忆,她讨厌勾心斗角,讨厌阴谋诡计,讨厌承天宫雕着层层迭迭的游龙嬉凤,富贵牡丹,延年仙鹤的沉甸甸的三层大屋顶。这硕大无比的屋顶高高在上,看一眼就让人眩晕,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它的威严气派,它用它的高高在上向旁人显示一种不可小视的庄严肃穆的存在。它使生活在这屋顶之下的主人也变得同样的庄严肃穆,不可小视。
汪氏当了十年的皇后,十年之间她将承天宫的陈设布置改了又改,力求跟陈太后做皇后时的格局相反。虽然她做了这么多的改动,但还是丝毫改变不了那些儿时的记忆,更改变不了弥漫在承天宫里的那股气息——皇后以为这气息老旧陈腐,因此想过许多办法加以驱除,可不论花香还是果香,檀香还是沉香,越是蒸熏那气息就越是浓郁。直到皇后慢慢习惯了这股气息,并且从内心开始喜欢起这座宫室。
这是她当家作主的中宫,是她母仪天下的所在,她呆在这地方越久,就越能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尊荣富贵,享受着那些羡慕的,嫉妒的,讨好的,敬畏的,惧怕的眼光。这里曾是陈太后的天堂,也是周太后梦想占据的地方,现在它是属于她的。
汪皇后由此想起她苦命的母亲临终时对她的叮嘱:忍着,凡事皆要忍着,要忍着啊,孩子!
这么多年来,她时刻牢记了母亲的叮嘱,忍、忍,咬着牙关忍,终于忍成了皇后,并且还要继续忍,一直忍到她那伟大的儿子成了皇帝,那她就出头了,也就能够出气了。
她头一件事,就是要拆掉这座她既喜欢又觉得腻味的承天宫,她要在它的基础上,建造一座更大的承天宫,这是她理想中的承天宫,是她颐养天年的场所,她将在这座宫里开开心心的活到老死驾崩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