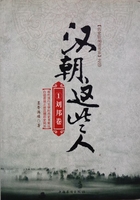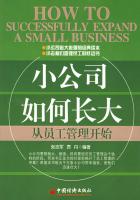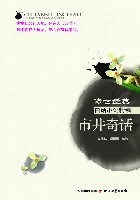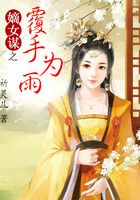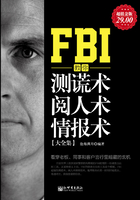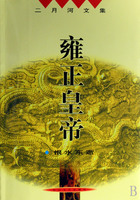春末夏初,南都来了一个特殊的人物。其人之所以特殊,一在于其身份,二在于其来处。
他是从洛都而来,他有一个长长的名号——“太平真人玄教大宗师”,他就是名满天下的得道高人张虚静张大真人。
张真人舍洛都而投奔南都,足证其人是忠贞坚定的义烈之士,也是靖逆无道失德天下离弃的表征,朝廷自然给予嘉奖,赠张虚静二品卿衔、在南都慕义坊赐给宅第,并命主掌天下玄门道教事。
朝廷里也不是没有人怀疑张虚静的来意,他莫非是洛都派往南都的一个卧底的奸细?千里迢迢,经州过府,洛都方面竟然任其南归,不予揖捕,可见是衔有使命。并且张真人于在洛都的所行所为语蔫不详,象洛都逆臣给靖王所上的劝进表,其中据说就有张大真人的署名。一个依附伪逆的贰臣,此时来到南都,这是张真人此行最为可疑之处。
对此张虚静的解释是,方外之人,教化苍生是传道弘教之本,故率门人弟子南归,一路上多逢各地道友教众接应,故而有惊无险,安然抵达南都阙下。
皇帝听说了这件事,以大真人千里来归,其忠贞可嘉,亦是朝廷之幸,诏有司勿问其它。
皇帝还说,待大真人休沐之后,将予以召见,聆听大真人对于国事的建言。
张虚静此行的确是怀有使命,否则靖王也不会放他南归。靖王现在愿意与江南化干戈为玉帛,需要有人居中当说客,他想来想去,才想到派张大真人去。
张真人是方外之人,与南都的皇帝颇有渊源。派他去可以借口是传教弘道,即使有人怀疑也容易搪塞过去,况且张真人既没有预闻洛都的军机,又不曾知晓南都的隐秘,于双方都能接受,便是他借机投奔江南,也不会泄露什么了不得的机密。
至于张真人本是南方人,根基也在南方,听到靖王肯放他南归,自是喜出望外,所以靖王关照他的话,是件件都应承了下来,唯恐靖王反悔。
但是从张真人个人的内心来说,他无疑是更效忠于南都的皇帝,毕竟他从一个南方名不见经传的小小道士一下子鱼跃龙门成为“太平真人玄教大宗师”,这都是皇上的优渥恩赐。
如今他返回南都,皇帝非但未治他一个附逆之罪,反而赠官赐宅掌教,这怎不叫张虚静感激涕零,唯求报效。
张大真人觐见皇上是在新建成的临安殿,殿里没有他人,只有皇帝并身边几个内侍太监。
张真人端详着皇上,只见眼前的皇上面容消瘦,神情疲乏,似有未老先衰之象,已不复当年张真人在洛都所曾见过的那个神彩飞扬,俊逸爽朗的年青天子了。
张真人心中感慨,葡伏在地,磕首问安:贫道归来阙下,磕见圣上。
皇帝淡淡的说:老神仙请坐吧,大老远的赶到都下,想来挺不易的。
张真人说:贫道受圣上的深恩,岂敢背弃皇上而臣事伪逆。
皇帝听了这话,不觉心中愤愤,大声说:洛都的旧臣若是都有这份忠心,靖逆何以能够成事!朕一直想,朕待士绅百姓一向不薄,国家养士养兵亦有近二百年,忠孝礼节,道德廉耻,他们平日也都烂熟于胸,靖逆谋篡之时,满朝文武、京师百姓却无半点忠孝节气,甘愿依附伪逆,以图保存富贵!
张真人说:东胡犯境,洛都人心慌乱,而圣上巡幸在外,天假其便,所以靖逆趁机窃国,而满朝文武无兵无卒,京师百姓又是一盘散沙,面对靖逆的骄兵悍将,自是张皇失措,只能俯首称臣,其实官员百姓内心未必肯服。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者,比比皆是。
皇帝紧绷的脸总算松开了一点:“朕想也不至于如此……朕虽薄德,治国或有不当,亦不至于天下离弃……”
张真人说:其实靖逆对于依附的朝臣们也是心存疑虑,不敢放手重用,眼下在洛都耀武扬威之辈皆是靖逆由西蜀带去的一帮凶顽之徒。此辈沐猴而冠,骄横不法,攘夺民财,不遗余力,民皆以为苦,转而感念陛下的仁慈,都以当初劝进附逆为悔。
皇帝“噢”了一声,不屑道:孽由自造,咎由自取!上苍借靖逆之手惩治劣民,以教愚顽,以明正道。
张真人应和道:诚如陛下之言,如今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上了贼船便难下了!
皇帝道:“哼哼,不吃足苦头,他们又怎知反悔?”当下乃泛泛的问起洛都的旧事,如宫室、陵寝、宗庙,以及洛都的街市,风物。
张真人都据实以告,特别说到西苑荒废已久,太液池几近干涸,长乐殿未央殿虽在,但已殿空人去、衰草离离,皇帝听了直是叹息:洛上繁华,南都终究无法比拟啊……
张真人说:可是正统在南而不在北,人心思南而不思北,皇上何故叹息。
皇帝说:家国遭难,河山破碎,思之岂不伤哉!假若是天命如此,朕亦复何言!老神仙乃世外高士,可有良策可以示朕?
张真人拱手说:天命亦在南而不在北!靖逆窃国,人神共愤,陛下当思进取。贫道自北边来,靖逆曾与贫道言,愿与皇上握手言和,共致太平。此靖逆内外交困,不得不筹思自保,故托贫道归来言与皇上。
皇帝在江南坐稳了身子,听到靖逆的名号亦不象先前那么剌耳,当下说:靖逆肯放你南归,想是有话要带于朕,此殿中只朕与卿在,老神仙有话不妨径直道来。
张真人说:靖逆作乱,为祸中原,眼下却困于东胡进逼,凶焰渐失,而中原人心难服,盗贼蜂起,靖逆迫于形势,唯有与陛下讲和,以便全力应付东胡。
皇帝冷笑道:势随时移,想不到他也有与朕谈和的时候!早知今日挨打,当初何必做贼!
张真人见状,便向皇上进言讨逆。
张真人说:中原之民翘首以盼王师久矣,眼下靖逆外困于东胡进逼,内忧于人心渐失,所以不敢轻举妄动,而附逆的朝臣亦有许多心向皇上者,王师出动,必作内应。
皇帝说:讨逆平乱,朕之大愿也,只是朝廷刚刚播迁到江南,诸事不备,百姓困穷,如若屡兴大军,则必滋扰生民,朕于心不忍。或许静待时机,徐作长图,靖逆作孽,必有自毙之时,天下自然乃归一统。
张真人听罢,低头默然不语。
皇帝又说:朕自即位以来,虽未必事必躬亲,兢兢业业,却也没有荒废儿戏,于百姓亦没有横征暴敛。朕也曾下诏求治,任用贤良,力图创中兴伟业,奈何积弊深重,妙手难医,朕一直思想,此中莫非有天意尔,故使朕遭此挫折……,思而想之,常为之不解?
这事皇帝常思常想,至今仍是满腹委屈,所以忍不住要替自己剖白辩解。
张真人叹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陛下深居宫禁,当国掌权者亦都是豪门贵戚,素日里高处庙堂,何以知天下民生之艰难。贫道出身微贱,自小厮混于街市巷闾,行游江湖,触目所见皆是大小权门豪夺劫争,毫不以生民百姓为念。天下出产,世族权门夺其八九而百姓仅赖一二,如逢凶年,则难存活,长此以往,岂不人心思变?民心即天心,民意亦天意,所以上天降此劫难警示陛下。
皇帝默然,过了片刻才道:权贵豪门充斥天下,朕亦深忧,只是树大根深,难以憾动。朕虽为天子,有心鼎新革故,然臣下左推右阻,事事非难,豪强权门亦不肯与朕相协,朕有心而无力,亦为之奈何?
张真人叹息一声:历朝弊政,积重难返,如病入膏肓,的确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荡尽。而群臣对此视若未见,争相歌颂盛世太平,若非靖逆乱起,举国岂非蒙在鼓里?今日陛下巡幸江南,而积弊仍在,贫道因此深为陛下憾!亦为天下忧!
皇帝道:世事皆难预料,人算亦不如天算,想人生区区百年,白驹过隙,飞鸿雪泥,朕私心惟愿此生此世能够平安无事做个太平安乐天子,可惜天不能予。退求其次能够安住江南,传承后世,于愿足矣!如今朝廷播迁南都,朕却常感神思疲乏,夜梦频仍,精力往往不继,老神仙世外高人,道法精妙,但问可有养生延寿的好法子?
张真人说:若想养生延寿,必得牢记清心寡欲、顺其自然这八字。
皇帝皱眉说:心不能清,欲不能尽,朕欲养生延寿竟是不能了?朕闻历代皆有帝王调丹鼎,练元阳,服食仙饵玉露,以求长生,不知其灵验若何?
张真人正容说道:贫道只练内丹,从未列鼎练丸,贫道亦未闻有服食丹丸而能飞升成仙的帝王。陛下心不能清,意不能守,气则易散难存,神则涣漫无主,贫道以为,须调养五内,清心凝神,抱守元真,持而久之,必有灵验绩效。
皇帝说:若非杂事缠身,朕真想弃俗入道,当个人间神仙何其逍遥极乐。
张真人说:圣上俗缘未尽,不宜入道修真,况且做神仙须耐得清苦,一箪食一瓢饮,孤身只影云游五湖四海,驱邪逐鬼,救度世人。皇上若心怀仁慈,常存善念,爱惜民生,倡导礼仪,昌盛教化,使黎庶百姓安居乐业,这便是最最上乘的修行了!
皇帝点头微笑,当下又问了许多通神役鬼施符作法之事,张真人一一替皇上解说,皇上听得津津有味,心向往之。
结束了与张真人的会面,皇帝亲自送大真人于殿外,目送大真人登车而去,皇帝归来静思,仔仔细细的想,觉得张真人的话颇有见地。
想那宗庙陵寝皆在中原,靖逆窃踞,总是心头大恨,如今趁着靖逆内忧外困之际,应当设法剪除剿灭,永绝此心腹大患。
皇帝于是派人宣召太宰、成国公陆正己进宫。
皇帝对于陆太宰现在是相当的倚重,此人灵活机变,比周如喜能干,比柳子安听话,又不象唐觉之那样任性使气,比唐会之戴有忠这些后起之辈更多些声望人缘,何况从洛都到南都这一路之上,都亏了陆正己跟在身边调处守护,实乃是从龙的首功之臣。
皇帝此时想到的便是陆正己曾经向他建议的联络东胡合攻靖逆的计策。
陆太宰来后,皇帝立刻向他说明了张真人的意见和自己的看法。
陆太宰沉默良久,才说:真人旁观者清,其言未必不成理,但真人方外高士,于国事之错综复杂之处,未必能够左右权衡,上下协调。北伐一事,开启容易,一战而胜固好,假若兵连祸结,延年累月,必然江南糜烂,不可收拾;至于与东胡通好,此事应与廷臣合议,取得共识才成,这样柳太师和唐太尉也才没有话说。
皇帝道:北伐一事,未有八九分把握不能轻启,与东胡通交结好,现在似可实行,如果三公意见不一,那就开大朝议,交由群臣讨论,以定下共识。
陆太宰说:通好东胡,此机密事也,人多嘴杂,反而不妙。
皇帝道:依卿之言竟是不能成事?
陆太宰说:臣闻东胡大汗今年适逢半百之寿,朝廷不妨派出使节以贺寿为名前往,一来借机察情观势,二来试探能否互通友好,至于能不能缔结南北合攻的盟约,尚须照情形而定。再说此事但问之于重臣便可,太师即使反对那也是孤掌难鸣,不起作用。
皇帝笑道:以贺寿为名派人出使东胡,这个主意好。事不宜迟,当早定大计。
皇帝动了心,此后几日频频宣召柳太师和唐太尉并左右相。
唐太尉说,政事宜问宰执,臣但主军务而已。
柳太师一心以北伐一统为念,对这个交结东胡南北夹攻的计划,并不热心。他劝告皇上说:交好东胡,必诱之以利益,若东胡索取无度,未必容易打发。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靖逆如狼而东胡如虎,为驱恶狼而引猛虎,殊属不智。
皇帝不死心,又再询之于唐左相和戴右相。唐左相说:北伐或是通胡暂时都没有必要,陛下宜守宜静,稳住江南,观其变化。
戴右相对皇帝提议的结好东胡一事却是极表赞同,不仅赞同还参与出谋划策。戴相认为,远者交,近者攻,用兵之道也,结好东胡,则靖逆腹背皆敌,自不敢轻举妄动,江南亦可赖此而保全,所以力请皇上议而行之。
就在南都君臣尚在热烈讨论,没能做出最终决定之时,洛都方面又有了进一步的大动作。
这一次是靖逆居然放归了周太后的宗族,子弟妇孺凡三百余口由太后之弟周如乐率领投奔南都而来,其距张真人来朝才不过二旬。
当年周如乐以平夷大将军之职奉命讨伐西南造反的木姓土司,不料大军开出竟是连吃败仗,被罢职槛送京师治罪,后因唐觉之取得大捷,平复了西南叛乱,周如乐才蒙恩获赦而归第闲居,不曾想皇帝离京谒陵,而靖王入都篡政,周如乐及其全族走避不及,陷于靖王之手。
一开始靖王将周氏全族统统投进监狱,周如乐以为大难临头,家族当诛无疑,不想皇上却在江南站住了脚跟,迫使靖王改变态度留下周氏合族的性命。
周如乐来到南都,带来了洛都方面更确切的消息,这消息让一心想结好东胡的南都君臣为之欣喜若狂。
东胡一直以绸缎布匹皆不如先前,茶盐之物也是以次充好,屡屡逼迫靖逆献纳更多更好的贡品礼物,并威胁说如若不然,将挥军而下,尽占其地,尽夺其民。
靖逆为此忧心不已,杭绸湖缎向为江南所产,湘茶吴盐亦是南方为最,中原不是向来不产,就是虽产质次,不中东胡大汗之意。
所以靖逆这次借放周如乐南归,再次表达相互结好之意,并愿出重金购买江南所产绸缎茶盐,靖逆并建议南北议和,共缔互不相侵之约。
皇帝召大小臣僚集于朝堂合议此事,君臣们都认为这是靖逆走投无路而有求于我,应予痛斥以绝其望。
议决的结果当然是断然拒绝与靖逆议和,更不许将绸缎茶盐之物流出境外以资敌用,皇帝并令人张榜立碑,公告于朝堂及南都九门之外——“有提及与逆贼议和者,斩!以禁输之物资敌者,斩!”黑底红字,赫赫分明。
一方面,皇帝派出敢死之士携带诏书前往洛都,诏书中说:靖王如能认清形势,应当上书请罪于朝廷,并削去尊号,退归西蜀藩地,皇帝尚能体念靖王为朕皇叔,自会给予宽宥赦免,如若据地以抗王师,必只有坐等灭亡。
另一方面,南都群臣倡议联络东胡共击靖逆的呼吁声嚣尘上,连深宫里的汪皇后都据此向皇帝进言。这下柳太师也无法坚持己见了,甚至私下里考虑了几回,觉得倒不妨派出使节与东胡先行接触,碰碰运气,也说不定运气好,南北合攻就灭了靖逆。
柳太师既然不出言反对,那内心自然是首肯了。皇帝由是欣然定策,诏以昌盛侯周如喜为正使,吉庆伯唐会之为副使,衔命北上结好东胡。
由于靖逆窃据中原,陆上路径难通,周如喜唐会之一行只能由长江口泛舟启航,然后转道海上北行。
周如喜唐会之这一番出使东胡,朝廷寄予厚望,因此作了充分的准备,除了所携的国书和随行的从人,并不曾忘记装载大量的绸缎茶盐之物,并有若干金银饰物,甚至脂粉珠花、香料药材用于交结东胡的权贵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