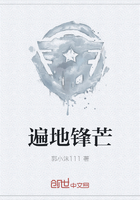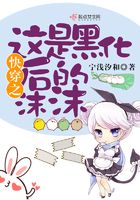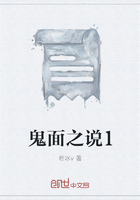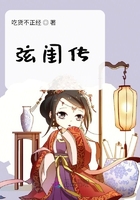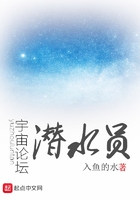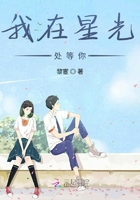人类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表明,至少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就始终贯穿人类文明发展全程,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类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史。据不完全统计,人类文明自有文字记载的5500年以来,共发生过15000多次战争和武装冲突,并造成了几十亿军人和平民丧生,其中,只有300年是处于和平时期,平均计算,相当于每100年,只有短短一个星期的和平时期。
一、战争和武装冲突
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巨大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军人死亡2114万,直接军费开支总和近1863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军人死亡2206万人,直接军费开支总和近11170亿美元。此外,两次大战造成的平民伤亡和经济损失更是天文数字,难以计算。两次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惨重教训,并直接促进了战后反战运动的高涨、和平主义的兴起,以及规范、调节和管理国家间行为的各类国际性组织的成立,其中最重大的事件,当属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
联合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为宗旨。《联合国宪章》确定了“国际关系间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并规定,“一国只有在单独或集体行使自卫权或参加联合国采取或授权的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力”,这就意味着,战争是非法的。
《联合国宪章》的权威性、约束力不容乐观,作为表现之一,是自其签订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并没有减少的迹象。美苏“冷战”期间,地球上每35年发生一场战争。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100余场战争,有90多个国家参战,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数量,并造成900余万人丧生。目前,世界上的193个国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国家处于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状态。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冷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制衡的局面消失,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强权或强权同盟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的现象有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多极化”的政治格局虽已成形并将继续得到增强,但多极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严重失衡,且这种失衡状况将长时间持续下去。
由于全球范围内政治和军事制衡关系的缺失和无力,使得强权或强权同盟更倾向于对弱小对手采取军事手段或使用武力威胁来解决问题。对于拥有超强军事实力的他们而言,军事手段更为简洁有效、成本更低。自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战争,无一不是这种情况。至于使用武力威胁的情况,更是数不胜数。
人类社会中,由一个集团发起、反对另一个集团的暴力行为,是人类的一种常态化行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想象会消亡。但是,战争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并因其具有设定的政治目标,而又与一般性的暴力行为有着显著区别。
战争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政治目标始终是战争的动因,战争是达成政治目标的途径和手段,战争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上的需要。最重要一点,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政治上的和平,而不是纯粹为了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未达成政治目标的军事胜利,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胜利”。这也是一些情况下所发生的:“赢得了战争,输掉了政治”。
战争通常被定义为“一个政治集团用来反对另一个政治集团的有组织暴力。”这里,突出了战争的“有组织性”,而暴力行为并非总是有组织的。战争在政治集团之间进行的,政治集团可以是国家、国家联盟或同盟、非国家性质组织等。此外,对战争常常有量化的要求,主要是与规模相对较小的武装冲突进行区分。例如,通常至少有参战的一方要遭受超过1000人以上伤亡的武装冲突才能界定为战争。虽然这种衡量和定义战争的方法有些简单和武断,合理性常常受到质疑,但在关于战争的研究中已成为惯例,方便且操作性强。
在当代政治和军事条件下,人员伤亡数量作为战争判据越来越不合时宜。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占据绝对军事优势的西方联军在战争主要军事行动期间伤亡甚小,利比亚战争中更是零伤亡。可以设想,如果未来军事强国之间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武装冲突将是短时和高烈度的,这类武装冲突会造成高科技武器的大量损耗和惨重的财富损失,但由于参战各方都具有较高的技战术水平,因此可以给平民和民用目标带来很少的附带杀伤,且参战各方伤亡人数不会很大,但无疑,这类武装冲突必然属于战争。
二、预测未来战争
战争是“铁与血”的政治。战争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克劳塞维茨用所谓的“迷雾”来形象地比喻,最为恰当不过,也正因如此,对未来战争样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预测的科学。
“预测和描绘未来战争”这一重大问题,各国都在进行研究。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将如何爆发、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未来战争与“现在战争”和“过去战争”有哪些异同?未来战争会造成那些新的伤害?随着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和争端越来越普遍,未来,国家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是否会减少甚至消失?
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但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尤其在政治、外交、军事这类最为复杂、难以预测和对国家最重要的领域。人们总是习惯基于对过去和现在的认识来预测未来,但基于对“过去战争”和“现在战争”的认识来预测未来战争,在充满着高度不确定和碎片化的当今和未来,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近些年来进行的几场局部战争表明,军事领域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战争和武装冲突表现出愈发强烈的难以预测性、不确定性的特征。人们相信,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将具备新的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过去战争”和“现在战争”对于预测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不具有意义;相反,历史和现实总是作为思考未来的起点,而非终点。
目的决定形式。发动战争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战争进行的样式,而战争进行的样式又服务于发动战争的目的。因此,研究未来战争样式,首先需要明确“人类未来面临的安全环境”;其次,需要明确“未来人类为何而战”。
三、界定战争
既然战争是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信息、生态等所有人类活动领域斗争的综合和统一,且以是否达成政治目标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指标,那么战争就应不仅仅表现为使用武器进行武装斗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否也可以“不流血”?
人类历史上,尚未出现过使用非军事斗争形式进行的战争。即使是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期间,美苏也是通过其代理人,直接支持或间接参加了多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这些“热战”,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国家间的武装冲突是战争的传统和普遍形式,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但是对于国内战争,即“内战”,是否必然被界定为“战争”,却存有争议。内战是在一国之内进行的武装冲突,传统国际法认为,只有在交战中的一方被本国政府或其他国家承认为交战团体或叛乱团体时,内战才能称为“战争”,并适用战争法的相关原则和条款。
现代国际法对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1977年6月8日在日内瓦签订的《1949年5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I条规定,即使为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在缔约国一方领土上的武装部队如果对缔约国的部分领土行使了控制权,从而使其能够进行持久和有组织的军事行动,也应当适用关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可见,内战只要发展到一定规模且持续较长时间,也应被界定为“战争”。
目前,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等组织在多个国家猖獗,如“基地”组织、ISIS等,大量实施恐怖活动,并呈现国际蔓延态势。这些组织被所在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作为打击对象,实际上,相当于承认其作为交战团体或叛乱团体。
由于这些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具有国际性,没有国家认为与这些组织的武装斗争是“内战”,只是将其作为非国家性质的暴力政治运动。《日内瓦公约》只有国家才能加入,这些组织没有加入《日内瓦公约》,未来也不可能会加入,不适用于国与国之间达成的《日内瓦公约》,因此,这些组织的参战人员不代表任何国家。
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分子在战斗时未穿着带有明显标志的军服,这样在发动袭击后,可方便混入平民中逃逸,且其袭击目标多为平民,手段残忍血腥,不能作为合法的参战人员。这些组织的被俘获人员即使可以受到人道主义待遇,但却不符合“战俘”的界定标准,因此不能享受《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战俘”待遇。对待这些组织的被俘人员,在羁押、审讯、审判等多个环节,许多国家的国内法律还存在着空白之处。为此,美国将反恐战争中抓获的俘虏关押在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监狱,这样,他们既处于美国管理之下,同时又不位于美国本土,从而可以规避一些美国国内法律上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传统西方强国受到战争的极大削弱,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运动,相伴随地,主权国家数量大幅增长。这些民族独立运动大多数是各国人民反抗殖民国家的武装斗争。传统国际法不承认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的武装斗争为战争。现代国际法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上民族自决的基本原则,承认民族自决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合法性。《附加议定书》第I条第四款规定,各国人民在民族自决运动中,对殖民统治、外国占领以及对种族主义政权作战的武装冲突也视为战争,并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可见,战争不仅包括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也包括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战争不仅是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一定条件下的内战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属于战争。
诚然,国际法尚且无法禁止和杜绝战争,但它对战争的约束和限制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未来,国际武装冲突方面的法律、法规、条约、公约、协定等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四、从国际法角度看战争
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是一种法律状态,要求战争除了具有“大规模、长时间的武装冲突”事实外,还需要交战各方的交战意向表示。
所谓“交战意向”,是指交战各方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武装冲突明确认定是战争的一种表示。交战意向一般通过发布宣战声明或递交最后通牒来明确表示。只有具备交战意向,才能构成战争的法律状态。一般来讲,如果交战的一方或双方宣战,或者非交战国宣布中立,就意味着进入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状态,同时意味着交战方和平关系结束,并自此时刻起,战争法和中立法开始适用,并据此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
实际上,只存在武装冲突的事实而未经宣战的战争并不鲜见。如果武装冲突侵犯了非交战国的利益或严重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那么非交战国和其他国际法主体的反应对于确定战争状态也具有重要的判定价值。交战各方对宣告中立的非交战国和其他国际法主体应当服从战争法的约束,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根据传统国际法的规定,战争必须经过“宣战”这一程序。1907年《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第I条规定,除非有预先的明确无误的警告,否则,国家之间不应开始敌对行为。采取的警告形式,可以是发布战争理由的宣战声明,或者是递交有条件宣战的最后通牒。
战争实践中更常见的,是国家为在战争伊始就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保证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和隐蔽性,往往先发制人,宣战行为常常滞后于军事行动,或者是不宣而战。1942年日本偷袭珍珠港,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都是未经宣战而进行的战争。
现代国际法中,“战争”与“武装冲突”这两个概念并存,二者密切相关。武装冲突是构成战争的前提条件,战争必然包括武装冲突,但并非一切武装冲突都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例如,如果武装冲突只是一般性的敌对行动,冲突各方不认为是他们之间和平状态的结束,且这种武装冲突是小规模、在短时间内进行的,冲突目的只是使对方屈服,从而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则属于一般性的武装冲突,而不应视作战争。这种类型的武装冲突在当前很常见,未来也将频发,冲突各方都保持了很好的克制。
如果冲突各方进行对抗行动的目的已经超过一般性的要求和条件,且冲突各方都认为和平状态已经结束,进入战争状态,且发生了大规模、持续长时间、涉及范围较广的武装冲突,则这种武装冲突就可视作战争,也是历史上发生次数最多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
随着军事科技的迅猛发展,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破坏力急剧增大,对抗强度不断提高,战争的持续时间呈现“缩短”的趋势。可以预测,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将是短时、高烈度的。
五、战争中的新出现因素
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法主体(主要是国家)之间,为击败对方并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而进行的武装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状态。
传统国际法上,只将国家间的战争被视作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并认为战争应当具有相当规模和范围,且要持续一定时间,偶然发生、地方性、短暂的边界冲突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现代国际法在战争主体范围上有所扩大,某些在传统国际法上不被认为是战争的武装冲突也进入到了现代国际法领域。
“9·11”恐怖袭击震惊世界,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被美国界定为“反恐战争”,同时作为前所未有的一种战争模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反恐战争彻底颠覆了人类对战争的定义和认识,并对战争样式的演变和国家军事力量建设带来了深远影响。
恐怖主义组织不是国家,没有主权、领土、政府和人民,由于不具备国家的特征,自然也不具备传统国家那样的弱点。实际上,恐怖主义组织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也因此不惧怕威胁。恐怖主义组织的分布呈现网络化,活动具有全球性,组织和指挥体系高度扁平化,发动袭击的时间、地点、规模、方式等难以预测,且往往无先例可循,但却可以对美国这样的军事和经济超级大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基于传统安全理念的国家在应对恐怖威胁时往往束手无策,军队的组织、指挥、训练、装备也在打击恐怖主义组织时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目前,各国都在对打击恐怖主义开展大力研究,并将其作为武装力量的主要任务。为适应和满足打击恐怖主义的要求,军队需要在组织、指挥、训练、装备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打击恐怖主义,首先需要将恐怖主义组织明确为交战对象。反恐战争中,战争主体分别是国家和恐怖主义组织,这就决定了反恐战争与传统战争有着显著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战争主体中,出现了非国家性质的武装组织、团体甚至个人,且由于对抗双方或多方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实力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状况,因此,“不对称”作战成为反恐战争的首要和基本特征。
随着新技术、新利益、新矛盾、新组织的出现,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主体及其进行样式也将发生变化。因此,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内涵、外延也需要重新加以定义。
至2050年的未来中长期内,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等领域将会发生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相应地,这将使得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在动因、主体、涉及领域、分布地域、进行样式、解决方式等方面,会与“现在战争”和“过去战争”具有较大区别,将具有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