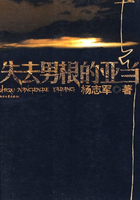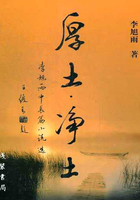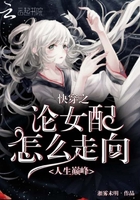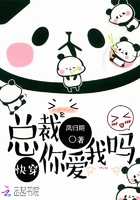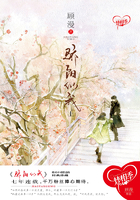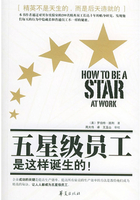多多手臂上的烫伤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愈合了,只是留在手臂上隐约可见的疤痕永久记录下了曾经发生的一幕。那疤痕红红的、鼓鼓的,像是一只还未蜕化的蝶蛹,只是不会动。然而,将多多送人这件事对多多内心造成的伤害,比起手臂上的外伤来要严重得多。
也许,多多还不懂得内心受的是什么伤,但有个事实毕竟存在,那就是她知道父母并不喜欢自己。她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不把姐姐换给别人,而要换自己呢?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要自己?她心里有很多的疑问,但却不知道怎样去找到答案。她开始封闭起自己小小的内心世界,常常一个人坐在屋后的树下发呆。虽然有时,她还会去找同龄的小朋友去耍,或者到河里去捉小鱼,但她已不再依恋父母的怀抱,她甚至不想也不愿意投入父母的怀抱,她的心与父母之间有了明显的距离。
接连几天,多多都没喊过爸爸妈妈,她对任何人都不喊。切饭的时候喊她就切,不喊她,就呆呆在一个角落坐下,或站着。即使有和她说话的人,她也爱理不理。
陈建川看着原本活蹦乱跳的多多,突然间变得不爱说话了,他几次试着把她抱在怀里,都被挣扎着,逃出了怀抱。
这天晚上,陈建川躺在床上对坐在床沿上给红琼和多多补衣服的杨召珍说:“咱们以后别想把多多换人了,我去过贾林青家,他们家孩子多,多多去了,可能饭都切不上。”
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要说杨召珍真狠心将多多送人,其实内心也是很难过的。
现在,只要睁开眼睛,看着多多,她的内心就充满了愧疚。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多多。很多次,也试着和多多说话,尽量将好吃的给多多,但多多都不领情,常常是不开腔不出气地走到一边。
本来就性情暴躁的杨召珍忍不住怒声呵斥多多,但呵斥的结果,往往是多多对母亲更加反感,弄得杨召珍也无可奈何。
杨召珍仔细地做着针线活,说:“不要再提换多多的事情了,想到这事,我就不舒服。多多经过换她的事情后,整个人都变了,与我们也不亲了。想到贾林青看多多烫伤后,一点表情都没有,我的心就冷了,说啥子也不再换自己的娃儿了。”
陈建川责怪道:“当初还不是你找的事情,你这叫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不说,还让自己的娃儿受伤。”
“哪个早晓得哇。事情都出现了,就只能这样。以后,我们加倍爱她还不行吗?赎罪吧,娃儿就是父母欠的债。”
按照规定,凡是年满七岁的孩子都应接受教育。由于农村学校条件有限,一个班上,同上一个年级的学生,年龄差距基本上会有两到三岁。山东村的孩子父母一方有城镇居民户口的去了福贵镇中心小学,农业户口的去了乡村小学。村里只有陈玲玉能上福贵镇中心小学,因为她的爸爸是军人。
杨召珍看着渐渐长大的红琼,内心里有种满足感,觉得孩子长大了,也应该上学了。自己就因为没读过书,只上了几天识字班,除了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和一到九几个阿拉伯数字外,其他都不认识。为了孩子上学,她早早地给红琼准备了军绿色的书包,还有铅笔、橡皮。
9月1日这天,杨召珍早早起床,做好早饭,喊上红琼起床吃饭。吃饭后给她换上了一套干净衣服,让陈建川带着她去学校报名。那时一个年级一个班,乡村小学共有五个年级,五个班。
到了学校,红琼发现陈梅、陈菊松、陈晓生跟她是一个班。
第一天背着书包上学的红琼,对读书的热情并没有她的母亲高。她甚至还不太想上学,还是被哄着去的,母亲告诉她,读书有多少好处,还有很多的细娃儿和她一起耍。
红琼到了学校才知道,上课不能讲话,要坐端正,要听老师讲课,还要写字,放学后,要做家庭作业。这突然的变化,让她有些适应不过来。往往是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她在下面不是打瞌睡就是用颜色笔涂书本上的图片,有一次还被老师罚站过,也挨打过手板。
多多看着红琼每天放学回家后就坐在凳子上,趴在桌子上做家庭作业,但她好像并没有认真做,而是东张西望,有时还给多多做个鬼脸。好奇的多多就凑过去,不是问她这歪(这个),就是问那歪(那个)。
一天,在红琼做作业的时候,多多又凑过去,被杨召珍发现了,大声吼道:“你姐姐在学习,你滚到一边去!”
多多看了看母亲,母亲的眼里都是凶光。她害怕了,胆怯地走到了一边。她看到红琼书上有五颜六色的图片,有些弯弯拐拐的东西,非常神秘。她有些羡慕。偶尔,红琼也会大声地读着:b、p、m、f……她就悄声地学读着b、p、m、f……
多多去找陈秀兰耍,陈秀兰不在家,陈玲玉在做作业。她又去晓生家、陈梅家、陈菊松家,见他们每个人都在做作业。她走了一圈,也没找到一个玩伴,于是自个在地上玩起了稀泥巴。
多多将泥土和上水,像揉面一样来回地揉着,和出的稀泥比她的手掌还大。她一会做成碗,一会做成杯子,一会做成汽车,一会做成小人,想到啥子做啥子。有时还将做好的碗里吐上口水,然后扔在地上,就能发出“砰”的声音。
她自个在地上玩着,正当她玩得高兴的时候,陈建忠担着水桶说:“多多,你还在这里耍稀泥巴,你妈来了,快回去。”
多多看见妈妈手里拿着一根竹条子,向自己跑来。她赶紧将稀泥巴甩掉。说时迟那时快,竹条子一下下落在了多多的手上和身上。
杨召珍看着多多那身泥土衣服,浑身都是气。她拽着多多一边打,一边骂着:“你个挨刀的,朗开这么不听话,衣服我不难得洗嗦。”
陈建忠放下水桶,上前拉了起来,说:“细娃儿就是在地上滚大的。”
杨召珍并没解气,说:“给老子回去在地上跪倒。”
多多回家跪在了院子的地坝里。陈建川看着她,上前把她拉起来,多多挣扎着不说话,也不起来,只是眼泪在眼角打转。也许,在她心里,即使跪下,不要面对妈妈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陈建川说:“孩子她妈,她又啥子了吗?你又打她。”
“你看看,今天才换的衣服,又弄脏了。”
“你给孩子说服教育嘛。”
陈建川说着又去拉多多,要把她抱起来。多多仍然不说话,挣扎着不起来。
杨召珍说:“别管她,她要跪,就让她跪吧,你去煮夜饭,我去打扫猪圈里的卫生。”
陈建川转身进屋做饭去了,杨召珍进了旁边的猪圈屋,院子里只剩下多多一个弱小的身影,她双膝跪在地上,目光呆滞地望着灰暗的天空。
第二天早上,陈建川发现多多身上起了许多凸起的小红点。凭着以前的经验,他想,是不是在出水痘。
陈建川赶紧去猪圈屋喊正在喂猪的杨召珍。杨召珍赶紧跟着陈建川进屋看多多。可能是因为瘙痒,多多坐在床上在用手抓。杨召珍看了看多多的手上,又仔细地看了看她的脸,接着又捞起多多的衣服看了看,说:“就是出水痘。”
陈建川说:“那朗开弄?”
“你去问陈三虎,给她开点药,出水痘至少要一个多星期。”
星期六的下午,放学回家的红琼第一件事就是做作业。当她把作业做完后,在地里干完活的母亲也回来了。她说:“红琼,赶紧去烧火煮饭吧。”
红琼说:“要得。”
灶屋里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线。红琼在灶台上摸着火柴,她划了一根,然后将煤油灯点上。煤油灯是用一个小的墨水瓶做的,非常简单,就是在墨水瓶里放上些煤油,然后用草纸做一个细小的灯芯,浸湿就可以。
紧跟着杨召珍也来到灶屋,说:“红琼,你先把这铁锅洗了,我去看看你妹妹醒了没有,都困了一个下午了。晚上我们炕(烘)面皮来切(吃)。”
杨召珍喊着:“多多,多多。”
多多睡得很死。
她伸手摸了摸多多。多多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发出甜甜的鼾声。陈建川到家的时候,杨召珍和红琼已经将夜饭弄好了。
陈建川问:“多多呢?”
红琼说:“妹妹还在困瞌睡。”
陈建川说:“哦,得把她喊醒,困了一个下午了。”
说着陈建川也去喊多多。
“多多,多多,醒醒,该切饭了。”陈建川摇晃着多多。
多多睁开眼睛,陈建川把她抱了起来。多多身上的小红点变成了小水泡。因为出水痘,接连几天都被关在黑暗的屋子里。每天除了切饭就是困瞌睡。
唯独星期三那天,红琼上半天课,她在家照顾着多多,还给多多做了吃的,当然,在多多的要求下,偷偷地放她去外面玩了一会儿,赶在父母回家之前回家的。
陈建川问:“肚子饿了没有?”
多多揉着眼睛,摇了摇头,然后用手要去抓脸上的水泡。
陈建川赶紧拉住她的手说:“不能抓,抓了脸上就不好看,就是麻子。”
多多似懂非懂。
陈建川抱着多多到桌子上切饭时,陈建安从街上回来了,他没进自己的屋子,而是直接进了陈建川的家。他自个在桌子旁坐了下来。接着从兜里掏出了两个麻花,分别给了多多和红琼。
杨召珍知道他肯定没切饭,说:“去拿碗筷来,我们一起切。”
陈建川说:“你今天又在街上打牌吗?少打点,你也二十出头的人了,得成个家。”
“我晓得。”
“给你说,你就晓得,一年一年混起快哟,把年龄混大了,成家就困难。”杨召珍说。
陈建安还没成家,一直是杨召珍的心病。看着陈建良成家后,都有两个孩子了,陈建安还是一个人,让她放心不下。
“我朗开不想成家吗?没得女的跟我,也没人给我说媒。”
他们说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隔壁传来了争吵声、哭声、骂声、打斗声。
杨召珍放下碗筷走出屋。陈建川也跟着出来了,只有陈建安和多多、红琼还在桌子边切饭。
赵月华抓住陈建良的衣领,又骂又抓,流着眼泪,嘴里不停地骂着:“你个龟儿子,有本事就把老子打死,老子不活了。”
陈建良抓住她的头发,用脚踢着,嘴里也骂着:“你个死婆娘,朗开不讲道理?老子输了钱,你就跟我闹,骂老子;赢了钱,给你就安逸。”
“你整天活不干,就知道在牌桌上坐起。当初瞎眼了,嫁给你这个挨刀的。”赵月华越骂越激动。
陈建良“唉呦”叫了一声,推开赵月华,说:“你有本事再嫁呀?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不是我,看你嫁得出去不?”
“哼,不要脸的,去你妈的!”
“死婆娘,你给我住嘴!”
陈建良又一把拧住赵月华的头发,把她按在地上撞,那架势吓得一旁的两个女孩子哇哇大哭。大孩子兰花已经两岁了,比小孩子桂花大一岁,她们看着父母打架,只是一个劲地哭。
陈建川和杨召珍一个拉着陈建良,一个拉着赵月华,劝了这个劝那个。
陈建川拉开陈建良进了自己的屋子,陈建安看着他说:“你球莫名堂,天天就知道吵!”
陈建良没好气地说:“你懂个球。”
陈建川喊着陈建安,“你就少说一句要得不!”
陈建良坐在陈建安对面的板凳上,见桌子上的盆子里还有吃的,拿起桌上的空碗舀起吃起来。
陈建川看着他说:“你也该懂事了,都两个娃儿了,整天就知道在茶馆打牌,能靠得住吗?赌博赌博,越赌越薄,我就没看见哪个靠赌博发家的。”
陈建良说:“我前段时间手气好,赢了不少钱,这两天手气臭,才输了钱。”
“你现在手里又有几个钱?赢了都还好,要是输光了,一家大小切啥子?”
“我就收活路后,打哈牌,又啥子?”
“你呀,赶紧切饭,切饭后,赶紧去弄娃儿。”
陈建良说:“老子才不管,让她妈管。”
此时,杨召珍抱着桂花,一边劝赵月华,一边给兰花说:“喊妈妈别哭了。”
兰花扑在妈妈怀里,说:“妈妈,不哭了。”
赵月华搂着兰花,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嫂子,你说他是不是个人,整天在外只晓得打牌。”
杨召珍说:“我知道知道,你先别哭了,都这么晚了,赶紧起来,别坐在地上,你看在娃娃的份儿上。”
杨召珍一手去拉赵月华起来,好说好歹,赵月华才起来拉着兰花进了屋。
安顿好红琼和多多睡觉后,杨召珍才洗脸洗脚上床休息,这一天也才算结束。
陈建川把煤油灯吹熄了,整个屋子里黑漆漆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他比杨召珍先上床休息了一会儿。
杨召珍侧着身子躺在陈建川身边,她说:“今晚这顿饭都没切昌盛,陈建良两口子总是吵吵闹闹的。”
“他们是那性格,有啥法?”
“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我实在不想跟她们住在一起了。再说,我们的住房太窄了,是不是也去村上申请批几分宅基地修几间房子?”
“我们现在哪有钱修房子?”
“去借钱。”
“哪里借?修房子不是笔小数目,我看等以后再说。”
“你也不动脑筋,孩子一天天大了,陈建良也两个孩子了,陈建安遇到合适的也得成个家,就我们现在这房子,朗开住人?我们是老大,先修房搬出去,把这房子让给他们兄弟一人一半,也就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再说了,住在这里也憋屈。”
“怎么憋屈了?”
“你看我们院子前面,陈建强加修了一间猪圈把我们的房子都挡完了不说,还把我们过上过下的路都封了。”
陈建川在一旁默不吱声地听着。陈建强加修猪圈时,陈建川主动找过他协商,希望挪动一点,别挡住他家的房屋。但陈建强好像是有意要那样干,不光超面积加修了猪圈,还把陈建川他们过上过下的一条路给封了。
为了那条路,陈建强与陈建川两家有了一次激烈的争吵,甚至找来了村里的领导调解,但由于陈建川家势单力薄,领导的调解还是有偏向的,最后没有改变结局,陈建川他们只得另外绕道走其他的路。因为那条路,也导致了两家心理的隔阂。
杨召珍继续说:“我都看好一块地,在那里修房子,屋基肯定好,而且那地我还找风水先生看了。”
“你哪个时候找人看的?我朗开不晓得?”
“你,家里啥事你操心过?”
“人家说啥了?”陈建川来了兴趣,赶紧问道。
“说那屋基很好,朝向也好,不但家业兴旺,后人也有发展。那块地就是我们的菜园地。”
提到菜园地,陈建川实在是清楚不过了。那是去年底才分得的。1982年1月1日,党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1983年又下发文件,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之后,全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每一个家庭都得到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使用权,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种多少就种多少,谁也管不着,农民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农民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失去了人身自由,农民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没有自由选择耕种的权利,也没有离开土地的权利。假如谁要想干点小买卖,那就要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被批斗。而陈建川所在的村是在1981年年底实行的这一新政策。
陈建川说:“农村的宅基地要经过村上批,按照人头批,这事好不好弄?”
“事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不相信,村上不给我们批,过几天我就找村上。就是不批,我也要修房子,那地是我们家的地。”
陈建川问:“钱从哪来?”
杨召珍说:“信用社贷款。头场赶场,我在街上碰见你在信用社工作的同学贾辉了,他问起我们的情况,我说想贷点款修建两间土墙房子,就是没担保人。他问需要多少,我说三百块钱。”
贾辉是陈建川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同学。陈建川上三年级时,父亲生病去世,作为家里的长子,也算是家庭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不得不辍学回家,帮着母亲干农活。贾辉却很幸运地一直念到高中毕业,毕业后,进了信用社工作。
陈建川说:“既然这样,我明天去信用社,先把钱准备起。”
夫妻俩越说越兴奋,完全没了睡意,好像他们所想的房子马上就要修建起来,似乎马上就能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了。
杨召珍接着又说:“只要我们夫妻同心,黄土也能变金。等把这房子修好了,我们再想办法,弄点其他东西来做,争取多挣点钱。庄稼人,虽说守点庄稼饿不死人,但除去成本也剩不了啥子。”
“那是,一步一步地来,日子总会过得越来越好的。”
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摆着龙门阵,直到外面响起了雄鸡报晓的啼叫声,才觉得时间不早了,催促着彼此,赶紧睡觉。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乡村小路蜿蜒曲折,漫无尽头。陈建川头上戴着斗笠,肩上披着蓑衣,脚上穿着破了几个洞的水鞋行走在乡间的泥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他的步伐迈得极大,他要赶紧去街上的农村信用社找贾辉贷款。
大街上,行人不少。有的站在街沿上卖起了鸡蛋、茶叶、食盐等生活用品,街上出现了少有的热闹。
这种场面是随着国家政策对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出现的。1981年7月7日,国务院文件里有句大实话:个体户也是劳动者。但是个体户也被限制在拾遗补缺的范围:“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应允许雇少量帮工和学徒。”少量指的是七人,超过这个数字,就成了资本家。那时,资本家就是剥削者的代名词,因此,并不好听,也是不允许的。而那时的个体户是专授予城里人的名称,农村人望“城”莫及。直到1982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胆量大的村民,开始尝试着做点小买卖,更多还是将自己家产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交换,卖点鸡蛋换点油盐肥皂之类的生活用品。
还没到上班时间,陈建川赶到那里时,信用社的大门紧闭着,他趴在门上,向门缝里张望,里面亮着灯光,隐隐约约能看见里面有人说话。
突然有人站到了陈建川的身边,问:“陈建川,你这么早就来了?”来人是他村的陈作然。
陈建川说:“早点来,今天当场人多。”
陈作然还不到五十岁,却已是满头白发了。由于过度抽烟,一嘴的牙子焦黄。他的个头不高,顶多一米五左右。他把披在自己肩上的蓑衣取了下来,拿在左手上,说:“这个雨昨晚下到现在,都还不停,气温越来越低了。”
陈建川说:“啥时候了,再不冷?现在是数九了,转眼就要过年了。”
陈作然说:“是啊,时间过得就是快,你家年货都准备了吧?”
“准备啥哟。”
信用社的门嘎的一声开了。陈建川往里面望了望,没见着贾辉的身影。他对陈作然说:“你先办理吧。”
陈作然站到柜台前,从自己裤腰里掏出一个小布袋子,再打开布袋子,把里面叠成一个卷的钱掏出来。这些钱里面,只有一张最大面值的十元人民币,其他都是五元、两元、一元的。他数了又数,整整数了三遍,才把钱递进去,交给柜台里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问他存多少钱?他说一百。
陈作然家的经济状况相比陈建川家要好得多。陈作然带着两个已经结婚生子的儿子陈武、陈海在村里干起了烧砖的买卖。父子三人合伙打窑洞,烧砖瓦。
陈建川站到了信用社的街沿边,他来回地走动着,不时将脑袋伸长,望着信用社的柜台里。他几次想问柜台里的工作人员,贾辉来了没有,但却没有那个勇气。他有些胆怯,也有些腼腆。他不喜欢求人,也不喜欢麻烦人。早上他本来是想让杨召珍来贷款的,杨召珍说她不识字。他想拒绝,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杨召珍说他的脸是床单包的,怕见人。
陈建川怀着不安的心情来回在信用社门前徘徊,虽说只是向信用社贷款,但多少有些难以启齿,特别是在自己同学面前。这世道,没有担保人,款贷不了。
“陈建川!陈建川!”突然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陈建川向后望了望,是贾辉。贾辉穿戴整齐,左手撑着雨伞,右手拿着一个公文包出现在他身后。
贾辉说:“来了有一会了吧?”
陈建川说:“刚来一会。”
贾辉知道陈建川的来意,说:“你爱人都把事情给我说了,我这就给你办。”
陈建川说:“麻烦你了,老同学。”
“客气话就别说了。”贾辉走在前面,陈建川跟着他进了信用社。
不到十分钟的工夫,陈建川贷款的事情就搞定了,拿到贷款来的三百元钱,陈建川连连给贾辉说了好几声谢谢、麻烦了之类的话。
离开信用社,陈建川没有立即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农贸市场。农贸市场的西南角有个专卖牲畜的地方,卖猪、卖牛、卖羊就在那里。他要去那里看看行情。家里的母猪产了十头小猪,还有一天就满月了,他要去看看现在的小猪行情,估计着能卖多少钱。两天前,他碰见了兽医站的兽医,让过两天给他家的小猪骟了。
农贸市场的景象非常壮观,人们在人潮中涌动,说话声、叫卖声、猪叫声、羊叫声,人与畜的声音交替着,声声入耳。陈建川艰难地在人潮中挪步,一只手却紧紧抓住裤子口袋,生怕贼娃子将自己贷款的钱给偷走。
好不容易挤到了卖小猪的地方,陈建川东看看,西瞧瞧,一会问这猪朗开卖的,一会又问那猪朗开卖的。陈建川只是问价格,却不给人回价,人家觉得他没买猪的诚意,也就不搭理他。
整个猪市转了一圈下来,陈建川心里多少有些底了。他便准备回家,但他刚走出农贸市场门口,意外碰见蔡家村自己三爹的儿媳妇王丽芬。
陈建川的爷爷生了十二个孩子,八个男孩,四个女孩。成年后,八个男孩成家了,搬离了祖屋,分散在其他乡镇,有的则当了上门女婿,去了别人家。四个女孩也嫁入他乡,唯独就陈建川的父亲守着祖屋。离陈建川家最近的也就是蔡家村他三爹陈来贵了。
陈来贵已故多年,生前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大儿子不到十岁夭折了,二女儿陈建珍嫁到了黄泥,一年后,随在大庆当石油钻井工人的丈夫移居到那里。三女儿陈建红没有文化,有点憨,有点笨,家人到处托人想把她嫁出去,最后嫁到了永兴覃姓人家。覃家兄弟姊妹多,家庭条件差,覃家三个儿子娶个老婆都不容易,所以当媒人把陈建红介绍给覃海涛时,也就同意了。
覃海涛婚后一年去了部队当兵。在部队上,他踏实、努力、上进,获得了不少殊荣。1972年,根据家属随军政策,全家到了部队。1973年,陈建川与杨召珍结婚时,他们参加了婚礼。1980年,覃海涛转业到了地方彭州市,任某局的局长。
陈来贵的幺儿子陈建行体弱多病,本以为这辈子讨不上老婆了,哪知经人介绍,遇上了成分不好的王丽芬,于是成就了这门婚事。
陈建行与王丽芬结婚后,很快就有了长子陈晓,次女陈落梅。应该说在农村有儿有女是最幸福的事情了,但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发现老大是先天性近视眼,而且近视的度数非常高。夫妻俩担心陈晓不能干农活,于是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陈达,是个健康的男孩,也如他们所愿了。
然而好景不长,陈建行由于长期操劳,本就不好的身体更加雪上加霜,意外检查出得了肺结核,从此丧失了劳动力,一家的重担落到了王丽芬身上。好在王丽芬一家与陈建川一家走得近,遇上农活,就得靠陈建川兄弟三人去帮忙。
陈建川看着嫂子王丽芬在农贸市场大门口与一堆人围着,便问她:“嫂子,你在这干啥子?”
王丽芬说:“我上街来买斤盐巴,老弟,你也在赶场呀?”
“是啊,建行哥身体怎样?”
“药罐子,一年四季不断。”
“孩子们都好吧。”
王丽芬说好后,然后又给陈建川说了一堆有关她家孩子的具体事情。
说陈晓和陈达学习成绩都还可以,希望他们以后能考上大学,这样就可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说陈落梅在一个星期前收到在彭州市的三姑父覃海涛的来信后,第三天就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去了他那里。
王丽芬还说,陈落梅到了她姑妈家,姑父说给她找点事情做,在那里待着,以后就在那里处理个人问题,哪怕找个菜蔬队的也比回老家种地强。
弟嫂拉了好一会儿家常话,陈建川也告诉了王丽芬他家要修房子的事情。王丽芬一个劲说是好事,只是有些愧疚地说,兄弟,你看嘛,我家陈建行这个病号,不能来给你帮两天忙,对不住!
“你个短嘴巴,你死到哪儿去了,大上午办屁那点事情都没办完,现在都啥时候了?”陈建川刚走到自家院子的地坝边,杨召珍站在街沿门口的骂声就迎了上来。
陈建川脾性很好,再怎么骂,都是笑脸相迎,这让杨召珍心头更气。
杨召珍能不生气吗?早上切过饭,冒着雨在地头干活,眼看中午时间快到了,就得收工回家,给在读书的红琼煮饭吃,免得上学迟到。饭煮好后,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陈建川的影子,问了过路的一个又一个人,都说没看见他。难不成是贷款没办下来,没办下来早该回家了。如果办成了,这整个上午躲到哪个犄角旮旯了,是不是把贷款的钱搞丢了?想到这些,杨召珍非常不安。她甚至让红琼去街上找了一趟。
现在看见陈建川回家了,她的气就来了,骂声也随自己心头的火气膨胀起来。
陈建川笑着说:“孩子他妈,火气小点要得不,你这声音像高音喇叭,生怕乡里乡亲听不到你的声音呀。”
“你安逸哟,出去就是一个上午。”杨召珍没好气地说。
“我也没耍,贷款办好了,我去农贸市场看了下猪价。”说着陈建川就将贷款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交给杨召珍。
杨召珍认真地点着钱。一旁的陈建川一边看她点钱,一边说:“今天我碰到王丽芬嫂子了,她说她家陈落梅去了彭州市覃海涛哥哥那里了。”
“估计以后要在那里安家。”
“听嫂子说,覃大哥要给她安排个工作。”
“听说他当大官了,不晓得以后能不能帮我们两个娃儿一下。”
“到时找到他帮个忙,可能会帮的,你看,我们结婚,没请他们,他们晓得后,都来了。”
“那得看以后了,毕竟从那以后就没走动,人不走不亲,水不搅动不混。话说回来,他那么远,也走不去的。”
陈建川突然想到了孩子,说:“红琼上学去了吗?”
“不上学,等你呀。”
陈建川又问:“多多呢?”
“不晓得,她长了脚的,我也不能随时背在背上。”
杨召珍说完转身进屋,将钱藏在一个墙壁的旮旯里。杨召珍有个习惯,家里有点钱,不是放在箱子柜子里,而是塞在斜房屋里的泥巴墙壁缝里。而她放钱的时候,正好被在另一个角落里找蝈蝈的多多撞见,多多不声不响地躲在角落,她睁大一双明亮的眼睛,清楚地看着杨召珍放钱的地方。
等杨召珍放好钱走后,多多窜着跑了过去,她仔细地找了起来,一下子就找到了一个塑料袋子装的东西,她用小手将它掏了出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钱。
多多看了看钱,摸了又摸,她想拿一点。她一次次拿了一张钱,又一次次地放进去,接连重复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完璧归赵地将钱放回了原处。
多多像发现了什么大秘密似的,脚步跳得轻盈而有活力,而这个秘密似乎天下就她一个人知道,但她也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她朝屋里走了回来,眼睛还不时向那处望去。
多多突然从屋子里冒出来,让杨召珍有些吃惊。她问:“多多,你刚才在哪里?看见什么东西没有?”杨召珍担心多多发现她藏钱的事情。
多多说:“没有。”
杨召珍说:“你刚才在哪里耍的?”
多多指了指灶屋,说:“那哈。”
杨召珍又问:“没扯谎吗?”
多多摇了摇头。
陈建川端着饭碗在桌边吃饭。他觉得杨召珍有些奇怪,问:“你把孩子审犯人似的干啥?”
“你切球你的饭,这儿没你的事。”说完,杨召珍就转身进里屋,看了看刚才放的钱,发现钱还在那里,她的心才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