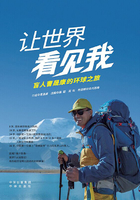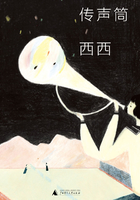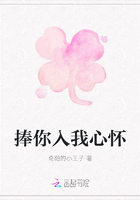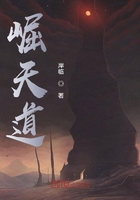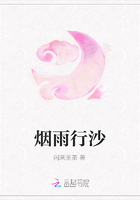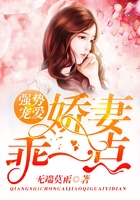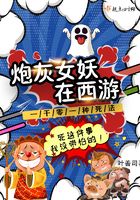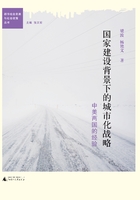我的母校在和畅堂,那是心中的圣殿。
可是,当时的校园何其简陋。刚从攒宫农场迁入和畅堂的所谓鲁迅故乡唯一的一所高校,有校无园,不成规模,还不如一些中专、技校布局合理,井然有序。在秋瑾故居附近,那浅浅的池塘边上,矗立着一幢新建的主楼五层、两翼四层的大楼,这便是校园的全部。没有设施完善的食堂,买菜打饭后须带回拥挤的宿舍;没有体育运动场地,出操和上体育课须走进附中小小的操场;没有热水和电扇,也没电视机,我们里外三层站在外语系教室的课桌上,伸长脖子,饶有兴味地观看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已是我们的至美享受。
就是这样的一所看似名不副实的学校,却让我念念不忘,许多旧事,记忆犹新。
忆和畅堂,最忆老师的不倦教诲和睿智哲思。有时,老师们刻意为之或随意而发的话语,让学生终生铭记,成为人生导向。当时教师紧缺,工作清苦,地位低下,学校谆谆教导学生要立志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学教师。在新生报到后的第一天,谢德铣老师笑容可掬地发表着训词:“你们刚刚进入校门,入学分数都差不多,但到了毕业时候,优秀的学生可以成为落后学生的老师,关键是看平时努力的程度。”说者娓娓道来,听者震耳发聩。在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大会上,时任副市长的陈祖楠手持一张卡片回校作报告,在一番铺垫之后,他突然提高嗓门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事业,每一个在一百步以外,就要向他脱帽致意……”台下所有学生都面露惊愕之色,以为不太可信。陈老师接着朗声说:“这不是我说的,是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的!”顿时,全场掌声雷动。陈老师在鲁迅研究之外教授教材教法。自担任副市长之后,仍利用星期日或夜间坚持回校上课。上课到最后一节课的最后时刻,他又热情洋溢地说:“教师是教育家,也是艺术家,在教师这一职业上,是大有可为的。”让听者刻骨铭心,给予很大的激励和启迪。在毕业晚会上,一个个任课老师热情地寄语学生如何成材。记忆最深的是年轻的鲍贤伦老师简洁而富有哲思的话语:“你们自小学到大学,见识过许多老师,知道什么样的老师才是最优秀的,心中定有一个优秀老师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你们的努力方向,希望你们个个实现这一心中的理想。”虽寥寥数语,却一直视为人生指南,镌刻在心底。
忆和畅堂,最忆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精深学养。城乡之间教育环境和条件相差悬殊,同学入学成绩相近,但素质有别,来自城镇的学生见多识广,素质优秀,而乡村学生本色自然,更需要启蒙和引导。如城里孩子不需要训练普通话,对农村学生却是难题。吴子慧老师讲授语音课,这位柔美的老师也有铁石的一面。她拎着一台如砖块般的单录机走进教室,让每一位学生录一段《海燕》,然后说毕业前再让每一位同学自己听,比较有否有长进。当时的老师十分珍惜教育的春天,个个心无旁骛,不浮躁、不趋利,潜心研究学问,看重教学效果。当时职称评审恢复不久,学校缺乏教授让我们心存遗憾,而从教学效果和科研成果看,这些讲师都有着教授层次的讲课水准和科研能力。印象较深的是王德林主讲文艺理论文思缜密,李秀实解读字词句功底深厚,邹志方赏析诗词意境引人入胜。袁傲珍、鲍贤伦讲授古代汉语,儒雅而平实的教学风范,使古汉语课化晦涩枯燥为生动活泼。在现代文学课堂上,顾琅川、吴国群学识涵养深厚,年青的蒋益才华横溢,他们或严谨、或潇洒、或奔放的教学风格赢得学生的敬仰。钱茂竹的古代文论,王德林的电影文学和吴国群的教学语言发声原理等选修课也让学生视专业课一样去研读。在老师的引导下,我试着学习训诂学,特意去报考自学考试作为成果检验。考试通过后,袁老师说:真不错。
毕业不久,学校主体部分从和畅堂迁至风则江畔。新老校园虽一箭之遥,却真正告别了有校无园的窘境。学校拥有了现代化的教学楼、图书馆、运动场,呈现出大学校园的宏伟气象。可是,忆母校,还是最忆和畅堂,因为在这里,滥觞于攒宫,勃兴于和畅堂的教育内涵仍在积聚和滋长,办学范式在发扬光大,逐步走向湟湟大观。我边学习,边工作,自以为在中文系的这一段历练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光,见证了中文系的许多经典创意和精彩瞬间,教学、科研和创作高潮迭起,硕果累累,呈现兴旺发达的态势。如顾琅川、邹志方聘请杭州的吴熊和等一批名家担任兼职教授,邀请作家萧军、诗词曲学研究专家万云骏等来校讲学,开展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和研讨活动,让师生大开眼界。沈贻炜、鲍贤伦邀请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毛时安等著名学者作学术报告,精心策划举办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还特意安排考察当时无人问津的鲁迅外婆家——安桥头,令参观者印象深刻。此时期,中文系老师的学术研究成果令人眼目。陈祖楠、谢德铣、王德林、吴国群、陈越从事鲁迅研究形成团队优势,在省内外享有盛誉,成为学校的一大特色和品牌。邹志方的陆游研究,佘德余的张岱研究,顾琅川的周作人研究,吴国群的茅盾研究在各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负有盛名。陈越在光明日报上通栏刊发学术文章,一时引起轰动,学界反响强烈;王松泉以板书学研究独树一帜,享誉中小学教坛;沈贻炜教学、科研和创作硕果颇丰,一部部小说发表和被改编成影视剧,让学生不知有多崇拜,身后紧跟着一大群文学青年;何仲生、王挺和张理明以不同的教学风格将源远流长、绚丽多姿的世界文学园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他们时尚而亲和,或潇洒、或清纯、或超然的风采让学生津津乐道。在鲍贤伦的书法理论和创作引领下,学生学习书法蔚然成风,书法之乡也真正从传统走向现代,开创了一个气象万千的大场面。在与师生的朝夕相处中,结下了深情厚谊,获得了许多老师们关爱和厚护。在心里,许多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老师是我尊敬的长辈,而许多青年才俊更是我的兄弟姐妹。柯岩寻野趣,三山觅诗魂,泛舟古纤道,沉醉五泄湖……一个个好时光都珍藏在心里。所以,特别留恋学校,特别珍惜与老师们相处的朝朝暮暮,牢记着其中的点点滴滴。当从副市长岗位回到学校任校长的陈祖楠老师在校庆十年庆祝大会上,激情澎湃,以诗化的语言描绘了校庆二十年时的美好愿景时,也是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没有想过会离开校园。当与同学一起在校园内栽下一棵棵小树苗之后,以为将伴随它们一起长大,成为参天大树。只是几年后的那个夏日,懵懂地走出了校门。二十年过去,梦牵神绕的常常是这一个精神家园。
忆母校,最忆和畅堂,因为在简陋而清苦的和畅堂期间,与许多老师的朝夕相处之中,让我知道为人处事应真诚坦荡,为人师表;让我知道学无止境,学习应成为一种爱好和习惯;让我知道人格也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大气包容,宁静淡泊。二十年过去,当年栽下的小苗已长成挺拔而伟岸的大树。当年的这些讲师、助教们早已功成名就、业绩非凡,涌现了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和作家、书法家。二十年来,他们的胸襟、视野和气质滋养着我每一个前行的脚印,无论获得成绩还是遇到难题,总是能坦然面对,宁静致远,执着前行。
(写于2015.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