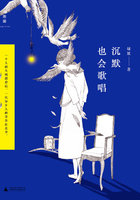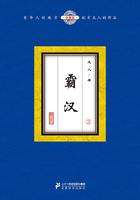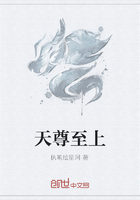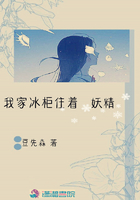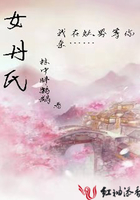那一年,在父母的热望下,我背着行囊离开了家门,来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只以为这只是求学,不会扎根。没想到自此以后,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因为自己留校,更是因为有了一个家,还有一位敬爱的妈妈。
毕业没几年,我遇上了杨子,一个酷爱读书和创作穿着红裙子的神仙般的姑娘。于是,向往杨家也成了一个小小心愿。在一个过大年前的周末,学校虽还没有放假,但也觉得无所事事,于是与杨子相约去作客。我穿上吴子慧老师伴我去百货大楼选来的羽绒衣,斗着胆儿,飞向时时向往着的杨家门。按着杨子告诉的线路,从儿童公园转向马弄,再向右进入一条窄窄的小弄,便是杨子说过的纺车桥河沿了。那一个井台边上的小门,便是杨子的家。
开门的便是杨妈妈,她个儿不高,胖胖的,皮肤白晰,仪态端庄,一脸笑容如春风拂面,温暖袭人。杨妈笑盈盈地招呼着,把我引到里边的客厅去。进门前的忐忑,进入后的紧张情绪即刻消释了一大半。
小门右边是搭建的厨房。那位站在热气弥漫的炉子前,瘦瘦高高,肤色黝黑的长者,是杨爸爸。杨爸手里点着一支烟,见一个陌生小伙进门来,微微一笑,道声“里边坐”便继续忙他手中的活儿。
走进客厅,只见杨妈今天在裹粽子。过年裹粽是一大习俗,体现一种年味,杨家也不例外。看桌上、板凳上放着一大团筐糯米,一迭迭粽箬,还有切成一片片的一大碗瘦肉……看来今天裹粽子的任务并不轻松。
客厅再里边是厨房改装的小书房,掩着门。杨子利用星期天在书房里复习功课,因为马上就是期终考试。听到我进入客厅的声音,书房门开了,杨子走了出来,见她穿得厚厚的,戴着一顶手工编织的线帽,手捧着一个热水袋,朝我莞尔一笑,算是招呼。杨爸端来了一杯茶,杨妈说:“你们到里边去吧。”她自己继续麻利地裹着粽子。
书桌上满是教材和资料,白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名词和数字,足见复习有多用功。我觉得坐在书房里帮不上什么,反而是影响她的复习,可又不甘心刚进来就离开。见客厅里杨妈独自在忙着裹粽子,心想,家里过年时也裹粽子,自己跟着母亲学过几招的。只是家里裹的是“四角粽”,这儿是“横包粽”。母亲说过粽子的形状主要靠控制粽箬的左手掌控,心想自己肯定也可以裹好“横包粽”的。于是,我走向客厅自告奋勇地向杨妈提出要参与裹粽。杨妈开始一脸惊异,转而欣喜:“读书人也会裹粽子?”
我洗净了手,先看杨妈示范,然后自己动手:先折粽箬做成兜形,然后装上浸胀了的糯米并揿得实实的,中间嵌入一条浸过酱油的瘦肉后,合上粽箬。这时候要特别注意粽角的形状,还有表面的光洁度。最后绕上线,打好结。如此,自己首裹的“横包粽”诞生了。杨妈见之喜形于色:“读书人裹粽也象模象样的。”此时,从厨房端水进入客房的杨爸也绽开了笑容,续了茶水后又上厨房去了。
一个人裹粽子变成两个人一齐动手,进度也加快了许多。杨妈打开了话闸子,问长问短的,拉起了家常。杨家的点滴故事,杨子已讲过许多,今天听杨妈妈饶有兴味地聊起来仍觉得十分新鲜、生动。杨妈说她是浙江绍剧团老旦演员,年轻时饰演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个白骨精的母亲,是饰演唐僧的著名演员筱昌顺的徒儿。前几年在《于谦》中饰演太后一角在上海连演二十九场,场场爆满。晋京演出后受到阳翰笙的接见,还有梅兰芳夫人的宴请……这让酷爱戏曲的我肃然起敬:眼前这位围着胸爿正在裹粽的杨妈却是一位与六龄童、十三龄童同台演出的绍剧名角,她便是许多绍剧经典剧中的皇太后(《于谦》)、佘太君(《百岁挂帅》)、李母(《智取威虎山》)、崔大娘(《奇袭白虎团》……虽是一片绿叶,却光彩夺目。
杨妈说,杨爸也是科班出道的绍剧乐队成员,后来为照顾孩子才放下乐器离开剧团。现在,杨家三个女儿中,杨大已成家,外孙女满月不久。杨二今天上班,杨子是小女儿。杨爸杨妈都曾教她们学表演或乐器,最后都放弃进剧团而去了企业……
杨妈十分健谈,时而细语,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客厅内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气氛,完全忽略了冬日的寒冷和彼此的陌生感觉。不知不觉中团筐里的米只剩下一小半,时间也临近中午。我想应该返回了,可裹粽还没有结束,临阵离开也不好意思,还是把任务完成再说吧。当然,初次登门是决不能留下吃饭的。裹粽终于完工了,满满两大盆粽子似两座小山,那是今天的劳动果实。我刚想告辞,但见杨爸从厨房里端上一碗碗冒着热气的菜,说“可吃饭了!”我站起来就要离开,杨爸妈却一齐热情地挽留:“太迟了,就吃了饭再走吧。”我一时不知怎好,这时杨子从书房里出来,轻声说:“那就留下吃饭吧,回去食堂也关门了的。”我就不再推辞。不一会儿,杨二也下班回家吃饭。
这是自己第一回走进杨家,也是第一次在杨家吃饭。而且,这不是人生的插曲,而且崭新的开端。
忘不了杨妈送出家门,在井台边上的叮嘱:以后常来玩,星期天没有事就到这儿来吃饭……
从此,我自由地进出这井台边上的小门,杨家成了我离开父母之后的一方乐土。常常与杨子漫步到小河边,信步跨过那座小小的纺车桥,徜徉在东双桥、八字桥和广宁桥畔,留连忘返。
有时留下吃饭,杨妈后来发觉我爱吃鱼,每一回总是煎好鱼,放在我面前。
寒去暑来,这一年的暑假,在杨子期待的目光下,我又走在求学路上。此前,已与许学刚老师一起二下福建龙岩读书,这一年华东师大把学习地点安排在芜湖安徽师大,而许老师因身体原因申请休学,不能同往。这个盛夏,持续高温,还没有台风迹象。杨妈得知我要孤身去芜湖既兴奋又担心。出发前的晚上,又在杨家吃晚餐作为送行。如每一次离家时,父亲总是叮嘱“有否忘了带上钥匙、手表、钱包?”一样,此时的杨妈也是不停地嘱咐着、唠叨着。我起身要回校了,杨妈也送我出门。杨妈跨出客厅,见客厅门外有杨爸刚带回家的六罐可口可乐,随手拿起其中一罐塞在我手里:“带着,路上可喝的。”
当时,只在电视里观看女排比赛暂停间隙,姑娘们在喝各种饮料,总以为那是至高享受。夜里,我把这罐可乐放在旅行包里,想着不能随便喝掉,应该在最需要的时候。
第二天,我乘车至杭州。杭州大学同学多,去前已写信请学新闻的钱渭南预订校内的招待所,买一张去芜湖的车票。此时,学哲学的积夫已毕业留校在人口所,耀鸿回嵊党校任教。学中文的国祥正在等待毕业分配,所以仍待在学校。午后,大家坐着闲聊。看国祥留着短发、光着背,看上去肌肉很发达,象个练武中人,有同学“祥子、祥子”地称呼他。因为高温,大家聊的话题也是如何消暑。积夫说:“有一次去一位老师家里,老师从冰箱里拿出西瓜,切成片让大家享受,一口吃下去,透心的凉,那个爽啊!”如望梅止渴,大家也觉得凉爽爽的。此时,我想到了旅行包里这罐可乐,心想自己还不知可乐的滋味是咋样的,以前只喝过汽水。当然,这个时候还不是喝可乐的时候。
住招待所同室的是一位来自北师大中文系研究语言学的教授,这次他来杭大授课。他坐在床沿上,先听我叙述,然后如同给弟子上课般地教导我:如何选定方向,如何研究地方文史,如何做到一步一个脚印,不好高骛远……觉得受益非浅,有着许多启迪。最后,我要他签了名。
第二天清晨,骄阳如火,我坐上了去芜湖的长途班车。临行前,我把这罐可乐从旅行包里取出放在随身书包里,心想在路上把它喝掉。又将搪瓷茶杯盛上水,把毛巾浸在杯里,以便随时可擦汗。当时的汽车没有空调,公路也是沙石路面。在烈日和高温下,客车向湖州方向进发,车行时有风吹进车厢,感觉凉快,一停靠就闷热难受。几次想取出这罐可乐,又想到中午阳光更炽热,再留着吧。临近中午,气温明显升高。车过长兴进入浙皖交界地带,道路更加崎岖,窗外人烟稀少,有点荒凉。这时,我取出这罐可乐,想打开喝下去。可汽车“吱”的一声,停下了。原来车停在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偏僻之地,让大家下车吃午餐。我就不再打开这罐可乐,点了个豆腐羹加一碗饭,努力吃下。午后客车继续赶路,进入了安徽地界,气温也越来越高,心想把可乐再留着,万一中暑了再饮用。
临行前查阅过地图,去芜湖须经过宣城,是盛产宣纸的地方。宣城停靠之后转向芜湖方向,总以为傍晚才会到达。不料四点过后,客车就进了站。我下了车,想擦一把汗,就取出搪瓷杯,打开盖子,手指触到毛巾,水是滚烫的,毛巾也是滚烫的,哪可擦脸?这时又舍不得喝可乐,留着再说。
走进安徽师大,一棵棵苍劲的参天大树,一条条幽深的林荫小道,一幢幢掩映在绿荫里的欧式教学楼,显现着这所学校的悠久和底蕴。而室内设施却非常简陋,学生放假宿舍腾空让我们入住,五六人合住一室。同室的有南通师专研究楚辞已有一些知名度的周建忠老师、泰安的闵军,还有与我年岁相仿的镇江赵永源等。当天晚上开班仪式后,第二天就要考试,这一夜大家就早早入睡了。室内只一台立式摇头电扇,放在靠窗的中间,整夜让它摇头送风。室内高温难耐,这电扇一扫到自己身上,还没过瘾,已摇到他人方向。一夜似睡非睡直到天亮。第二天,大家一起笑谈这一夜享受电扇的体会,便匆匆上教室参加考试去了。
平时考试时,习惯泡上一杯浓茶,这一次带着这罐可乐放在桌上。华师大的考试有它的独特个性:不出难题偏题,题量也不大,就是四五个题,让学生选其中之二三,主要考核学生答题的质量,而且给足时间,时间规定为四小时,可让尽致发挥。当天上午、下午各考一门。试卷发下来了,只是薄薄一页纸,外加数张八开答题白纸。试卷共四个题目,要求选二题作答,看似简单却又一时无从落笔。沉思片刻,慢慢进入了考试状态。接近四个小时时,我才完成答题,其间只喝了几口茶,没有打开可乐罐头,想到下午天更热,考试更辛苦,留给下午吧。
下午考试,我进入状态快,下笔如有神,不到三个半小时就可以交卷了,也只喝茶,没有打开这罐可乐,又带回到宿舍。傍晚我去买来了一个西瓜,大家共享着时候,周建忠老师提议:每天轮流买一个西瓜,不论大小,不要攀比,一个就行。大家一致赞同,这一规矩直到学习结束。因为天天吃西瓜,我把这罐可乐忘记了。
不同于二下龙岩读书期间,第一次只有万云骏先生带着助手赵山林老师唱独角戏——万老一人讲课为主,赵老师中间插上几节课,一个夏天灌输的全是诗词曲比较研究;第二年是方正耀和马兴荣老师演出二人转——方老师讲明清人清小说研究和马老师授元明清文学。而这一回华师大派遣一个专家团队粉抹登场:中文系主任徐森华携高足谭帆授古代戏曲与曲论,高建中讲唐宋词研究,周圣伟激情演说词学理论,听者如饮佳酿,印象深刻。不知不觉中学习结束了,大家结伴上黄山观光。整理行李时,才知道这罐可乐还在,可仍舍不得喝,就带上黄山去吧。
我没有去买登山鞋,也不用持拐棍,自信穿这双后跟有点高的凉鞋也可以登上黄山。随身包上只放着这罐可乐和茶杯,经过屯溪来到黄山脚下,就开始登山了。黄山不愧为“天下第一奇山”,此时觉得不是奇在拥有奇松、怪石、云海,而是攀登天都峰时山道的险峻、窄小。翻过那个闻名于世的“鲫鱼背”时更觉得奇险无比。这时有点后悔不买登山鞋了,可登黄山没有退路,只有继续前行。来到迎客松位置,那是黄山上看“五绝”的最佳看点,也是到过黄山的标志。因为要住在黄山上,这个时候没有也不想喝掉可乐,留待明天吧。
山上昼夜温差大,夜宿高山,盖着厚厚的棉被子听寒风呼啸,松涛阵阵,如进入隆冬季节。清晨没有租棉大衣去观日出,也没有与周建忠老师他们一起登莲花峰,一则觉得凉鞋后跟过高,下山不太舒适。再则,心想留一处观光点,以后与杨子一起上莲花峰吧。于是,一人继续在山上转悠着。又临近中午了,在一处休息区吃饭,又摸到随身包里的可乐罐头,心想午后就要下山返回芜湖了,总不能带回绍兴去。此时,仰望蓝天,白云竞渡;俯瞰群山之外,点点村落,隐约可见,我小心地拉开易拉罐扣子,品着其中滋味,想到了小时的汽水之味,想象积夫所称的第一口冰西瓜味道,也想起杨妈送给这罐可乐时的爽朗笑声。一时觉得这滋味格外爽口,更格外甜蜜,美在心头。
午后下山返回芜湖,再乘坐至上海的列车,然后转乘沪甬开车在凌晨时候回到绍兴。但见绍兴遭遇了一次罕见的强台风袭击之后,环城西路上不少梧桐树横躺在路边,呻吟着。
第二天,我又回到了纺车桥河沿那个井台边上的家门。杨妈见我返回了,看平安无事,连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杨妈担心的是台风来袭,一夜牵挂。杨妈当然不知道芜湖那边仍是艳阳高照,赤日炎炎。我向杨爸杨妈报告了一路走去,直到黄山上才把这罐可乐喝下的事儿。杨妈听后哈哈大笑,道一声:“真是呆大赳(意为傻得可爱)”脸上写满了欣慰的笑容。
这一回读书回报给杨妈的成绩单是:唐宋词研究、明清人情小说研究考试和词学理论的考查均为优秀。从杨妈的称赞声和杨子自豪的目光里,所有的疲惫一时烟消云散。因为学有所得,立即跑到柴场弄许老师家,要求他不要放弃,明年一起上华师大本部完成学业。
一年之后,我与许老师在华东师大完成最后的学习考试。结束这一天,杨子也专程到华师大,还有当时的校领导王文光出差到校。当夜,我和许老师拿着大小盆子和茶杯去食堂买几个菜,四个人围坐在宿舍的书桌上聚餐。因为一身轻松,大家开怀畅饮,载笑载言,好不开心。在随后的两天里,我携杨子先去吴淞小姑家,又去新闸路,走进鲍贤伦、王挺老师家里。那几天徜徉在长风公园、南京路上,享受着“罗马假日”般的好时光。
返回后,因为仍处于暑假,杨妈对我说,想去我家走走。我立即把喜讯告诉家中的父母,这让父母喜出望外。母亲喜滋滋地告诉邻居,邻居婶婶们又奔走相告。一位《三打》中的绍剧演员要到村里来的消息,很快从城隍山传到老屋台门,扩散到大半个村庄。
我先回家作些准备,再回到在县城里的大姐家。第二天,去车站迎接杨爸杨妈的到来。班车到长乐后,小姐夫驾驶三卡车接站,到太平乡政府二哥处休息片刻后,再由二哥陪同着一起向村里进发。山道蜿蜒曲折,坎坷不平,杨妈平时易晕车,而这回却精神饱满,信心十足地说:“这次不算辛苦,相比前几天到东白山军马场慰问演出,这次是享福了。这儿空气好,不会晕车。”到村了,小姐夫停下车,此时杨妈戴上太阳镜,只见此时的杨妈不再是裹粽子时的居家母亲,俨然是一位如王昆、郭兰英、徐玉兰那样的艺术家,端庄、优雅,颇具大家风范。因为家在村最高的城隍山,杨爸妈健步而上。闻讯而来的乡亲扶老携幼,齐刷刷站在路口或家门外,如夹道欢迎,向艺术家投之注目礼。杨妈总是报之以浅浅的微笑。
父母早已在家门外等候,父亲乐呵呵的,母亲笑嘻嘻的,把最珍贵的客人迎进了早已打扫干净的家门。
这是过年才有的氛围。二哥负责去镇采购鱼肉,父亲负责采摘新鲜蔬菜,母亲上灶烧饭菜。父亲难得休息在家,全心陪同客人。父亲生性豪爽豁达,年青时常翻山越岭下平水,过绍兴五云门外去余姚挑私盐,对沿途的风土人情如数家珍,加上熟悉戏曲又博闻强记,与杨爸杨妈两位绍剧人一见如故。他们聊家住楼房的建造过程,聊如何教导子孙读书,聊儿女如何孝顺……屋里充满着快乐的空气。
许多父老乡亲慕名而来,都想领略《三打》电影外生活中的绍剧艺术家风采。一时,乡邻接连不断、门庭若市,母亲总是热情招呼、乐此不疲。
第二天清晨,我陪同杨爸妈在村里游走。走进“老屋台门”,又登上画图山观赏村景,再下梯云桥畔看潺潺流水。最后,走进了马氏家庙。站在那精致的戏台前,曾在许多宗祠戏台上演出过的两位艺术家,也被这大气、恢宏、精美的家庙吸引住了。此时,敬爱的昌翰先生已从嵊州师范退休回乡。先生的父亲是重建家庙的发起者和主持人。先生作为长子,对家庙有着特殊的感情。先生闻讯进来,和蔼可亲的,说家庙往事更是娓娓道来,先生说用石材为主是为了建成永久性建筑。这一根根高大光滑的石柱取材于苍岩施家岙,先用竹排水运至太平,再由村里的大力士们抬进村再打磨而成;这戏台低平设计是为了让看戏人不必仰视,不易疲劳;戏台两根台柱子不用粗木柱而是用两支细长的铁柱,是为了不阻挡观众视线,影响欣赏效果。家庙的特色还在于砖雕、木雕,堪称二绝,都是当时当地和东阳的能工巧匠的杰作。先生还兴致勃勃地读起石柱上的一副副楹联……我是闻所未闻,杨爸妈也连声称道。杨妈对先生说:“小崑有这么大的村庄,这么美的家庙,这么好的民风,这么多的读书人,都是代代传承、发扬的结果,这样的村庄真的很少见。”
此时仍处暑假,已上学的侄子侄女和外甥们都放假在家。他们个个活泼可爱,又聪明好学,得到杨爸妈的喜爱。十年、二十年过后,他们已长大成人成材,杨妈仍能记得他们的名字,常常询问着,时时念叨着。
母亲一向热情好客,更是闻名的家务能手。这二天使出了浑身解数打理饭菜。母亲精心制作的炒榨面、煎豆腐,还有取材于湖塘塍的高山酱萝卜,让杨爸妈连声夸赞。自此,母亲与杨妈结下了深情厚谊。此后两位母亲间的互相牵挂和问候成了一个恒久话题。
第三天午后,杨妈要起程再回娘家——嵊州城南芭弄村。在村口,杨妈与母亲执手话别,杨妈说:“这儿夏日清凉,空气清新,亲友个个热情好客,真是个好地方,以后肯定还会再来。”
杨妈出生在艺术之家,父母兄弟都擅长吹拉弹唱。外祖父母是王金发的弟和弟媳。十六岁时,杨妈被考官慧眼识中,意外地考上浙江绍剧团。因父亲早逝,进剧团后没有几年母亲也与世长辞。作为家中长女,杨妈以微薄工资不时倾力接济家中兄妹。特别是把生病小妹带到身边抚养成人更被传为佳话。
走过澄潭江穿城一段的长长的木板桥后,前面就是芭弄村了。这时,杨妈告诫我:对家人可能出现的怠慢不要在意。我当然不会的。进入村里,迎面就是一个古朴的台门。左边住着大舅,右边是二舅家,二舅生病坐在椅子上,不时咳喘着,显得很难受。原来此行是看望生病的二舅来的。
晚餐之后,天下了雨,没有路灯,整个村子漆黑、安静,觉得这夜有点漫长。经舅舅和表兄弟们安排,杨妈住大舅家,我和杨爸睡二舅小儿子家。这是二舅新建的房子,勤劳的二舅也因此积劳成疾。大儿子住右边,小儿子住左边。走进房里,有二张床,北边靠窗大床是小儿子夫妻加尚在襁褓里的儿子的。南边床归我和杨爸同睡。五人同睡一室,此时想的是尽量早早入梦。只是熄灯之后,一次次被婴儿的哭闹声催醒。
早起后,见杨妈笑吟吟地进来,说就在二舅的大儿子家吃早餐。大儿沉默寡言的,而大儿媳妇热情招呼着。她早已起了个大早在灶头上忙碌着。她小心地端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鸡蛋肉丝面,喝一口汤,感觉挺鲜美的,而他们自己却吃别的,心想杨妈进村前的担心并不存在啊。
离开了芭弄,直接去北站。我先送杨爸妈乘车回绍兴,再回家去。排队检票之时,思想前后,加之这几天的伴随,一时觉得与杨爸妈难分难舍,情深意重。一向不善于称呼人的我,此时学着杨子的称呼爹妈的习惯,脱口而出:“阿爸、妈,你们慢走……”杨爸妈听后,先是一愣,转而相视一笑,杨爸只是微笑,杨妈说:“你放心吧,早点回来!”
自此,我在离开家门、离开父母之后,又拥有了一个新家、一对爸妈。特别是这位妈妈,是一位功底深厚的绍剧艺术家妈妈,一位一直以来视我为己出,疼我、鼓励我、器重我、赞赏我的妈妈,一位当我有失敬时从不指责、抱怨,总是包容、勉励的妈妈。
只是涌泉之恩,却再难以滴水报答。
(写于2016.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