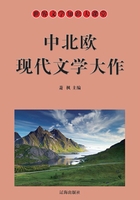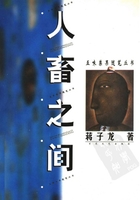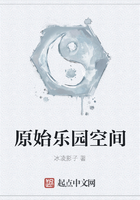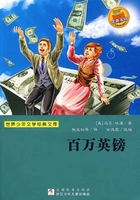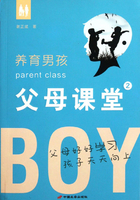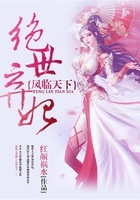记得,在高考前的一段日子,学校放了假,让考生在家里作迎考的复习。
那是一段初夏的时光,昼很长,夜好短,极符合惜时如金的考生心意。每天,总是随着鸟儿的鸣叫声起来,到屋后的山上,坐在一棵挺拔的香榧树下早读。呵,“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不过所处的不是清晨的校园,而是参天的大树之下。这个时候,勤劳的父亲也总早早起来,上自家地里干早活。当旭日东升,阳光照耀在香榧树下,也照射到我脸上的时候,就下山回家吃早饭了。这个时候,母亲已备好了早餐,父亲也肩扛锄头,手里拎着满满的一篮子蔬菜,从小溪对面的地里归到家门。在将满盛着新鲜蔬菜的扁篮送到妈妈灶台边上的时候,父亲脸上写满了笑意,那是父亲辛勤种植获得收获的喜悦心情。
父亲与妈妈生来似有一种男耕女织般的默契。一个上山劳作,一个操持家务。久之,就造成了术业有专攻般的分工:父亲专于农事,不会家务,偶然做了,也是成不了模样的粗活;妈妈精于家务,也不太上山,如上山了,也不如别的母亲那样能干。但父亲和妈妈一个相同点就是特别重视教育,特别希望子女读好书。
一段紧张而宁静的居家复习日子过后,我又回到了镇上的中学参加高考。
那时,大家普遍不够富裕,用以读书生活的费用当然不会很多。自己也不会在乎读书的清苦,只会珍惜读书的机会,生活将就着过得去就行,绝不会想到吃什么花什么的。与许多学生一样,平时以自带干菜为主,不太去排队买菜。那时,在学校食堂里排队买菜只有“居民户口”的学子才可能拥有的待遇。高考几天,能不吃蒸熟的干菜,得以加入排队买菜的行列,已是一种莫大的改善。
那天午饭后,与往常一样,习惯在食堂前的橱窗上看报。忽然听到了一个亲切的声音,叫我的名字!
啊,是父亲来了,正站在我的背后,亲切地注视着我,微笑着。一时觉得好意外,因为父亲虽极其关心读书,但从不到学校里来,或在老师前问这问那的。
父亲仍是平时上山劳作时的装束,带着笠帽,打了补丁的白上衣,黑裤子。
问父亲,怎么来学校了?
父亲说,与别人一起来镇上为集体销售一批“燥茶”,茶叶销售完毕,就来学校看看我。边说着,边从上衣口袋里挖出五元钱来,塞在我的手里,笑着说:“就要考试了,能买菜吃,吃得好一点!”
心里当然明白,妈妈已将家里仅有的钱让自己带来了,也知道这肯定又是父亲向集体预支来的。
现在看来,这五元钱,真的不算多。可那一刻,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对父亲说:“有从家里带来的钱,足够了。”可嗓子里感觉塞塞的,不知说些什么话,才好。
父亲仍是一脸笑容,没问复习迎考上的事,只说了声:“要回去了。”就转身离去。
我说不出什么话儿,只望着父亲远去的,那高大的、微微有点儿躬了身的背影,缓步向着学校大门走去,又消失在大门边,踏上归家的长路。
父亲走了,我转过身子,把脸朝向长长的报栏,佯装继续阅读墙报。其实,是为了不想让眼眶里打着转儿的泪水流下来,也不想让同学看见什么。
这是那一个高考前的午后,父亲留给我的一个背影,一个铭记于心的记忆,现在仍如在目前。
(写于2009.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