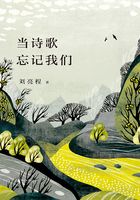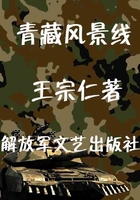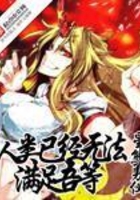许多事都如过眼烟云,而有些事却铭心刻骨。许多年前,二哥和姐拍摄高中毕业合影情景,记忆犹新,仿若昨天。
那时不满十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家里刚陷入磨难之中。此时,大昆办起了高中。当时姐刚初中毕业,而二哥好几年前在长乐中学读完初中。父亲送姐读大昆高中以外,还竭力让二哥与姐同上高中。此举让众乡邻迷惑不解,但父亲却坚定不移,只是七口之家,供养四个子女上学的重担全压在父亲肩上。
俊逸云集的首届高中班,给二哥和姐提供了珍贵的学习机会,也为全家打开了一扇充满温情和清亮的窗户,更让背负精神和生活重压的父亲不时露出爽朗而欣慰的笑容。这些来自大昆地区各村和沃基、坎流、南庄等村的许多青年学子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他们成群结队,串门走户,意气风发,构成了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常挤在楼上小小房间里,或研讨作业,或指点江山,或操琴放歌……这一方寸之地,成了他们的作业园地、文学沙龙、青春诗会。楼上房内青春激扬,楼下灶间热气腾腾。有这样的同学到家里,父母总是喜形于色,乐此不疲,台门内外洋溢着快乐的空气。父亲对学子们总是乐呵呵的,他们也跟着我们叫“父亲”,仿佛全是自家的兄弟姐妹。我也慢慢熟识了这些哥哥姐姐,叫得出许多人的名字,如孔村的岩袁、油竹潭的金钗、上园的水娟、留王的小明、水口的岳汀等。认得岩贵、福苗这样气宇轩昂的帅小伙,梅飞、小飞那样才情并茂的奇女子;知道有两位活泼开朗的“华娟”,两个沉稳内敛的“立元”,还有一位几乎与红楼女子同名的小才女——“静文”。后来还知道不少同学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如二哥和同村的永兴、樟贤他们能撑起一支有实力的篮球队;永良擅长打乒乓球,听说有过不俗的战绩;先看到娴熟地拉着悦耳的二胡,后又很有范儿地拉起当时十分稀罕的小提琴,还能写一手好字的正琪,让我们好生崇拜。
有时,如有老师到来,让一家人视为无上荣光。父母把每一位老师奉为上宾。印象最深的是渔樵老师和善敬老师。渔樵老师是大昆本村人,在小崑有亲戚,当走访了亲戚后,总会拾级而上,到我家坐上一会儿。被父母兄弟姐妹迎进门的渔樵老师温文尔雅,笑容可掬,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告诉父亲一对儿女在校的表现。这时候,父亲面含笑意,一脸的虔诚。渔樵老师娓娓道来,细说着二哥如何的优秀,姐又是如何的聪慧……父亲听得笑哈哈的,妈妈喜滋滋的。这时候,窗外的一方天空似乎渐渐清朗起来。
善敬老师是长乐人,经历丰富曲折,富有传奇色彩。他是哈工大的毕业生,曾是抗美援朝时的随军记者。善敬老师真诚坦率,博闻强记,每次坐定后,他总是侃侃而谈,聊经历、道人生、说诗词,激情四溢,在台门外便能听到善敬老师的清脆嗓音。一些邻居会寻声而至,倚在我家门边聆听着善敬老师的倾情谈笑,仿佛我家的厅堂也是他的三尺讲坛。一家人与他亲密无间,在我们孩子心目中,他便是家里一位可敬的长辈。
不知二哥和姐邀请过多少老师和同学进过家门,只记得当老师或同学到来了,家里不再有苦闷,而是心情舒畅;不再有阴霾,而是阳光灿烂。有一回,大概是春节后,云飞和静文两位姐姐到家作客。第二天,她们要返回了,妈妈不肯放行。在房门和天井间的沿界石上,妈妈紧紧拉着静文的手,夺着她的阳伞,不让她们离去。机灵的静文此时无以应对妈妈的盛情,只有咯咯地笑着:“哪会噶客气来!”
冬去春来,那一天家里又来了一群同学,为首的是岩袁。他总是满面春风,特别亲和,老少都能打成一片。他家与我家有些相似,他与岩贵这对兄弟和二哥与姐这对兄妹同班读书,在班级里也是一个奇观。他家兄弟五人与我家兄弟姐妹五个人数年龄也相仿,所以平时交流时也多了一些有趣的话题。这一回,听他们说就要毕业了,明天到中学拍摄毕业集体照,今天先到小崑聚会。我还没有去过大昆,听说他们要去拍毕业照,心里直痒痒的,希望能跟随他们去大昆看热闹。二哥和姐没有反对,可妈妈没有答应。还是岩袁说服了妈妈:我是大“Yuan”,他是小“Yuan”(名字中都有一个Yuan音),我带他一起走吧。这时,对岩袁心存特别好感。自此以后,当有人故意逗我,问岩袁岩贵兄弟谁更帅一点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倾向于岩袁。其实,岩贵是班里公认的帅哥之一。
第二天清晨,同村的和外村来客共二十来位同学组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进在担架横路上。这时候,日出东山,云蒸霞蔚,大家的心暖融融的。一路欢声笑语,青春飞扬,岩袁牵着我的手翻过了瓦窑平岗,穿越柿树岙头,下东湾岭,进入大昆地界。俯视山脚下,阳光映衬下的一堵白墙矗立在小溪边上。岩袁说那便是中学的厨房了。我的心早已飞向这向往已久的陌生校园。
大家从学校背后的土坎上跃下进入教室。我站在石阶尽头好奇地打量着这一奇特的校园,只见在群山环抱之中,学校座落在狭长的大昆村的最东边,西南侧紧挨着供销社。学校从供销社东墙外进入,入口处正对着面前这三米多宽的十多级石阶。以这石阶为界,西边依山而建有一幢二层教师宿舍楼,东边是操场,主体是一个篮球场。操场东边上几级石阶便可走到给师生提供蒸饭和开水的厨房,厨房楼上又是学生宿舍。厨房东侧以下,源自东湾的涓涓山泉便是师生淘米蒸饭的饮用水源了。操场里壁用错落的石块砌成高坎,然后在高坎上建成一排一字形教室。教室门外走廊连通东侧的厨房和西边的教师办公室和教师宿舍。四间教室恰好与操场长度一致,构成了学校的主体部分。从学校进口而建的十多级宽阔的石阶便是连通操场、办公室、教室和教师宿舍的枢纽。听说这一排教室是师生边学边建的丰硕成果,凝聚着师生的汗水也寄寓着他们的梦想。在这特殊的年代里,在东西白山之间的深山幽谷、大昆江畔围墙建校,兴办高中,以教育人,这儿开始引人瞩目,令人向往,寄托着山乡人的几多希冀。
我在走廊上、操场上、厨房边上转悠着。最后回到走廊上倚栏张望着面前的一切。这所学校虽然简朴,却是崭新的,虽然狭小,却生机一片。这个时候,见一些年长的同学在教室一角或走廊上话别或互赠礼物,一些年小的同学头顶肩扛的,将教室里的桌椅搬到操场东侧开始做合影前的准备。忽然,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传来,只见一辆自行车从学校入口处飞驰而至,急停在操场围墙一边,是摄影师赶到了。摄影师麻利地解开后座上的绳束,从油布包里取出摄影器材,在操场中央支起三角架,架上相机。又开始指挥师生在操场东北角梯次摆放好三排桌椅。准备停当后,老师招呼全班同学到操场集合,老师们也来到了操场,其中有善敬老师、渔樵老师的身影。摄影师先让个子略高的男同学进入第四排凳子上站立,其他男同学站到第五排课桌上去。又让个儿略高的女同学在第三排站定。然后请老师们端坐在第二排的板凳上。待老师们坐定后,摄影师又让其他女同学蹲在老师们膝下。这时候,只听行列之间交头结耳,笑语一片。站队停当后,摄影师回到照相机后,钻进黑布口较准镜头。反复调试之后,他探出头来。这个时候,他俨然是一位自信而严谨的乐队指挥,向一些师生发出位置较正指令。刚还在起哄逗乐的大伙儿,霎时安静下来,听从摄影师的指令,抬头亮相,塑造成一组立体群像。只见摄影师右手按着快门,扬起左手,指挥师生看着他左手,听着他的口令:一、二、三,“咔嚓”一声,一个个青春的姿容便永远定格在这早春的阳光下,也深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此后,父母仍时时惦念着照片内这些熟悉的,给家人带来许多快乐和莫大慰藉的高中学子。
此后,不少同村的毕业生成了村校的民办教师或代课老师。听说他们同班中的许多同学加入了这一行列。
后来,我的小姐姐和两位堂姐,还有甘霖的一位表姐进入大昆中学读书,也成了善敬老师和渔樵老师的学生。
后来,听说二哥和姐的一些同学陆续升入高一级学校,不少成为教师或进入党政机关。
后来,我也意外地进入大昆中学读书,只是二哥和姐他们是首届,我已是最后一届。照片中的老师张立平成了我的班主任,校长高宏章是化学老师,朱水华为物理老师,照片中的学生正琪成为英语老师。照片中一些同学的弟妹也成了我的同学。直到二年级时,渔樵老师才成为我的语文老师,一位经常将我的作文在课堂上深情朗读、备加赞扬的老师。至此,他成了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的老师。曾有一段时间住宿在信用社和广播站合用的楼上,结识了二哥和姐他们的同学而合影里没有出现的广播员苏萍姐姐。
后来,我又进入长乐中学,意外的是善敬老师担任文科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让父母兄弟姐妹颇感惊喜。多年未遇的善敬老师一如既往,性情真率,充满激情,富有爱心。至此,他成为我们全家的又一位老师。
后来,在二哥和姐那儿得到的一些碎片化消息,串连起来的印象是:一些同学尽致发挥他们的智慧和胆略,艰苦创业,取得了非凡的业绩。也有一些同学教子有方,如我侄儿外甥一样,考入许多著名院校,出现了不少硕士博士和留洋学子。即使扎根在乡村里的同学也是村庄建设的领头雁,他们传播文化、滋润文明,显现着不同凡响的软实力。
我想,在那一段特殊的岁月里,合影里的许多师生对我二哥和姐而言,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同窗谊;对一家子来说,他们的真情厚义,如长夜里的一缕光亮,苦寒中的一股暖流,彰显着人性的芳馨,驱使一家人重新扬起生活风帆,激起对未来的信心。就整个班级而论,照片中的同学各有各的心路和精彩,一家有一家的酸甜苦乐。岁月能磨灭许多故事,而有的却经久弥新。这许多年前的合影,可能不只是我的孩提印象,更是照片中人难忘的青春记忆。
(写于2017.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