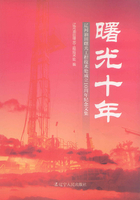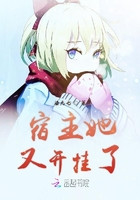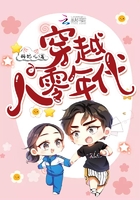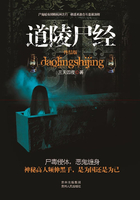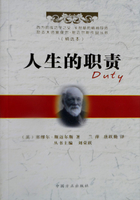妈妈住大哥家多年,已好几年没有回村了。每一回想带上妈妈去看看公路修到家门外的新变化,妈妈总以晕车为由作罢。这个星期日,仗着两位姐姐同在,大姐家又离停车场不远,我又要妈妈回村走走看看。这一次,妈妈没有推却,欣然同行。
不知是因为回村的喜悦,还是妈妈仍很健朗,妈妈不用小姐姐搀扶,下车后健步如飞,走石阶也如履平地。这个时候,妈妈如游子归家般的兴奋,没有老态龙钟的模样。
妈妈在十年前记忆力开始减退,对眼前发生的事,过后就忘记;对新认识的客人,如再次登门就不知是谁了。出门忘了带钥匙,烧菜忘了放盐也是常事。可是这一次,却不一样。午餐之后,大姐陪伴妈妈去串门访旧。走进了久别的家院,又眺望家门外新建的沥青公路,让妈妈喜形于色。一路遇到一个个新老邻居,妈妈都能一一相认,亲呼他们的乳名,没有平日易健忘的窘态。
好多亲友说,他们每与妈妈相逢,妈妈象当年那位人见人敬的接生员湘云姑婆一样,那亲切的笑容温暖如春,拉着他们的手问长问短的,久久不肯松开。大姐说,今天妈妈与婶婶们相见时,彼此如阔别已久的亲人,格外亲热。妈妈出生八个月后就从外婆家抱到老屋台门奶奶家做养媳。妈妈在老屋台门长大,台门内外的晚辈们都称妈妈“湘娟娘(姑姑)”,从不按辈分称奶奶或婶婶的。全家搬入城隍山新居后,与众多新邻居朝夕相处,困难时互相接济,近邻胜过远亲,结下了深情厚谊。而今意外相逢,妈妈一个个拉着她们的手,互相打量着、寒暄着,个个笑逐颜开,不忍离开。大姐说,妈妈特意走进了徐杏芬家,这让这位婶婶喜出望外。以前,两家一墙之隔,窗对着窗,孩儿们常常隔窗招呼、嬉笑。这位婶婶不太擅长家务活,妈妈手把手教她衲鞋底、缝衣服等活儿。遇到受委屈时候,妈妈也会挺身而出帮衬她。所以,在许多邻居心目中,妈妈有副热心肠,乐于帮人助人。
只是有几位婶婶不在家,让妈妈脸露憾色。九旬舅妈生病治院,更让妈妈忧心。
冬日暖阳,青山苍翠,我们准备返回太平了。妈妈依旧不用搀扶,下踩一级级的石阶也如上行时的稳健。正要上车,忽听着一声呼唤,但见一位白发苍苍的高个子婶婶匆匆而来,原来是灿琴。妈妈迎上前去,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这时,又见一位满头黑发的小个子婶婶疾步走到她们面前,原来是洪生花。只见妈妈立即分出一只手紧紧拉着生花的手,一手牵一人,说长道短,依依不舍。夕阳西下,彩霞满天,我赶紧拿起手机摄下这一珍贵的镜头,让这一温馨无限的画面定格,更留在心底。
原来,当大姐和妈妈走到她们家时,都不在。她们闻讯后,急忙忙往村口赶。这位高小子婶婶是老屋台门的邻居。每当我回村遇见,她总是直呼我的乳名,显得格外亲热。她也会关切地询问妈妈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她经常夸赞妈妈,大致意思是她与我妈妈自小在一起,妈妈热情好客,心灵手巧,针线活好。当年村里在大办食堂的同时,又选出十多位精于针线活的青年妇女在兰洲公祠办起缝补站,为村民裁衣制鞋。妈妈是缝补站的头儿,威信高,人缘也好。妈妈在平时也常教她裁衣服……现在妈妈不住村里,让她时时记挂着。这位小个子婶婶是家住城隍山后的邻居,两家非亲非故,却不嫌贫寒,相互支撑,成为世交。几年前妈妈意外摔伤,这家叔叔和婶婶得知后起了个大早,心急火燎地到太平探望养伤的妈妈。
在两位婶婶的叮嘱下,妈妈松开了手,与她们道别。不知是一天奔走劳累了,还是遇见了众多亲友心满意足,妈妈上车不久就安然睡着了。
望着妈妈从容淡定的脸庞,回味着妈妈回村后的兴奋和婶婶们的盛情,我放纵着思绪,妈妈经历过的几个片断,虽历经数年,但如在目前。
大概在七八年前,妈妈被大哥接到株洲。虽在异乡,但一家三代,其乐融融。直到现在,妈妈仍在念叨着:白天大嫂和侄女去上班,大哥陪着妈妈聊着天。妈妈度过了一段十分安逸的时光。只是有一天,当妈妈获悉我岳母生病住院时,妈妈忧心忡忡,决意提前返回探望亲家。
多年前,岳父母专程造访小崑与父母相聚。两位绍剧名家不嫌城乡差异、农工之别,与父母结为亲家。父母住绍兴时候,多次到岳父母家作客,得到盛情款待。许多年来,他们之间虽很少相聚,但时时相互问询,托我互致问候。父亲和岳父先后离世之后,我每次回家,妈妈总会问:“外婆怎样?”每次会这样说:“外婆白白胖胖,女儿孝顺,福气很好。她是电影(指《三打白骨精》)里演过戏的名角,却很随和,与外婆特别说得来。”每次总是让我捎个信叫外婆在夏天到小崑纳凉。岳母因到过小崑,熟悉全家情况,平时聊及家事,总是夸赞父母重视教育,子孙读书成材,不时询问侄儿外甥们的读书和就业,拳拳之心,时时溢于言表。
农村人小病不住院,一旦住院以为肯定是大病。这一回岳母住院,让大姐代为探望也不行,妈妈提前从株洲回到太平,又迫不及待地要大姐陪同到绍兴看望病中的亲家,那几天,妈妈口口声声说:“我与外婆很说得来,一定要去看看外婆。”
时值早春,乍暖还寒。我护送着妈妈和大姐按响了岳母家的门铃。岳母开了门,四目相对,妈妈呼一声“外婆”,岳母应一声“奶奶”,两位白发老人双手紧紧相握,室内外瞬间变得无比温暖、灿烂。此情此景,让我心潮起伏,一时无法平静。妈妈见岳母无大碍,就放下了心。岳母也很快康复,继续着晨练太极,拜师学书法和绘画的宁静生活。只是每年会有几天的住院,近年住院次数明显增多。记忆力下降的妈妈依然时时牵挂着亲家,为不让她过度担忧,我没有传递岳母一次次住院的消息。去年中秋以后,岳母病情加重,虽在精心治疗,病情却在恶化,不幸在今年的夏天溘然长逝。就在这一天,平时几乎没有病痛的妈妈突然腹泻不止,一天过去,形容枯槁,弱不禁风。我不知道这是纯属巧合,还是因为两位妈妈心有灵犀?总觉得因为她们情深意长,亲密无间,才有此超越时空、感天动地的心灵感应。
夜色弥漫,回到太平村,妈妈从瞌睡中醒来。我也收回思绪,寻思前后,觉得妈妈年近九旬记忆力减弱,健忘也属正常,可妈妈又时而异常清醒、坚定执着,虽饱经风霜,却热情、达观、平和,那阳光般温暖的笑容,如春雨般滋润的话语,传递的是妈妈深厚而博大的仁慈之心。这是历尽风雨之后对新时代的感恩之情,对合家和美的欣慰之意,对亲友相助的感激之心。
于是,觉得年高的妈妈,依然是自己的心灵港湾、精神家园。
(写于2016.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