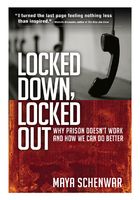粗线条勾勒一下中外文学批评理论形态的发展脉络,因为批评话语主体和批评客体对象的对应关系殊异,所以可以规划出两条文学批评路线:其一是批评主体先行、主导,而批评客体仅仅作为被动的批评对象而存在的“主先客后”型或称“我注六经”式;其二是批评客体先行、主导,而批评主体要秉承忠诚于作品真实、历史真实的批评原则而言说的“客先主后”型或称“六经注我”式。这是两种立足点和出发点相向而行的文学批评观,分别为“情结主义”批评观和“情境主义”批评观。由此经由的两条运行轨迹及采信的两类批评范式,也就描述为“情结”文学批评范式和“情境”文学批评范式,它们各自所产生的批评效应也是截然相反的。诚如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一文中所指出的,历史阐释的真正困境还是在于左右为难的导向问题:“究竟应该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是忠于阐释对象的历史还是忠于阐释主体的‘我’的阐释?”[1]
本论著秉持“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各美其美而又美美与共的阐释理念,首先采信“情境”式文学批评方法,即批评主体主动“沉降”到文化事象和文学文本典籍中,从文本“原始痕迹”和作家的“客我”批评视角来还原和注解那些“共鸣性”的文化文本,进而用“厚描”式粗笔勾勒出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理论形态的来龙去脉和精髓要旨,外化表征为批评主体对作家和文本的本源认同和原创剔抉。接下来,改用“情结”式文学批评方法,“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揭示其大胆跨越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疆界,将“文化解读与历史叙述”“政治话语与权力结构”和“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等多重架构内在勾连起来,弥合无间地构塑成“想象的造型共同体”和“主客融合的文本联合体”的理论质素与实践特色。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批评观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历史主义批评观和形式主义批评观的“新”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话语和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范式,突出表现为一种对历史语境下的“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交互叠加的”文本联合体加以文化释义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批评形态。针对文学批评形态的“批评主体”与“文本结构”二元批评格局和话语体系,不同形式的批评观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打出了各具特色而又主题鲜明的个性旗帜。形式主义批评观选择了“文本结构和形式语言”这样一组阐释关键词,传统历史主义批评观选择了“历史的客观决定”论。
而新历史主义批评观则选择了“批评主体与历史叙事”这样一组杂糅了主客视域的阐释策略。新历史主义批评观在对文本中心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扬弃”和“重塑”中,使“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这一组叙事策略重获关注并宠爱有加,也使“历史叙述与文化结构”“政治解读与文化诗学”这一对批评范畴成为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新科”话题。
新历史主义批评学派大致诞生于20世纪后半叶的欧美文化界和文学艺术界。这一批评思潮首先在方法论领域取得突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期的“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王朝断代史”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视角(critical perspective)和批评方法(critical method)。时移世易,这种刻意置身于历史语境中来阐释文学文本的“文化内涵与权力结构”的独特理论研究方法(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一大批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也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其中,如雷贯耳者有斯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海登·怀特(Hyden White)、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路易·蒙特洛斯(Louis A.Montrose)等。初始是一种新构想(a different framework of Literary Theory),进而创生一种新理论形态,这一历史事件往往萌芽在社会急剧变革转型和学科重组变迁史上需要自我反思、自我修复、自我净化的历史时刻。新历史主义之“新”是相对于传统历史主义之“旧”和形式主义之“冷”而言说的。
加拿大文艺评论家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一书中,说过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文学位于人文学科的当中,它的一侧是历史,另一侧是哲学。由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于是批评家必须从历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事件,从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思想。”[2]诚哉斯言!首先从“知识论”角度来看,文学向来不追求文学自身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如果用那种整齐划一的科学方法论来裁量文学的知识架构,可真称得上暴殄天物了。再次从历史文化维度来看,文学史的脉搏同时跃动着历史事件的“自我塑造”和哲学思辨的“历史记忆”。弗莱的这一论断可以说是新历史主义批评话语的首次发声,仿佛来自历史深处的遥远回响,虽然它还很稚嫩,又单薄微弱。
近代以来,历史主义批评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强调一种总体性的“本质主义”历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受到社会发展规律支配,所以他们作出如下承诺:历史主义将历史形态首要看作一种自我整体力量自主迸发和自由释放的思维形式,它想方设法为被看作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总方向提供一种阐释的理想模式和一整套“历史叙述”(historiography)。其中,这里暗含了整体论和决定论两个要点。这种“总体发展”的机械“本质主义”历史观,在20世纪初即遭遇了政治思想家和形式主义批评家的迎头痛击。
譬如说,英国政治思想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中认为:历史整体论(或称决定论)存在着思想的盲点,“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历史虽然没有目的,但我们能把这些目的加在历史上面;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3]波普尔对历史主义当头棒喝,并痛陈其累累罪行,诸如历史主义鼓吹的“集中的权力”极易做大而会消弭“个人的权力”,这种“封闭社会”的乌托邦工程极易导致集权主义。拨乱而反正之,他倡扬的“开放社会”的“非中心”论、“非权威”论已被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
对传统历史主义批评学派发起攻城略地的另一组生力军是俄国形式主义等批评形态。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使文艺理论越出“历史”的雷池而跌入“形式”的渊薮。历经走马观花式的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潮起潮落,文艺批评实践在支离破碎的文字栈片中进行着一种“互文性”阐释实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后结构主义批评学派的主轴概念,意指不同文学作品内蕴的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交互贯通、彼此渗透、相互交叉的联动关系。很快,这一概念便广为散播,成了跨界多栖明星。后来人们也用这个概念来界说不同文类的“子本”文本之间,甚至“母本”文本与政治境域、社会结构以及历史语境、批评主体之间的互渗、互参、互构关系。
当下流行的“跨学科的互文性视野”则主要是指跨越了常规意义上的学科疆界和认知规范,在本毫无交集的不同文类的各种文化文本之间搜寻求索内在的关联性与相通性。映射着“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式批评架构的中心位移和整体倾斜,盛极一时的“作家权威”“文本崇拜”等批评理念已成明日黄花,位列边缘、谪居边陲的批评家跃迁为文本阐释和意义理解的精神教父,“误读(misprision)和逆反(antithetic)成为现代阐释的独特锁钥”(布鲁姆语)。至此,历史意义、文化灵魂等传统理念和经典释义都在语言的解析和形式的分析中变成了意义的碎片。历史主义烟消云散,终于禅让于整个形式主义思潮。
在“新”历史主义披挂上阵之前,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等批评形态,已经将历史意识、历史批判、历史叙事等话语模式作为自身文化阐释和审美分析的主要符码(governing agenda)。正如撰写过大作《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与历史主题》(1986)和《戏剧的目的》(1996)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蒙特洛斯所说,“我们的分析和我们的理解,必然是以我们自己特定的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的;我们所重构的历史(histories),都是我们这些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所作的文本结构”[4]。这种迥异于“旧”历史主义的历史文化研究思潮,直接冲击着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操作和意义拼接,使那蜗居冷宫的“何谓文学批评形态?”“文学批评与历史叙事的本质意义何在?”“文学批评史的功能何在?”等本源性和根基性问题又获新宠,迫使和协理人们在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交汇点上,找回了久违了的“精神伊甸园”,进而面向新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精神迈进了一大步。这无疑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粉墨登场以至登峰造极”创设了逻辑前提和精神储备。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980年,格林布莱特在《文类》(Genre)学刊上发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型:从莫尔到莎士比亚》(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1980)等系列论文,首次将自己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改称作“文化诗学”(poetics of culture),“文化诗学的中心考虑的是防止自己永远在封闭的话语之间往来,或者防止自己断然阻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生活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我仍然关心着作为人类特殊活动的艺术再现问题的复杂性”[5]。同时,他认为文学批评家阐释(explanation)的任务是:“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6]。这意味着刚由新历史主义批评思潮派生出来的文化诗学批评观更加注重从文化意识和历史叙事角度来理解(understanding)文学形态,把文学形态置于更为宏阔的文化系统和文本结构中进行研究,从而打破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甚至于用非文学学科领域的经济学等学科术语对文学现象加以评判界说,以期达到文学形态与文化系统之间的流通融合与阐释互动。
如果说新批评的文学分析方法关注文学文本本身甚于关注文化、历史、作者与读者,那么,新兴起的文化诗学文学分析方法则强调文化意识、历史形态和其他相关的因素决定了文学文本的意义。这样,“文化意识”和“历史形态”就在全新意义上的“文化解读”(cultural reading,也可译为文化阅读)过程中,进入了当代文学艺术的政治批评视野。文化诗学关注历史,并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延展了文本的阐释维度和意义空间,使文本的创作和阅读成为蠡测生命诗性密度的标尺。在尺度的历史测量和领悟的历史意识中,创作主体和批评主体透过文本而寻绎到生命的美感元素和诗性意义。历史和文本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此概念系胡塞尔首倡,后经哈贝马斯对之进行了社会学改造,成为其“交往行为”论的轴心概念,“生活世界是日常交往实践的核心,它是扎根在日常交往实践中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相互作用的产物”[7]——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语境下的文本,也是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矢量同轴坐标的文本。历史不同于矢量的数量化时间,历史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沟通、商谈”过程,在其中不可逆转的单向度性一再重复出现,过去与未来在文本意义生成中瞬间接通。
与新历史主义批评思想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文化诗学批评流派的“登台在场”,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文艺复兴期人文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文化诗学批评方法重新粘连并命名不同种类的写作实践,以政治解读和意识形态化表征的方式开展文化批评,关注和倚重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历史“语境”,将文艺复兴期发生的逸闻轶事纳入“权力话语”和“权威造型”的历史关系和阐释语境中。从本源意义上来看,落户于“语义学”学科范畴的“语境”一语,顾名思义就是语言环境的简称缩写,指的是在篇章段落中,任何一个语词或句子身处的“上溯与下倾”两个维度的上下文间性关系。具象化语境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它是一切阐释行为的逻辑前提与理解开端。一般而言,任何单个的独立词语或句子,只有置身于具体上下文的间性互文关系中,才具有确切的含义和认知的价值。
与前面提及的“互文性”语词有着相近的传播经历,“语境”一语早已突破了原初的语义学和纯粹的“语用学”领域,以至于被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门类广泛采用。在广为流播的过程中,语境的内涵与外延也大大拓展了,相对定型化的惯用法主要用来指一种微观的文本或宏观的理论,甚或宇观的思想的生成过程与各种外在力量及周边环境的复杂关联,故而又每每被称作历史语境或文化语境。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批评形态就是以倡扬“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批评策略著称于世,正是借助于以历史文化语境为主导的综合性的“语境化”批评手法,新历史主义才毅然冲出了传统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羁绊与藩篱,而最终走向了文化诗学的广阔天地。顺利接棒的文化诗学批评观继续固守“草根”姿态,以边缘之身“反行”颠覆之事来拆解正统学术,以怀疑否定的眼光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加以质疑,在“语境化”进程中将文学和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最终从文本历史化过渡到历史文本化,从政治批评过渡到批评的政治。
一 文学文本“周围的和内置的”社会存在
文化诗学批评学派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本土”,已然成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思潮的翘楚与显学。文化诗学以其对文学文本及其联合体(作品)加以文化释义和政治解读的批评旨趣,践行着对“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交互诠释和双向调查,达成了对盛极一时的形式主义批评和旧历史主义批评的双重超越,凸显出弥足珍贵的学术原创性(academic originality)。是否具有学术原创性曾是美国的消解派(deconstructivism)文艺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评判“西方文学的正典”的审美效果和艺术价值的主要尺码。一种已经成为“历史流传物”的文学作品或文化产品总要对当下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有某种情感触发和美感意义才值得去探究、去追寻,这理应是整个人文学科得以存续的底线要求。于是,孜孜以求地追索文学意义的发掘、培育、构塑和评判成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职责与使命所在。就文学意义本身而言,所谓意义也并不是恒定固化的顽石一块,恰恰与之相反,它永远处于持续不断的无限生成之中,而文学阅读理解活动就是文学形象赓续塑造和文学意义持续生成的阐释历程。
当代美国文化诗学批评观的勃兴其来有自,首先是出于对一度红极一时的“新批评”学说等形式主义批评观的某种厌倦和反拨。“新批评”学说一贯主张“文学就是文学,只能是它自己,而不能是任何其他,所以‘为文学而文学’也好,‘为艺术而艺术’也罢,就理应是天经地义的”,[8]真正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就是要逃离作者与远离读者,为规避作者的“意图谬误”和读者的“感受谬误”的双重侵扰,要坚定地回到文本及作品的“自足体”本身。它执拗地将文学作品的审美语言、内在形式及其有机构成视为文学的本体,注重对单个经典作品的艺术语言和审美意象本身的细读和剔抉,拒斥从文学以外的或传记学或心理学或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等任何其他角度来品鉴文学,从而构筑了一席自为的、超越的、非他在的“文学审美”之地。
这里的“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两个新颖概念是“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威姆萨特(W.K.Wimsatt)和比尔兹利提出来的批评术语。其主旨是反对传统的作者“意图主义”,而主张一种绝对的作品客观主义,认为作品的意义只存在于作品的自我文本之中,存在于作者对文本的有意味的自我阅读之中,不容置喙地一再宣称和服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新批评”派的集大成者韦勒克(R.Wellek)和沃伦(A.Warren)在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中也提出:“任何传记上的材料都不可能改变和影响文学批评中对作品的评价”[9]。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浪漫主义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1912—)在描绘“艺术批评的诸种坐标”时,将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视为各种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要素。他指出,“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10]套用该理论,“新批评”学派的批评倾向是“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只根据作品存在方式的内在标准来评判”。但是只从文学内在标准来批评文学自身,这又如何能确保文学自身定位的可靠性,如何能确保文学批评在批评自身时不“灯下黑”而迷失方向呢?
卢梭曾十分肯定地断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又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这是否就成了人类所必须面对的永恒命运呢?20世纪中叶以来,“新批评”学说以及结构主义批评观等形式主义批评观构筑的“审美意义与文本结构”貌似固若金汤,不曾想怦然遭遇了来势汹汹“要重估一切价值与标准”的解构主义批评观的釜底抽薪。熟识的“人与事”变形、异化,耳熟能详的概念术语面目全非,常规的思维定式改换门庭,文艺批评家们纷纷以各自的方式逃离形式主义的语言囹圄,一切仿佛转瞬间换了人间。然而,面对如此光怪陆离、波谲云诡的批评乱象,牢不可破的桎梏与壁垒被击碎之后,虽重获解放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但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解构批评并未自由多久、风光多远,又深陷文本意义延宕、价值虚无、所指取消的“跌跌撞撞、无家可归”的批评困境。斯时历史语境赋予了批评话语以新情势、新任务、新气象,“沧海争流,方显英雄本色”,当代美国文化诗学批评观就在这种历史参照系下横空出世。新历史主义批评学派极力服膺解构主义批评观对文本敞开性空间和批判性特质的不懈追求,但却又毫不迟疑地抵制和贬抑其无限消解和粉碎一切的偏激主张,转而提出解构与建构并行不悖、和衷共济的文化诗学观念。
格林布莱特认为人类的文化筋脉是一个流动的、不断构建着的意义生成的过程,置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人的本质涵韵也是一个不断塑型的“向美而生”的历程。意义被看作是文学存在的方式,又是文学实现的方式。见证并表征这一“人类的独特的人文景观”的文化架构是一种意义生成和显现的象征,即一种系统的“隐喻性”结构。概括地讲,新历史主义的操作方法可以用格林布莱特的一种努力来说明,即试图探讨“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内置的社会存在”。这种被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Genoverse)称为“文化解读”的批评方式,代表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种文化分析倾向:分析文本赖以产生的文化和体现在文本中的文化。这样,文化与语言,或历史与结构,经由文本的“一桥飞架南北”,成了文化诗学批评方法的两翼。两翼齐飞,这是文化诗学批评观的学术追求。
俄罗斯文论专家程正民深刻指出:“文艺学研究可以从历史出发,也可以从结构出发,但如果是科学的研究,它所追求的必然是历史与结构的统一。文艺学如果从历史出发,那么历史研究的客体就是审美结构;如果从结构出发,那么也只有靠历史的阐释才能理解结构的整体意义,对结构的认识和理解只有通过历史的阐释才能得到深化。”[11]这种把历史的与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认识很有见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或称新历史主义)以具体的批评实践做出了极好的诠释。这一理论学派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它的诗学理论主要以跨学科的文本阐释为特质,格林布莱特也因此被称为“跨学科人文教授”(professor of interdisciplinary culture)和“文化诗学之父”。
二 对“生活世界”的审美观照和人文把捉
缕析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思想产生的现实语境,20世纪文学批评史是各种文艺思潮交汇激荡、腾挪跌宕的历史,也是文学艺术、文化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固有身份、内涵、功能和意义,不断被质疑、重新阐释的历史。各色批评学派之间划定的学科疆界不断消融,“包容他者”蔚成风气,即便针对备受争议的形式主义流派,托洛斯基(Trotsky)在《形式主义诗学流派与马克思主义》中也给予了客观分析和公允评价,“形式主义批评反过来又可以开辟另一条大路,一条通向艺术家感知世界的道路,也有助于发现艺术家个人,或发现整个艺术流派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以社会研究的方式对它进行探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不仅读者,而且这个流派本身也能给自己明确方向,即了解、净化和指导自身。”[12]形式主义(formalism)也同样昭示理论批评家可以寻找到新的航标。
延至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文化经济社会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传统上名目繁多、学科林立的人文精神科学世界业已进入重新组合、互联整合的振荡期和多发期。文学批评理论也已不能够再拘囿于纯粹的文学理论领域,而必须是跨学科多层面的理论研究与现实实践。格林布莱特倡导要把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首先放回到历史语境和文化视域中去,尤其要着力将文学文本以及非文学文本一并放在产生它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政治解读和文化阐发,同时又要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反思“历史记忆”、评判“历史事件”,最终还是要复归当下,激扬文字、指点当代,使其同时秉有阐释者的当代身份。这里,一直游离在正宗文学意指系统之外的非文学文本首次共享了“国民待遇”,也就被纳入了联网统一的社会文化符号系统之中,这种对非文学文本文化性与审美性的关注和阐释极大程度地激活和深化了人们的情志通感和内在认知。在这种理论情势下,文化诗学的开蒙启智和理论反响,意味着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多领域(Multi-domain)的批评观和话语体系的构塑发展业已成为一种理论需求和鲜活现实。
伴随着“从历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事件,从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思想”的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哲学观念的有效整合,思想观念的点滴渗透,汇聚成了思想理论耦合贯通的浩渺激流,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形态跨越了文学、人类学、哲学、宗教学等人文学科和精神科学,凝聚成一种思想的洞见和精神的高蹈。走向批评的多元化(Multi-element of Criticism),重划学科疆界,实现跨学科研究的目的不是在于消弭疆界本身,而是在这种疆界的跨越和重构中焕发文学理论研究新的生命活力,凸现出文本的文化蕴涵。可以说,在寻求关注当代人的生存境遇的语境(the survival of contemporary human beings)和文化转向的大背景(the background of culture turning)下,文化诗学批评观促使生动鲜活的个体生命活动能量汇聚成波澜壮阔的社会“正能量”,从而使文学批评实践和人们的实际生活更加接近和璧合。
在人的社会性存在和实践活动中,逐渐达成的体现在横向坐标意义上的杂多性联系,是一种社会存在和社会力量本身,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这种内置的、居于统摄地位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力量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和“权力形式”,在格林布莱特看来就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和主导权力形式对人类“自我力量和自我造型”的社会催压和文化塑造,也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权力运作。在文学文本的内置“权力场”中,它常常外化表现为自我力量与种种“异在”力量的持续不断的冲突、斗争和重构。特别是到了当代社会形态,人类的文化权力结构和历史叙事形式规约了自身发展的运行轨迹和趋赴归宿,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和生活世界本身。文化就是人类精神的凌厉状态和对世界幻象的深邃理解,也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思想底色和认知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existing form of literary works)是开放的,它通过对生活世界的审美观照和人文把捉,热情拥抱和坦承告白生活的真实和冷峻,重新续接和架构不同个体与人群之间的间性密切关系和有效链接。这种对文学形象与文化现象的整体把握和诗意阐释,直接促成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坦然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化综合研究的领域,这样就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鲜活的元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文学研究的版图和格局。兼具审美性和诗性复合基因的“文学性(literariness)”成为现代文化的魅力形式和精神动力。这种将文学批评实践和人们的文化生活、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勾连起来的理论态度和学术追求,直接导致和护佑着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研究的发生和掘进。
第二节 格林布莱特的学术经历
斯蒂芬·格林布莱特是当代美国学界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学批评家与文化理论家,现为哈佛大学英文系约翰·柯冈人文科学大学教授。他曾任文化批评刊物《表征》(Representations)主编、颇具盛名的《诺顿文选》(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的第二任总编辑、1997年诺顿莎士比亚全集主编、2000年诺顿英国文学全集主编等。格氏涉猎广泛,治学严谨,著作颇丰,研究兴趣遍及文艺复兴文学、新历史主义及西方文化史等领域,但情有独钟的还是他开创并发扬光大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学派。其代表性论著包括《瓦尔特·拉勒斐爵士:文艺复兴的人物及其角色》(Sir Walter Raleigh:The Renaissance Man and his Roles,197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1980)、《莎士比亚的商讨》(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1988)、《不可思议的领地》(Marvelous Possessions:the Wonder of the New World,1991)、《重划疆界》(Redrawing the Boundaries,1992)、《遭遇新大陆》(New World Encounters,1993)、《早期英国戏剧的新历史主义序言》(A New History of Early English Drama,1997)、《新历史主义实践》(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2000)、《炼狱中的哈姆雷特》(Hamlet in Purgatory,2001)、《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Will in the World: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2004)、《权力的即兴创造》(“The Improvisation of Power”in The Greenblatt reader,2005)、《学会诅咒》(Learning to Curse:Essays in Modern Culture,2007)和《莎士比亚的自由》(Shakespeare's Freedom,2010)等。已有《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盛宁译,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什么是文学史》,孟登迎译,原载《批评探索》1997年第23期;《重划疆界:英美文学研究的变革》,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辜正坤、邵雪萍、刘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四部中译本。
从批评理论学派纷呈的“共时性”视角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文化批评界总能听到格林布莱特揭橥新历史主义批评、挑战形式主义,为倡扬“文化转向”鼓而呼的“旷野呼告”(舍斯托夫语)。哈佛大学霍米·巴巴(Homi Bhabha)教授曾高度评价说:“他不仅创建新历史主义批评学派,而且刷新了文学批评的思维习惯。”[13]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文学研究领域,格林布莱特对历史景观和社会图景的文化综合分析,以及对摄控历史事件与历史记忆的意识形态化话语和权力形式的主体性阐发,使他成为当代欧美学界举足轻重的知名批评家与文化理论家之一。诚如王岳川教授在《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一文中指出的,“在‘主体’与‘结构’二元上,形式主义选择了结构和语言,历史主义批评选择了历史的客观决定论,而新历史主义选择了主体与历史”。[14]
从批评理论学术史的“历时性”视角来看,格林布莱特的批评思想最初萌芽于60年代前后,在经历与新批评学派的学术论争之后,80年代初在新历史主义的猎猎战旗下获得理论“学派”地位,90年代末期“取而代之”日渐式微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成为当今最具学术生命力的批评理论之一。在新历史主义批评思想从文本性“文字图像”到历史性“文化产品”批评理论的主体性建构进程中,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义”开创性学说留下了“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方法论印记。躬逢其盛,时为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格林布莱特却不再执着于苦心孤诣地解读经典本身,反而视野陡转,转向了文学文本的外部社会环境的语境圈,更倾向于文本间际“断裂处”的天籁之音。60年代中期赴剑桥大学深造,有幸师从威廉斯,亲沐其治学的风采和思想的光辉,这给身处学业和学术双重困境的格林布莱特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由此奠定了他的主导性批评方向,“在威廉斯的课堂上,我以前接受的文学批评训练所精心排斥的内容——谁控制了印刷出版,谁拥有土地和工厂,文学文本里压制了谁的声音,表现了谁的声音,我们所建的美学价值观替什么样的社会策略服务——重新成为文学阐释的对象”[15]。
当研读到威廉斯对于文化物质性和文学生产性的开创性和缜密性论述时,格林布莱特如沐甘霖,似乎“真实的触摸”到了历史批评的学术兴奋点。这一突变征候明显地体现在他早期的两篇学位论文中:一篇是1965年在剑桥大学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三个现代的讽喻家:沃尔夫、奥威尔及郝克雷》(Three modern allegorist:Wolf,Orwell and Hao Kekei);另一篇是1969年在耶鲁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瓦尔特·拉勒斐爵士:文艺复兴的人物及其角色》(Sir Walter Raleigh:The Renaissance Man and his Roles)。在这两篇长篇专论中,他将批评的触角“向上溯”,延伸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期的纪传体历史文学,聚焦于文艺复兴时期多位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所蕴含的强大的文化生产与社会批判功能。两文的鲜明特色充分体现了他的批评方法论的“首次转向”,从中可以明显看到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论的深厚印迹。
正如伊格尔顿(Eagleton)所言,“历史是文学的最终能指(signifier),正如它是最终的所指(signified)”[16]。以文学话语与历史形态的互涉意指关系为切入点和突破点,格林布莱特提倡“历史转向”的理论呼声,号召美国文学批评重新转向社会与历史的“互构形态”,并身体力行,直接切入到文艺复兴期的传记小说和戏剧创作,在具象化文本的阐释行为与塑造活动中运用“批判中继承”的手法来改造传统历史主义批评方法,致力于搜救和恢复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遮蔽的文学性话语和主体性历史。但是,从格林布莱特批评思想的发展史走向来看,主体性的历史再现和历史性的主体建构才真正是重构历史主义的理论关怀和学术旨趣。不妨参考一下格林布莱特的求学履历,在他主导思想逐步孕育成熟的关键期,他先后进入以希伯来宗教信仰文化起家的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和崇尚科学理性精神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深造。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两所举世闻名的学府的迥异其趣的学术氛围与人文环境,让他深受多重批评思想的激荡和洗礼,最终培育出兼容并蓄的跨学科批评品质。
尚未进入而立之年的他开启了执教生涯,初出茅庐,本想大展身手,但孰料开局不顺,初绽锋芒的他屡遭误解和排斥。虽受此近乎“胯下之辱”,但他仍然坚持自己跨学科的文化诗学原则:“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和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毫不相干的文学视角,我更加不安,但是这也没有使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就赞同、支持各种见解或接受某一种政治套话”[17]。他的执着一念终于换来“柳暗花明又一村”,所幸时过境迁,他的批评观念所遭受的冷遇并没有持续太久。70年代初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在美国学界盛极一时,为新历史主义理论“邻家有女初长成”的蓓蕾初绽和瓜熟蒂落的成熟提供了时代契机。堪称天作之合的是,福柯本人竟也在伯克利分校兼职持教鞭六年,这段机缘巧合恰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崛起和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话语形态的生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深度和文化背景。
格林布莱特以福柯历史谱系学方法论的批评观念为“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传统历史主义的“单声道”倾向:“传统历史批评认为历史存在于文本之外,是文本符号的外部指涉物。这种观念以内部连贯性和协调性为预设前提,尽管时常被视为两三个要素的融合,仍旧被给予历史事实的地位。回避了文学阐释和利益矛盾的问题,这种想象通常作为超越了偶然性的恒定参照基点,文学批评可以心安理得地引经据典。”[18]对福柯历史谱系学的推崇有加,只是徐徐拉开了格氏对传统历史主义的理论改造的大幕,而幕剧的高潮则是对莎学专家蒂尔亚德(E.M.W.Tillyard)及其代表作《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所极力倡导的“理性规则”论的批判。
蒂尔亚德认为:“既然伊丽莎白时代被理性和规则的总体概念所统治,而且‘戏剧就是规则’。那么文学批评的意义就应该是在‘理性和规则’的思想观照下回到历史语境解读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以及读者的反应。”[19]针对蒂尔亚德的传统历史主义批评观,格林布莱特分别从意识形态性权力话语与主体性历史叙事两个维度上接招应战,进而提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理念。在历史的意识形态性方面,他指出新历史主义“涉及权力的诸形式”,其批评实践“向那种在文学前景和政治背景之间作出截然划分的假设挑战,说得宽泛一点,是向在艺术生产和其他社会生产之间作出截然划分的那种假设挑战”;另外,从主体性和历史性的视角,他又强调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旨趣并不在于抽象的普遍之中,而是在于某些个别的偶然性事件、被塑造的自我、特定文化的生成性的规律和矛盾的作用,而那个被阶级、性别、宗教、种族和民族身份等各种文化期待所塑造的自我,在历史的进程中恒定地产生变化”。[20]
在对传统历史主义批评观的“当头棒喝”批判当中,格林布莱特首先从机械的“二分法”中挣脱出来,彻底打破“文学前景”与“历史背景”的二元分立,在历史的话语圈中,不再去刨根问底追查“前景与背景”的前缘出身,历史从幕后背景中走出来,走上前台为文学“站台背书”。历史摆脱了婢女的附属地位,终于可以与文学并驾齐驱而“双兔傍地走,不辨雌雄”了。格林布莱特就此总结道,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整体格局来看,文学文本及作品只是其中的一环,一个相对独立的内置了某种社会存在的网络节点,它并不是单纯的作家创造物或历史语境的反映物,它和文学意指系统的其他综合因素环环相扣、陈陈相因。而在与周边阐释环境的“沟通、商谈”中,更是不遗余力,广为布点,成了文学形态、社会存在与历史语境相互交织与双向构塑的权力产品。
格林布莱特在高举的新历史主义旗帜上,明确打出的是历史性与意识形态性的两块金字招牌,但在探寻凭依权力话语形式来表述纵横交错的历史踪迹的文本阐释实践中,张扬的却是以主体性来重构历史主义的学术旨趣。这也显露出格林布莱特整体思想形态的复杂性、多层性、歧义性,甚至还有交互性。在整个美国文论界热衷于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之时,他却一头扎进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撰写了一系列影响巨大的文艺复兴文学专论,并在这种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活动中,提出了“走向文化诗学”的理论主张。这一主张得到周围一些同仁的积极响应,由此创立了一个超越耶鲁学派解构批评并与之并驾齐驱的、以加州大学教授为主体的文化诗学学派。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称之为“现在作为解释方法的历史转向”。但是,从新历史主义的学术谱系来看,格林布莱特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提出的“文化诗学”话语形态,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理论内涵: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历史的主体性和主体的历史性、阐释的文化性和文化的阐释性。[21]他的文化批评实践集中体现出文化人类学对文化诗学的方法论转向,以及对文化批评范式的整合作用。
第三节 研究文献综述
在西方文论语境中,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两种批评形态互为表里、如影相随。“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始自格林布莱特的《文艺复兴中的权力形式与形式的权力》一书。多利莫尔与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的《政治的莎士比亚》(1985年)也是这一批评学派的力作。新历史主义为什么把焦距对准了英国文艺复兴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特别是莎士比亚这一特定人物?推本溯源,无论是作为一段历史分期,还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文艺复兴”称谓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是后来者用来进行历史描述的概念。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总不可避免要把历史的原来面貌作某种剪裁和改装,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与文化意义。而新历史主义话语批评不仅直面了这一“文化现实”,更对类似于“文艺复兴”这样的诸多概念进行了再理解和再解读。吉恩·霍华德在《文艺复兴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一文中曾就此问题做了专门的分析。
依循惯例,欧美文论界对文艺复兴期文学文本的研究大多沿袭了“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解读方法,而新历史主义的“自我塑造”论无疑给沉闷的形式主义批评的“自我指涉”论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正如同说解构主义意味着对国家机器的颠覆,转为对语言的颠覆,所以在新历史主义的操作中充满着权力、巩固、颠覆之类的意识形态化概念。整个操作规程中,活蹦乱跳的政治术语,比如说表征、霸权文化、再到马克思化(Re-Marxi fication)、历史性元叙事(historical Meta-narrative)、权力、自我间距(Self-distantiates)等,信手拈来,“词不离手,曲不离口”,政治语言表达形式成了基本的言说方式和思维形式。在具体操作上,新历史主义批评思想主要的兴奋点与最终的目标不在历史本身,也不在美学的东西本身,而是仍在意识形态或政治方面,即福柯的“权力—知识—主体”的批评话语策略。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独为擅扬政治学与社会学范畴的工具性概念,它批判性地扬弃了福柯话语权力论的合理内核,以“社会学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之矛还治“语言学的话语工具”之身,虽反戈一击,即便并没有因此带来专注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复位,但至少声音洪亮地喊出了久已“万马齐喑”的异调杂音。粗线条描摹一下从“新批评”学说到后结构主义思潮以来文学批评观念走过的“文学自律与文学他律交替上位”之路,可以清晰地描绘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自身的成长历程和周围环境的反响状况。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犹如一把高悬于文学艺术神殿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极度地扩充了文学的文本间性交际空间,文学文本不再是与社会历史完全隔绝的、自我封闭的孤立性存在。相反,摆脱了自闭症的“文学文本”广交善缘,拥有了历史文本、政治文本、人类学文本等众多追慕者。仅以我国的新时期文学为例即凸显了这一新征象,它紧扣时代主题,反映社会变革,引领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同时也为构筑自己的文化诗学贮备了丰厚的土壤和充沛的种源。另一面正是因为极大地扩容了文学的内存空间,文学拥有了多副面孔、多维特征和多重身份,于是在“泛文化”文本的多种话语解读与阐释实践中,文化诗学批评理论与相应的文化研究“强强联手”又使文学面临着“面目全非、自我消失以至自我毁灭”的灭种危险。正因如此,它一面遭到本是同道的解构主义的偏激攻讦,同时也受到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外围观念“与之划清界限、唯恐避之不及”的迂回包抄。
一 国外研究现状
格林布莱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型〉导论》一书中,首次提出“文化诗学”这一概念:“这种批评的正规目标,无论有多么难于实现,应当称之为一种文化诗学”。但是,这一术语并未马上流行开来。直到1982年,格林布莱特应《文类》(Genre)杂志之约,编选一本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文化论集,并将之称为“新历史主义”,文中他再次使用了“文化诗学”这一词汇,“对文类的研究正是文化诗学的任务所在”。美国文论界如获至宝,很快赋予了“文化诗学”一种包打天下的口号寓意,某种意义上反而阻碍了其在理论框架层面上的进一步发展。正如路易斯·蒙特洛斯所言:“各种各样的被视为新历史主义的实践活动,并没有集结成一个系统的、具有权威的解释文艺复兴文本的范型,并且这种范型似乎还不是可能出现和被希望出现的。”[22]
1986年,格林布莱特在西澳大利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 Australia)作了一次“走向文化诗学”的著名演讲,他对自己一直从事的“新历史主义”研究做出了两项澄清与重申:首先,“师出有名”才是第一位的,起名和正名事宜被理所当然地推到了最前台。他首次正式将“新历史主义”的笼统提法更名为“文化诗学”这一标准称谓,由此才算正式拉开了这幕文学批评戏剧的帷幔,一场有声有色、生动活泼、波澜壮阔、别开生面的文化历史剧开演了;其次,“如何来理论定位”是需要紧接着就跟进的,他明确将文化诗学“界定为一种实践”,斩钉截铁地断言,“就我而言,它根本不是教义”。文化诗学名义上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熔铸了“认识论与历史观”双重维度的文学批评观,是需要在批评活动中必须遵循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理应隶属于思想观念、理论思辨范畴,但在格林布莱特这里,文化诗学被下放到了接地气、读作品的境域中,似乎应验了多么朴素的“只有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的硬道理。一切来源于实践,一切又复归于实践,如此循环往复,才能抵达对批评客体的对象化主体把握和意象化审美理解。文化诗学终于开辟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的文学批评道路。
自兹以后,“文化诗学”才真正挣脱了“新历史主义”的阴影笼罩,这一领域的东方研究者们竞相争用这一术语来描述自己所“专攻的术业”。这其中还有一个很奇特的文学现象,尽管格林布莱特本人更倾心于“文化诗学”这一极富诗情画意的诗意提法,但对这一流派的其他批评家来说,却大多仍有意无意地沿袭使用“新历史主义”这一标签来概括和注解他们所展开的学术建构与批评实践。经常刊载文化诗学批评文章的学术刊物主要有《再现》(Representations)、《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英国文学史》(English Literary History)和《英国文学的文艺复兴》(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等。虽然文化诗学的批评并不能实现历史真实的现实回归和历史真相的大白天下,它只能提供对历史语境和历史文本的又一种阐释,但毕竟又一种新的批评话语形态横空出世、略具雏形。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视角,一种阐释文学文本的历史内涵的特定的方法论,业已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格林布莱特首创的文化诗学批评流派在西方文化境域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一诗学思想主要以跨学科的文本阐释为特质,他因此被称为“跨学科人文教授”和“文化诗学之父”。
实际上,新历史主义本身也遭遇了同样的不尴不尬和不明不白。1989年,《新历史主义》刊物主编阿兰穆·威瑟(H.Aram Veeser)在编撰这一流派的重要理论文章时,就将这一流派定名为“The New Historicism”(新历史主义)。时隔五年,威瑟又编了一本名为《新历史主义读本》(The New Historicism Reader)的论文集,但收入其中的论文却没有一篇是以“新历史主义”为题的。这其中部分缘由似乎可以归结为“都是文本惹的祸”,毕竟新历史主义所关注的庞大的“文化文本与非文化文本共存共荣的”关系网络呈现出庞杂凌乱而又复杂多元的异常混沌态势,“自我力量、本我结构”的理论颗粒溶解在了与异己力量争锋交织的“合力共同体”之中,这样也使其自身陷入了一种自我冲突或理论矛盾之中难以自拔。倘套用一般的理论构建套路来“丈量”的话,这简直是自毁长城,但这或许缘于新历史主义者们压根就不曾想过要建构什么庞大吓人的所谓理论体系。
威瑟在细读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的批评文本之后,认为新历史主义批评思想的一个理论假设是“文学和非文学的‘文本’不可分离地流通”。正因为新历史主义者采用了各种文本之间川流不息地、“不可分离的流通”方式,才使得批评形态各分支间盘踞已久的“天堑”变为通途。这种跨越学科边界、倡导整体性思维方式的研究方法,将审视解读的视角和焦点置于社会文化综合体的关系网中,从而为彻底实现对“新批评”学说、结构主义等形式主义流派只重文本“自足体”结构的超越与扬弃,提供了逻辑前提条件和方法论依据。新历史主义批评思想的诞生以及最终流向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的发展态势绝不是格林布莱特个人心血来潮的应景之作,而是有着自身复杂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历史登场的必然性。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格林布莱特的多部重要专著相继出版,也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与此同时,深度探究新历史主义的各种专论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它们或从学术谱系的新颖视角切入,较为详尽地梳理了美国新历史主义与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渊源;或从文学文本和历史语境的关系出发,从文本、意识形态与历史阐释三个层面对三种情境主义文论进行了深度探讨;抑或从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史的“历时性”视角出发,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背景做了详尽研究。其中,威尔逊(Wilson)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一文认为新历史主义尽得文化唯物主义之精髓与真传,实际上早已成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重要分支。倘硬要分析二者的差异的话,在共拥同一套基因谱系的前提下,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变种和异化。威尔逊主张从学术价值、历史谱系与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将新历史主义打包接收,全盘纳入文化唯物主义的总体框架之中。克勒布鲁克(Colebrook)的《新文学史》一文则认为福柯、威廉斯、布尔迪厄(Bourdieu)、德赛图(De Certeau)等理论家是格林布莱特及新历史主义学派的直接理论来源,民族志、人种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新历史主义提供了整体批评思路和诗学观念体系。
从历史角度来看,美国学界对新历史主义批评观的评判始终充斥着不同学派理论的批评声音。勒翰(Lehan)教授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一文中认为,新历史主义批评话语受到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过多影响,过分热衷于对历史的肆意消解和对文化的过度剪裁,存在“过分意识形态化”等理论盲区。这也是大多数理论形态的通病,只择一端而罔顾其余。他的同事波特(Porter)教授在《历史与文学:新历史主义之后》一书中也极力反对新历史主义在文学研究中过多渗透意识形态和权力意识,认为这种理论杂糅性将导致新历史主义四分五裂、自行消散而走向理论消亡。2000年,凯斯坦(Kastan)在《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fter Theory)一书中明确宣称,“‘新历史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一批评所惯用的‘轶事嫁接法’(anecdotalism)已是臭名昭著,他希望看到一种‘事实更加充分的历史’,但又不要回到先前那已经被废止的传统历史主义的老路上”。[23]布鲁克·托马斯(Brook Thomas)在《新历史主义与其他过时的话题》(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fashioned Topics)中直接断言:格林布莱特的历史批评实践在对后现代文化的挑战中已经再次落入旧历史主义的传统套路,新历史主义学派行将就木。一时众声喧哗、危机四伏,学者们争相“站台发声”为抢得敲响新历史主义的第一声丧钟而奔走相告。
延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终于“柳暗花明又一村”,格林布莱特在其后续重要著作中不断注入格尔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元素和新鲜血液,逐渐明确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指向与理想。与此同时,西方学界在后现代文化历史终结论的喧嚣中,对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的研究兴趣与认识水平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布莱尼甘(Brannigan)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The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和杰诺韦塞(Genoverse)的《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politics of New Historicism)等则指出其仍然属于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历史转向”。对于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出现的“历史转向”与“文化政治”的复杂学理关系,百瑟丽(Belsey)的《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Towards a Cultural Poetics:Theory and Practice)和伽勒尔(Gallagher)的《实践新历史主义》(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等均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基于当前对新历史主义批评过程中出现的‘历史转向’这一批评现象的混乱理解,这里有必要澄清如下一点,那就是斯时的转向绝非历史传统的回潮与复辟,它并没企图推动这么去做,谋求强制性催逼文学批评重新转向传统的社会事件史或作家生活史,但对此也不会袖手旁观”。这么做的初衷是要倡导文学批评开辟一条通向一种基于历史语境和当代反思并驾齐驱、交相辉映的文化批评话语策略,力图在共时性的文本阐释与整体反思中重拾某种历时性的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化线索。
有那么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观大力推动批评活动中的主体性话语重建,许多人因此而给它打上了“情结主义”批评范式的标签。尤其是伴随着海登·怀特携“新史学”的“元历史”研究加盟到文学批评的理论探讨中来,关涉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理论属性的各种争鸣也就愈辩愈烈。其实,怀特在《评新历史主义》《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和《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与情境主义策略》等多篇论文中明确指出,对历史文本中的零散插曲、逸闻趣事、偶然事件等历史内容的“创造性与话语性”阐释,可以被认为具有“情境主义”而非“情结主义”的诗学品质和批评范式,而对历史的各种阐释实践则体现出某种形式主义的“元历史”结构。跟怀特的理论主旨如出一辙,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菲尔德则认为,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必须以文艺复兴期的戏剧评论为“情境”平台,提倡展开文学与文化结构、文学与历史语境、文学与政治权力话语、文学与审美意识形态等基元范畴的总体性研究。
在当下的欧美语境中,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思潮仍处于涨势阶段,虽不至于热闹到人声鼎沸、众声喧哗的地步,但还是吸引了大批仰慕者、追随者趋之若鹜,竞相效尤,整体批评格局呈现出多重话语杂乱交织的纷呈态势。新历史主义倡导批评的主体性理想和实践性品格,从不刻意追求要去架构多么庞大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大厦,这一理论品质也直接导致了它的代表人物们大多不愿意赋予他们的批评实践以清晰的理论定位。由于新历史主义者只是追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文本”的文化阐释和政治解读实践活动,或许是不屑,也可能是无意,他们自身拱手放弃了架构一种明晰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的努力,这一做法明显有悖于积习已久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追求。面对仿佛突然冒出来的这个“黑马”,美国学术界咋口结舌,有些不知所措了,对它的评说毁誉参半,对它的界说更是莫衷一是。直至2005年,佩尼(Payne)教授编辑出版了《格林布莱特读本》(The Greenblatt Reader,Edited by Michael Payne,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其中收录了格林布莱特各个时期的重要论文,囊括了其基本理论内涵,颇多新见,产生了很大理论影响,以至于本身研究文化诗学的学科门类业已成为显学。
躬逢后现代思潮的语言转向、结构转向和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在欧美学界的全面崛起、如日中天是在经历当代“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才得以实现的。正是在对各种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倾向的拨乱反正之中,才逐渐促进当代文学批评整体重新转向了历史文化语境下具有“反本质主义”意味的主体性思想构塑与倡扬。在以反本质主义、反普适主义为主体框架的“解构主义”思想潮流席卷之下,西方文化将欣羡的目光投向了对“元历史”叙事的总体性把握和“共鸣性文本”阐释的审美性观照。以往被深度压抑而“下沉”到潜意识的各种文化成分如沐春风,纷纷冲破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普适牢笼,重获了拥有独立话语权资格的权力象征与身份角色,不屈不挠地最终导向了一种边缘化和权力化的政治美学话语形态。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格林布莱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采用历史阐释和主体建构的批评视角,来寻找经典意识形态问题“断裂”之处的权力踪迹,恢复被权力遮蔽的“他者”声音,也就不足为怪了。
格林布莱特倾慕于以历史文化和主体阐释为批评基点,以揭橥文本的历史性维度和构塑主体的文化性视角重新介入文艺复兴期戏剧与前现代文化的批评领域,提倡以主体建构的历史性和文化性双重视角重新探求与认知西方历史碎片中的社会境况和文化影像。因此,他的文化诗学批评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学科界限和语言隔阂,以文本阐释和文化塑造为总抓手,深刻揭示出历史话语形式与文学话语形式蕴含的共同“诗性”品质。在对文学文本的这种“泛文化”批评中,他极力提倡对文学文本展开“文史哲社一体化”联动的整体性研究,而正是这种在历史语境和文化结构之间穿行不辍与交叉阐释的批评方法,已经使得“文学的历史叙事”与“历史的文化批评”的双向建构问题再度成为当代文论研究的“黄金档期”焦点栏目,逐渐促进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思想的研究旨归向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方法论的历史性转换。
与此同时,欧洲学者们的实践性批评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流派注入了更多的思想资源,也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比利时根特大学的皮埃特斯(Pieters)教授近年来专治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先后推出了《批评的自我塑造:格林布莱特和新历史主义》、《与逝者对话:文学与历史的探讨》等专著。他认为与其徒劳地为新历史主义建构庞大和统一的、机械的“本质主义与普适主义”的理论体系,还不如专门就某位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或某个历史文本展开个体与局部的“小历史”(petti histoire)式个案研究,从而避免重蹈理论研究中好大喜功地构建宏大历史(grand histoire)式叙事体系的覆辙。皮埃特斯对后现代历史主义与文学历史关系、文艺复兴的自我塑型等论域展开了全方位的理论研究,再度掀起了针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流派的研究热潮,无疑是代表着新历史主义批评形态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标志性文论事件。
二 国内研究现状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关心与思索的问题,同样也是中国学者关注与思考的问题,文化诗学批评流派在欧美崛起不久,中国学者就把它译介到了国内文论界。但格林布莱特的论文论著译介过来的并不多,仅零星散见于部分专题研究审美文化等范畴的专业论文或专著中,且多语焉不详。时至2014年年初,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理论研究,国内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仅为120余篇,论著也只有寥寥两三部。可以说,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与文化诗学批评思想一直沉寂于文学批评研究的边缘,其中,针对新历史主义批评思想的阐发与探究又占去了多半壁江山。相对而言,即使是在对新历史主义理论范畴的研究中,关于海登·怀特和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研究又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更遑论专门针对文化诗学批评思想的系统化、科学化、精细化学科式研究了。
虽然早在1993年,格林布莱特的《文艺复兴的自我塑型》导言就被赵一凡翻译并收录于其论文集《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中,《通向一种文化诗学》被张京媛翻译并收录于其论文集《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中,但是,作为新历史主义领军人物的格林布莱特在中国学界却还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西方学者。虽然每逢新历史主义的场合就必然会引用到他的相关论点,但是国内学界针对格林布莱特本人的整体批评思想进行体系化、学科化专门研究的案例却并不多见。直到2012年年底才填补了这项学科建设空白,暨南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王进所著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批评理论研究》,国内大陆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研究格林布莱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专著。但即便如此,在这部篇幅不长的著作中还是把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两种批评学说不加辨别地合并处理,直接导致了专属格氏批评思想的理论特色与实践个性隐而不彰。
当下国内针对中西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的专项研究仍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粗线条勾勒一下进展情况,研究现状与批评流派大致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蒋述卓、童庆炳开创并主导的“本土化”的中国文化诗学批评学派;另一类是以张京媛、王岳川、盛宁、刘庆璋、张进以及新锐批评家王进、傅洁琳等为代表人物,对格林布莱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承继性与开创性研究。这两种批评学派都与格林布莱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批评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形态带来了新的方法和思考,开启了新的探索与发展。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首先梳理一下“本土化”的文化诗学批评观的发展脉络。单从时序上来说,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的弟子、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在国内较早提出了“文化诗学”概念,还以“文化诗学批评观研究”作为选题,一举拿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诗学:文学批评的跨文化视野与现代性进程》,从跨文化视域与现代性语境的双重视角架构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的理论体系。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宗教艺术研究中大胆尝试运用文化和美学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开了“跨学科、跨文本、多领域”综合研究的风气之先。惜乎他仅为疲于应付、应对各种“后”思潮在中国的狂轰滥炸开出了一剂改良主义的温和调理药方,虽然在中西文化“交流、沟通”关系中也强调要重视和实践文化诗学的批评观,但他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复杂语境尚没有充分而清醒的认知,更没有充分重视文化诗学批评观内孕的批判性、实践性和对话性。由是观之,蒋述卓当时只是点了一下题,没能进一步展开和深化下去,停留在了破题阶段。
基本与之同期,童庆炳另辟蹊径,通过对新时期以降中国诗学发展历程的“实证主义”梳理,创造性地宣示和论述了中国诗学在依次完成了审美论、主体论和语言论三个层面的“批评转向”之后,业已开启了文化诗学批评观层面的又一次转向。正是在他的奔走相告和鼓与呼下,众多的文学批评家也随喜转向了译介、运用、重构这一理论形态,引无数才俊折腰、效尤,学人们纷纷投身到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批评实践、谱系架构、学术争鸣等中去,竭忠尽智,力图将文化诗学批评思想构塑成中国诗学的重要运思和实践方式。
至于对于格林布莱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批评理论本身的研究,国内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步,此阶段翻译和介绍的学术著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和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这两本书中收录了一些有关新历史主义经典论述的译文。后渐入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各美其美、美之人美、美美与共”的研究阶段,专著有张进的《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蒋述卓的《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论文成果有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林继中《文化诗学刍议》(《文史哲》2001年第3期)等。它们或是对格氏批评理论中某些论断进行阐述,或是通过再理解、再阐释格氏批评思想的核心批评观为建构“本土化”文化诗学批评理论找到可资借鉴之处。
清华大学的生安锋教授曾以《透视文化、重构历史:新历史主义的缔造者——斯蒂芬·格林布莱特教授访谈录》(Penetrating Cultures and Reconstructing History:An Interview with StephenGreenblatt)的形式专访过格林布莱特教授,这也是国内较早的与美国当代文论大家的“点对点、面碰面”式跨文化交流与跨文明碰撞。在访谈中,格林布莱特首先简要回顾了自己学术生涯中所受的形式主义(Formalism)、传统马克思主义(Western-Marxism)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情况,以及自己是如何逐渐关注与介入文艺复兴期历史文学和莎士比亚研究,从而在莎学研究中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的。作为颇具盛名《诺顿文选》的第二任总编辑,他清晰地指出了《诺顿文选》和英语文学经典的建构和重构(canon formation and reformation)之间的关系,以及文选使用者在经典建构中的作用、经典的筛选机制(selecting system of canon)和其中的商业因素(commercial elements)等。他还谈到自己对缔造文化诗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新构想,以及阅读阐释莎士比亚本人及其作品的新认识、文学批评与政治活动主义(political activism)之间关系的新理解,还有对“历史的文本性”等核心观点的重新阐释与澄清等。最后,格林布莱特还对中国学界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评判与质疑做出了认真的回应。
三 本论著的学术创新点
本论著的学术创新点(academic innovation)择要枚举如下:本论著能够直面格林布莱特批评思想的庞杂性和摇摆性,尤其是其文学文本的批评实践远胜于文学批评观念的批评现实,主要采用从文学文本内部构造、各类文本间性与各批评形态之间等多层面和多维度进行整体比较、总体把握的综合研究方法,从“比较视域”本体切入,立足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文学性和历史性两大“元范畴”问题,兼顾泛文化解读和意识形态化语境两个维度,深刻剖析了格氏倡导一种“新史学转向”视域下走向文化诗学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聚焦于检视展开文本阐释和自我塑造的现实可行性。同时还着重指出了其切合斯时的文化现实需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文本阐释”论、“自我塑型”论、“意识形态”论以及“文本无边界”说等主要批评范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上这些方面均围绕着凸显格氏批评理论中的核心元素,即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观来展开。
梳理格林布莱特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形态架构,立足于其理论的复杂性,细察与明辨其多部类“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杂多关系和“交往”网络,并尽可能加以描述。在厘清格氏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架构时,一般要涉及两个概念: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在当下文艺学界,这两个概念都是颇具争议性的。谈到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往往联想到对文本价值确定性的消解,而文化诗学则常常被理解为对文学意义的泛文化解读。可以说,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分别对应着描述格林布莱特整体学术思想时并驾齐驱的两个维度——史学的维度和诗学的维度。无论是把这两个概念合成一个时,还是单挑出一个来因时制宜各有所侧重,实际上都是试图把格氏的批评思想在文学批评理论的框架内整合起来。作为这种整合中心的诗学,其实也就是文学文本阐释研究。因为无论给格氏批评理论贴上怎样光怪陆离的标签,他真正的学术成就并非提出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庞大理论大厦,而是他所锻造的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合模”分析方法与阐释视角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贡献。
以往每每论及格氏文化诗学的理论架构时,颇多偏重于从新历史主义批评视域来阐发,落脚点定位在断裂的历史观和整体文化观两个层面上。而本论著则着重从破茧而出的文化诗学批评视角来理解与阐释,着力点落实在认识论层面的文化整体观,本体论指向的历史本源观,主体论维度的诗学意义观,实践论向度的“文本无边界”说四个理论原点上。更为重要的是,这四者又并非截然分立、孤立存在;相反这四者一以贯之在文本阐释的全过程(或言之:贯穿在自我力量的形塑和自我造型的重塑过程中),同时又架构起了贯通四者的桥梁,那就是本文一再凸显的思维范式与批评空间:自我造型的形塑流程。这样上述“多极”便构成了格氏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多元体系和多维世界。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思想恰是从格林布莱特开始,才具有了世界性的学术影响,这与其独特的理论风格息息相关。自我造型,文本的“惊叹”与“共鸣性”的诗性阐释,以及对文本意识形态权力运作的多层面解读,都是格氏作为新历史主义者的个性化阐释和理论构建,体现了富于创见的理论深度。又鉴于新历史主义这一“新史学”批评观,为格氏的文化诗学批评观准备了充沛的思想渊源和方法论依据,如何在准确、客观和明晰地界说两者的内在关联的逻辑前提下,重点突出文化诗学批评观的特异性和独到之处,便变成了现实之需和理论之基。本论著不仅清晰地关注了这一重要事项,而且倾其所有打造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特有的主轴方面,体现了一定的逻辑思辨性和学术原创性。
本论著秉持“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各美其美而又美美与共的阐释理念,首先采信“情境”式文学批评方法,即批评主体主动“沉降”到文化事象和文学文本典籍中,从文本“原始痕迹”和作家的“客我”批评视角来还原和注解那些“共鸣性”文化文本,进而用“厚描”式粗笔勾勒出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形态的来龙去脉和精髓要旨,外化表征为批评主体对作家和文本的本源认同和原创剔抉。然后,“转换一下说法,接着说”,改用“情结”式文学批评方法,“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大胆跨越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疆界,将“文化解读与历史叙述”“政治话语与权力结构”和“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等多重架构内在勾连起来,弥合无间地构塑成“想象的造型共同体”和“主客融合的文本联合体”。毕竟,一种批评理论能具有开拓性价值和意义,打开了一种文学文本的阐释思路,构建了一种新的批评范式与思维方式,抵达“片面的深刻”已属不易。
尽管中西文化诗学纠葛着这样那样的差异性和共同性,但都贯穿始终着一条加粗的理论主线,它们的批评实践活动也是紧紧围绕着这条主轴而运转、运作的,那就是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批判性、实践性、自我反思性以及对权力结构的敏感性,和对意义建构及对话性公共空间的倍加重视。一方面在嵌入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之时,在文本结构和文化解读之间穿梭,为不断反思人类文化行为和重建社会批判和意义建构的想象空间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渗透到中西文学、文化甚至政治研究之中,重新塑造人们评判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政治权力、文本与历史、语言与意义等思想观念问题的概念术语、运思方式和实践范式。唯有直面文化诗学复杂多元的批评话语形态及其应对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各类质询的批评实践,才能创生我们在“文化诗学之后”(After the Cultural Poetics)的批评新愿景,从而开创一条更加宏阔与诗意的文学批评道路。
第四节 本论著的逻辑线索和基本架构
实际上如同很多批评流派的遭际一样,涂抹着同一标签的新历史主义及文化诗学批评学派内部也是自说自话,杂语横生,各行其是,并不存在什么用同一个声音来发声的情形。不同批评家的主打观点也各有侧重,千差万别,而新历史主义及文化诗学批评观也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没有确切指涉的措辞”。考虑到这样“个体异于整体而又优于整体”的独特的理论特征,要想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思想观念的深度开掘有些突破和创见,就有必要摆脱传统的学派式的研究套路,同时力避批评范式中宏大叙事模式的“本质主义与普适主义”倾向。正如布莱尼甘所说,“不依靠某种理论家的作品就无法定义某一批评实践,为了寻找共同的特征而压抑不同实践者之间的实际差异,由此而来的各种定义是不准确的,这些共同特征的准确性也是受到质疑的”。[24]如是看来,多数情况下,某个批评家个体的个性特征与实践特色同所属的批评流派拥有的共同特征与实践共性之间,既非一般意义上的部分与整体的种属关系,也非互为兼容的特殊与一般的真包含关系,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激化成剧烈碰撞或激烈冲突。当此之时,在具体的批评实践活动中,便陷入了“鱼与熊掌如何选择”的难题,是为了保有理论虚幻的共性与一致性而牺牲个体特征的准确性,还是相反呢?
与其挖空心思去罗列、“点赞”某一流派的不同批评家的集成观念,或是以某些批评家的复调和声去“泡沫化”这一批评流派的理论张力和话语空间,倒不如收束视野,握紧拳头,重拳出击,锁定某一个体文论家本身的批评思想架构,从而达到“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整体研究目的。因此,本论著以格林布莱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观为研究个案,结合格林布莱特的具象化批评实践活动,通过重点分析他的经典性论断和代表性论著,逐步演绎出其批评思想的来龙去脉和精髓要旨,目的在于从理论的上游源头上厘清与把握文化诗学的学理思路和实践走向,揭示出“文化的主体性”与“主体性的文化”,“历史文本化”与“文本历史化”,“权力话语化”与“话语权力化”等多重互文批评范畴的文化品格、历史语境和政治内涵,竭心尽智力图将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观的思想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学术峰巅。
与此同时,重估和重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与理论框架,并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理论价值与历史局限,一方面对于较为全面地宏观把握当代文学批评的核心理念和最新批评思想的新成果、新发现具有开拓性意义;另一方面对中国“本土化”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当代阐释和主体重建无疑又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启示价值和历史观映鉴意义。我们有着充沛的理由与依据来确信,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理论一旦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学批评生态,势必助力于其自身批评实践的疆域扩展与理论完善,在“立场自醒、理论自觉和价值自省”的思想基础之上,强力拉动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向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生态型批评”(ecocriticism)理想不断靠拢,从而保持一种涵养传统与吸纳新知“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批评态势。
本书共分八个部分。
绪论部分对本论著的选题缘起、论域范围、选题思路、传主学术经历、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以及基本概念和范畴界说作了粗线条的梳理和勾勒,并撮要描述了本论著的逻辑线索和理论架构。
第一章主要交代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的学术渊源,其中包括第一节——该批评形态的思想来源;第二节方法论背景——方法论视野下与格尔兹“文化人类学”的同质异构性;第三节认识论背景——认识论视野下与伽达默尔、利科“新诠释学”的内在互文性;第四节价值论渊源——价值论视野下与詹姆逊“政治诗学”的同源异流性。
第二章是本论著的核心部分之一。重点条分缕析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的五大理论范畴,分别为:第一节“新历史主义”批评视域;第二节认识论层面的文化整体观;第三节本体论指向的历史本源观;第四节主体论维度的诗学意义观;第五节实践论向度的“文本无边界”说。
第三章是本论著的最为核心部分之一。较为全面、完整、详尽地阐述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文本阐释”论,主要蕴涵五个层面,分别为:第一节文化诗学视域中的文本阐释理论概说;第二节文本阐释理论的“比较视域”本体;第三节碎片的“共鸣性文本”历史观——在“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的双向阐释中重塑文本与意义之间的互动图景;第四节整体的文化观,或称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对话:倡扬探究文学形态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语境;第五节诗性的“文学文本”阐释或称审美的诗学观——文本阐释理论的当代诗性审美形态。
第四章是本论著的又一个核心部分。详述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的“自我塑型”论,主要涵盖五个层面,分别为:第一节文化阐释的发生学景观和诗性蕴含;第二节“文本联合体”的文化表征和哲学表达;第三节文化生产流通的“社会能量”转换论;第四节“自我塑型”论的话语架构及诠释实践;第五节跨文化境域中“公共文化镜像”的自我塑型。
第五章概述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形态的“意识形态批判”论,分别从五个方面来展开:第一节“文化解读”的“意义生成说”视域转换;第二节语境化的“思辨的理解”作用力场;第三节意识形态化的“凝视的理解”话语机制;第四节权力结构的“隐喻性”表征形式;第五节从“文本间性”理论到“主体间性”实践的“旨趣”转换。
第六章主要探究了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多元化的批评范式,分析了若干具象化的文本阐释实践样式,分别为:第一节以文学文本阐释实践为主轴的多元化批评范式;第二节“情结”文化批评范式的“知识论转向”;第三节比较形象诗学视域中的“共鸣性文本”;第四节主要是具体运用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观,落实到文化诗学境域中来析述文学意义的审美阐释实践模态。
本书以结语收束全文,在粗略交代当下世界文论面临的整体形势和共同任务的总体格局下,简要概说了对格氏文化诗学批评理论与话语体系的整体性评判和多维追索,同时也对文化诗学批评观念史的各个历史分期作了终结性界说。作为兼容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维度的“国别体”文化诗学批评学派中翘楚的“中国形态”压卷出场,从而为文化诗学整体形态平添了更多中国元素与中国气派。与之并行不悖的是,在此进程中不惟培育了更其浓烈的“问题意识”,预设了更多合模的“文本阐释”可能性,而且预留了更加宏阔的“理解”思维空间。
注释
[1]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2]盛宁:《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0期。
[3][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4][美]哈罗德·阿兰维瑟尔:《新历史主义》,陈华生译,罗特里奇公司1989年版,第15—36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9—80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9—80页。
[7]刘志丹:《交往如何可能: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新探》,《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8][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页。
[9][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页。
[10][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王宁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1]童庆炳:《文化诗学: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结合》,《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12]傅洁琳:《试析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理论的语境和方法》,《齐鲁学刊》2010年第4期。
[13]王进:《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批评理论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14]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15]王进:《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批评理论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16]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London:Verso,1978,p.24.
[17]Stephe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4-49.
[18][美]斯蒂芬·格林布莱特:《什么是文学史》,孟登迎译,《批评探索》1997年第23期。
[19]王进:《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批评理论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20]Stephe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4-49.
[21]王进:《美国文化诗学的历史轨迹:格林布莱特批评理论评述》,《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2][美]阿兰穆·威瑟主编:《新历史主义》论文集,英译本见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89。
[23]盛宁:《新历史主义还有冲劲吗?》,《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24]John Brannigan,The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London:Macmillan,1998,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