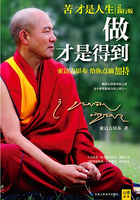就在召开常委会的这天晚上,贾丕仁白天下乡,晚上回C3楼休息。他一面密切注视着常委会的讨论情况,一面考虑着如何应对史大山搞的那个财务审计。
潘婷婷伺候他痛痛快快洗完澡,他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潘婷婷问:“今晚还有事吗?”他说:“今晚我还有要事处理,你先回避一下,等我处理完了,我再打你手机。”潘婷婷会意,立即关了门出去。
潘婷婷一走,他便将电视机关掉,独自在客厅里慢慢踱步。他有关起门踱步思考问题的习惯。每逢遇到重大问题或难题,他总要一个人关起门来思考,将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解决的途径和办法,以及利弊得失,都要考虑得清清楚楚。经过反复分析比较之后,择其优而从之。最后痛下决心,付诸实施。
眼下,他对史大山在古城遗址上大兴土木可能遇到的麻烦和问题,以及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反复思考和评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史大山的失败是确定无疑的,也是无法挽回的!而自己正可利用史大山的这个重大失误,推波助澜,将他推入绝境!如此一来,他便可从史大山搞的那个财务审计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彻底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
其实,贾丕仁早就知道,史大山正在酝酿东城老街改造计划。那是史大山刚来不久,在一次市长办公会上,讲到他去东正街和南正街遇到的尴尬,说这两条老街已到非改造不可的时候了。当石松把这个情况告诉他时,他暗自高兴,心想,“你史大山如果真要搞,算是撞到枪口上了!”那时,他对史大山还并无恶意,不过是想看这位新市长的笑话罢了。自从史大山搞了那个财务整顿之后,他感到自己受到严重威胁,才不得不重新启动他的接班计划。现在,他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一举将史大山除掉!
当然,凭心而论,城区东扩和改造两条老街都是好事。他任市长时,也曾试图去做,但随之而来的麻烦和问题,让他退缩了。他不能为干成一件事而冒个人风险,甚至丢了自己的乌纱帽!这次史大山要干,是他一心要营造政绩,根本不知其中的难度和风险。对这件事,他本可冷眼旁观,让史大山干去:干成了,有他一份功劳;干砸了,是他咎由自取,怪不到他头上。伹现在的史大山,已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苦苦思索了许久,终于想出一条双管齐下的妙计。他自认为,此计一旦实施,将给史大山致命一击。他正要打电话给侯三元,问常委会开会的情况,不料侯三元却先打来。他问:“情况怎样?”
侯三元说:“会刚开完。史大山的计划好不容易通过了!”
“怎么,争论很激烈?不过这样也好。如果通过太顺利,反而会引起他的怀疑。”
“下一步该怎么办?”
“还是静观其变吧!”
“宇文生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向你汇报。你见不见?”
“他要汇报什么?”
“大概与史大山的计划有关吧。听说他在市长扩大会上放了一炮,搞得史大山下不了台。他在会上挨了史大山的批评,是不是要找你诉苦?”
“那就让他来吧。”
贾丕仁放下电话,心里一阵高兴。他本要找宇文生授计,不想他自己送上门来,正好借机点拨一下。
宇文生是他来乌市前就认识的。一次,他刚被提拔为地教委副主任,行署抽他临时带一个检查组来乌市检查血防工作。当时还是市宣传部副科长的宇文生参加了接待,负责安排生活。宇文生陪他到南部乡镇检查疫情,一路上走村串户,查看湖区、河道灭螺情况,检查人畜饮用水源和厕所等。一连跑了三天,宇文生鞍前马后,跑上跑下,生活安排得十分周到。检查组离开时,他力促部里拿出一笔钱,买了不少礼品送给检查组,最后换得检查组对乌市血防工作的放行过关。这次接待,让贾丕仁对宇文生产生了好印象。
贾丕仁调来乌市后,暂住市沁园宾馆,闲来无事,自然想起了宇文生,便打电话叫他来聊天下棋,有时也要他约人来陪他打麻将。后来,贾丕仁接来老婆孩子,分的住房恰好同宇文生门户相对,宇文生便趁机同他接近,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两人的关系便愈亦密切。在一次闲聊中,宇文生得知,贾丕仁也是省大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只不过比他早一届。他便当着贾丕仁的面,称他老同学、老校友。这让贾丕仁听了很不高兴,也很不自在!两人的关系再好,也总得有个上下之分,尊卑有别吧?宇文生不识时务,着实让贾丕仁对他有了看法,认为这人很不自量,不懂官场规矩,平时也就淡淡地应付。但宇文生毕竟主动与他接近,在那段人生地不熟的难熬日子,同他一起消磨难耐的时光,加之他也有意拉一批人起来为自己立脚,于是借机将宇文生提为科长,后来又让他当了文化局长。
他现在就想,宇文生虽不十分可靠,对自己却是忠心耿耿。再说,他毕竟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有恩于他,他理应为自己效力,即使将来遇到什么情况,也不至于反水。这么想过之后,他打算先耐心听听宇文生的牢骚,然后适当加以点拨,以期为己所用。
没过一会儿,宇文生便匆匆赶来。他喘息未定,就抱怨说:“史大山太不讲理了!不让人把话说完,就强行拍板!他还不指名地敲打我,要我同市政府保持一致,不要忙中添乱。你说说,这哪里是发扬民主?明明是压制不同恴见!我这个文化局长怕是再难当下去了!”
贾丕仁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坐下,又为他倒了杯纯净水,这才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你身为文化局长,如果该说的不说,那倒是严重失职;说了,他不听,那是另一回事。我看你不必为此烦恼。我听说,周国民在会上同你吵得很厉害?我看这也很正常。他作为城建局长,抓城市建设是他的职责所在,他也没有错嘛。我看你们俩争得好!这就使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他们说,你和周国民是我的人,一切都听我的。你们都长着一颗脑袋,又是堂堂一局之长,怎么会事事听我的?你说是不是?”
贾丕仁如此一番表白,既笼络了宇文生,又同他保持了距离,这就举重若轻,能更好地做宇文生的工作。他打量了一眼宇文生,见他的气消了许多,于是话题一转,说:“不过,我得提醒你,有件事你不得不防!如果史大山一定要蛮干,上级主管部门必然会追究他的责任,到时,你这个文化局长也脱不了干系!你打算怎么办?”
宇文生一听,顿时有些紧张,喃喃地说:“那可怎么办?我不是事先没说,可说了他不听,叫我有什么办法?!”
贾丕仁站起身,背剪双手,一边踱步,一边装着为宇文生分忧的神情,思索一会,趁机开导说:“这事仅仅在会上说是不够的!上级怎么会知道,你在会上发表过反对意见?应该通过适当途径,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这样既不失原则,又有据可查,即使今后出了问题,你也完全没有责任。你说,这岂不是更好?”
宇文生一时没反应过来,说:“我本来要向文化厅反映的,可是史大山当面敲打我,我怎么敢反映?”
贾丕仁冷冷一笑:“如果向文化厅反映,别人马上就会知道是你干的!史大山也会抓住你不放!你就不能通过别的途径?”
宇文生很是茫然。他一时想不出什么别的途径,又好像想到什么,却苦笑一下,又摇了摇头。
贾丕仁见宇文生一副榆木脑袋,有些生气,便下了逐客令:“你是宣传出身,你回去好好想吧。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
宇文生没有讨到答案,只好起身告辞。贾丕仁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这才疑惑地离开。
贾丕仁回到沙发上坐下,点烟抽着,仔细回想刚才同宇文生的谈话内容,觉得天衣无缝,毫无破绽,而宇文生实在迂腐,不禁哑然失笑!
打发走宇文生,他又马不停蹄地打电话把沈德松叫来。他要同沈德松好好谈谈,从源头上把史大山引来的那股祸水堵住!
沈德松年纪五十开外,宽额头,尖下颏,小眼睛,脑门光秃,外表酷似某影视明星。他任审计局长已有多年,为人圆滑世故,人称“不倒翁”。他的为官之道是:唯上是从,唯命是听。只要是书记说了的,他会不折不扣地去做。这次市政府换届,论年龄,他本应退居二线,但靠着贾丕仁的关照,他仍留任。因此,他对贾丕仁更是恭敬有加,俯首听命。
他不知道,贾丕仁半夜打电话找他何事,但隐约猜到,可能与这次企业审计有关。这次开展企业审计,本来史大山已对他提出要求,要他依法审计,不徇私情,对审出的问题如实上报,不得漏报瞒报。但他对史大山的要求内定了一套标准:大问题端出慎之又慎;涉及个人的问题概不提及;上报前向贾丕仁请示。现在,已开展的几个企业基本结束,初步结果已经出来,正在撰写结论报告,不久将正式提交市长办公会讨论。此时,他正好去向贾丕仁汇报。
贾丕仁待沈德松落座后,扔了一包烟给他,自己点上一支,抽了一口,便问:“对几个企业的审计,情况如何?”
沈德松答道:“笫一批开展的四个企业已基本结束,正在写结论报告。”
“主要查出了哪些问题?”贾丕仁紧问。
沈德松想了想说:“各个企业不尽相同,但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财务管理混乱,企业法人的权力过大,得不到制约,瞎开支、乱补助、挥霍浪费的现象严重。从已审计的四个企业看,都设有小金库,资金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这些小金库,主要供厂长经理请客送礼拉关系和个人挥霍。有的报账打白条,有的干脆一句话,连个白条也没有。二是企业生产和经营都存在对内和对外两本账:对外是假账,往往虚报浮夸,虚盈实亏;对内的账,主要由法人掌握,对外绝对保密。三是个别企业亏损严重,甚至业不抵债,面临破产倒闭的危险。”
贾丕仁问:“最严重的是哪些企业?”
沈德松答:“是钢管厂和盐化厂。”
贾丕仁问:“主要是些什么问题?”
沈德松说:“钢管厂资不抵债达一千多万,已停产一个多月,职工有三个月没发工资。这个厂财务管理混乱,除厂长李小怀可以任意开支之外,其他副厂长、车间主任和科室负责人都有权开支。”
“有没有涉及个人的问题?”贾丕仁问。
沈德松立即明白贾丕仁问话的意思,便小心回答说:“从账面上还看不出李小怀有什么问题。但职工反映,他拿职工集资款买小车、建别墅,还借出国考察之名,卷走巨额资金到国外。现在集资款到期无法偿还,职工意见很大。”
“你对集资款查过吗?到底有没有问题?”贾丕仁紧问。
沈德松答:“从账面看,有一千二百多万,都用在了购置设备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贾丕仁问:“那职工为什么对李小怀有意见?”
沈德松支支吾吾:“这已超出了我们审计的范围。不过,职工向我们递交了一封关于李小怀贪污的检举信。”
“拿来我看看!”贾丕仁伸手要检举信。
沈德松忙说:“我已交给了史市长。”
贾丕仁很生气:“到底举报了哪些问题?为什么不交给纪委或监察局?”
沈德松急忙解释:“这封检举信我看过,就是我刚才汇报的那些问题,全是捕风捉影,并无真凭实据。我想,这样的材料一定是满天飞,才把它交给了史市长。”
贾丕仁这才点了点头,没有深究。又问:“盐化厂的情况呢?”
“盐化厂的问题主要在业务人员身上。据我们查账,全厂外欠货款有四千多万没有收回。现在厂里流动资金短缺,马上面临停产的危险!”沈德松回答说。
贾丕仁问:“有这么严重?”
沈德松说:“据厂长黄世才汇报,主要是三角债问题。不过据我们调查了解,全厂八个业务员,个个都有大笔货款没有收回,有的少则几百万,有的甚至多达一千多万。职工反映,这些业务员拿公款在外面搭天桥做生意,都买了私人别墅和小车。”
“能不能说得具体点?”贾丕仁问。
“具体材料我没带来。”沈德松不肯明说,支吾其辞。其实,他早已知道,欠货款最多的是贾丕仁的胞弟贾小仁,他一个人就欠了一千二百多万。职工反映,贾小仁与人合伙,在山西一个煤矿买有股份。
贾丕仁心里明白,沈德松不肯当面说出贾小仁的问题,只好再问:“你们还查出了盐化厂哪些问题?”
沈德松迟疑一下,仍硬着头皮说:“我们还间接查出黄世才有个秘密小金库!”
“怎么个间接法?”贾丕仁带着质疑的口吻问。
沈德松轻声说:“是工会主席胡为家偷偷向我反映的。他还向我写了一份检举材料,我没带来。”
贾丕仁瞪着沈德松问:“你就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显然,他不想让沈德松去追查这个问题。
沈德松赶忙说:“这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我不会去插手的!”
贾丕仁点了支烟,慢慢抽了一口,盯着问:“怎么我听说,你已将钢管厂和盐化厂的情况向史大山汇报了?”
沈德松一听,立即有些紧张,赶忙解释说:“前天晚上,史市长打电话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要我汇报审计情况。我毫无思想准备,只好把查出的初步情况向他作了简要汇报,并没有谈及具体问题。”
“是这样的吗?”贾丕仁质疑道。
“我确实没有谈具体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沈德松发誓说。
“比如盐化厂的小金库,你确实没说?”贾丕仁怒眼圆睁。
沈德松被逼急了,站起来,郑重表白说:“如果你发现我向史大山反映了黄世才私设小金库的问题,你可以马上撤了我的职!”
见沈德松如此惶恐不安,贾丕仁缓和语气说:“算啦!只要你不主动去查就行。至于别人怎么反映,就让他反映好了!”
沈德松仍不放心地问:“若是史大山知道盐化厂有个小金库,要我去查,怎么办?还有,盐化厂那些业务员的问题,要不要向史大山汇报?”他后面还有一句,如果史大山问到你胞弟贾小仁的问题,怎么办?只是他不敢说出。
贾丕仁断然反问:“你是审计局长,难道这样的问题还要问我?”
沈德松只得点头称是。
这时,贾丕仁起身,踱着步,一字一顿地说:“史大山搞的这次所谓企业审计,本来就没有向市委请示,是他个人的擅自决定!我看他是另有目的!你是明白人,就不用我说了。但是,你作为审计局长,一定要心中有数,不要跟着史大山的指挥棒瞎起舞!从现在起,你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对审岀的问题随时向我汇报,对拿不准的问题要及时请示,不要自以为是,自作主张;二是要严格把关,对该端的问题就端,不该端的问题坚决不端,特别是对涉及个人的问题,更要慎重;三是审计结论报告出来以后,先交我过目,才能向市政府那边上报。”
说到这里,他打量了沈德松一眼,见他毕恭毕敬地做着笔记,才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说:“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些要求?目的只有一个:防止有人钻审计的空子,借机整人,把企业搞乱;同时,也防止审计失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你知道,我以前在市政府那边,对这类问题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既为企业,也为个人,留有充分改正的余地。这样不是很好吗?如果由着史大山的性子来,存心去挖企业的什么问题,还不把企业搞乱,把人心搞散?除此之外,能有什么好结果?”
听了贾丕仁这番话,沈德松这才完全明白,贾丕仁此次找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从审计这个源头,把所有重大问题堵住,让史大山无计可施。但他仍不免担心,如此一来,他夹在中间不好做人!不过他知道,只有贾丕仁才是他的真正靠山。他不得不表态说:“你放心,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去做!”又疑惑地问,“如果查不出什么大问题,那史大山不是怀疑我搞假审计?”
贾丕仁把手一挥,断然说:“听我的!”
沈德松瞪大眼睛说:“好,我听你的。”
他接连找了两人谈话,一头是点火,一头是灭火。点火点得奇妙,灭火灭得隐秘!他自以为得计,心里感到踏实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