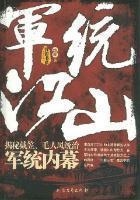第一卷 在后方
“他们就这样杀了我们的斐迪南。”女用人告诉帅克。几年前,当军医审查委员会鉴定帅克为白痴后,他就被退伍还乡,在家以贩狗谋生,专替奇丑无比的杂种狗伪造血统证明书。
除了干这档子买卖外,帅克还患着风湿症。这时,他正用风湿油搓着他的膝盖。
“哪个斐迪南呀,米勒太太?”帅克问道,一面继续搓着他的膝盖。“我认得两个斐迪南。一个是给杂货店老普鲁什当用人的;另一个就是斐迪南·柯柯什卡,他是一个捡狗屎的。这两个随便哪个被杀掉我都没什么可惜的。”
“可是,老爷啊,死的是斐迪南大公呀。就是住在科诺皮什捷的那个,又胖又虔诚的那个呀。”
“我的天哪!”帅克尖叫了一声,“事故在哪儿发生的?”
“在萨拉热窝,老爷。用的是左轮手枪。当时他正带着自己的大公夫人坐着小轿车兜风呢。”
“多神气呀!米勒太太,坐的还是小轿车呀!当然哪,也只有像他那样的阔老爷才坐得上啊。可他没料到,坐一下小轿就会出这事。还是在萨拉热窝哩,这不是波斯尼亚的省会吗,米勒太太!那大概就是土耳其人干的了。原来我们就不该把他们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抢过来。你瞧,结果怎么着,那位大公大概受了好半天罪才死去的吧?”
“大公当场就中弹身亡。听说他们有一帮子,老爷。”
“那就对啦,米勒太太,”帅克说,这时正搓完他的膝盖。“打个比方,要是你想去干掉一个大公或皇帝老儿什么的,你肯定得找些人商量合计。常言道,人多智广嘛。这个人出个主意,那个人再献个妙计,就像我们的国歌上说的,功德就圆满了,事业马到成功。要紧的是你得瞅准了那位大人的车子开过来的那一刹那。”
“这人朝他身上开了一枪还是几枪?”
“报上是这么说的,大公成了个筛子。”
“活干得真麻利,米勒太太。如果让我去干这档子事情,那我得去买支白朗宁。这种手枪看上去像个玩具,可是只需两分钟,就可以打死他二十个大公,不管他是瘦的或胖的。不过,关起门来说,米勒太太,胖的还是比瘦的好打些。人们都还没忘记当年葡萄牙人是怎样枪杀自己的国王的。那家伙就是个胖子。好啦,我现在要去杯杯满酒馆啦。”
杯杯满酒馆就只有一位顾客,他就是干密探的便衣警察布雷特施奈德。老板巴里维茨正在洗着各种玻璃杯盘。布雷特施奈德想方设法要和他扯点正经事,可就是谈不起来。
“今年这夏天蛮不错的啦。”这是布雷特施奈德郑重谈话的前奏。
“不错个屁。”巴里维茨回答说,一面将杯盘放进橱柜里。
“他们在萨拉热窝可给我们干了桩好事啊。”
“在哪个萨拉热窝呀?”巴里维茨反问了一句。
“是波斯尼亚的那个萨拉热窝,老板先生。那边他们枪杀了斐迪南大公。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向来不过问这类鸟事。”巴里维茨先生非常小心谨慎地回答,一边点上他的烟斗。“现如今,谁要是跟他妈的这类事情搅和在一起,那谁不就是去找死吗。我是个买卖人,顾客进门要喝杯啤酒,那我就去给他倒一杯。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或者死了个什么大公呀,跟我们毫不相干”
布雷特施奈德没再说下去,他四下望了望空无一人的酒馆,很感失望和扫兴。
“这里曾经是挂过一张皇上的像的,”过了一会儿他又找起话茬儿来说,“而且就是如今您挂镜子的地方。”
“嗯,说对啦,”巴里维茨回答说,“可苍蝇总在画像上拉一摊摊的屎,我只得将它挪到房顶与天花板之间的顶间处,那儿最保险。”
“萨拉热窝那边肯定糟透了,老板先生。”
“嗯,波斯尼亚和黑塞奇维那的气候向来都热得要命。记得我在那边服役时,他们都得要往我们长官的头上搁冰块的。”
“您在哪个团服役来着,老板先生?”
“我可记不住这类屁大的事儿。”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说。
这位便衣警察布雷特施奈德就再也不吭一声了。他阴沉不快的表情直到帅克的到来才变得好转起来。帅克一跨进酒馆门槛,就要了一杯黑啤酒,说道:
“维也纳今天也披了黑纱了。”
布雷特施奈德的两眼立即放射出希望的光芒,简短地接上一句:“科诺皮什捷也有十幅黑纱披挂在国旗两旁。”
“该挂十二幅。”帅克足足地喝了一大口说。
“您为什么认定要挂十二幅呢?”布雷特施奈德问道。
“好记呗!也好算钱;成批成打地买肯定便宜多了。”帅克说。
又是一阵沉默。直到帅克用自己的一声叹息才将它打破:“唉,怎么就真的翘了辫子,归了西天啦。眼看就要当上皇帝老儿怎么就一命呜呼了呢!”
“萨拉热窝的事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布雷特施奈德把话题又扯了回来。
“您错了,这是土耳其人干的,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个省才干的。”于是,帅克就奥地利当局对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发表了一通宏论。
“老板先生,”布雷特施奈德感到有希望能从这两人中抓住一点话柄。“可是您不得不承认这档子事情对奥地利是个很大的损失呀。”
帅克替老板回答说:“这无法否认。而且是个惊人可怕的损失。他斐迪南可不是随便哪个二百五都能代替得了的。可他似乎应该再胖点就好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布雷特施奈德更来劲了。
帅克甚为满意地回答道,“我的意思是,他要是长得再胖一些的话,那他肯定会在这档子事之前中风而死,也就不说死得这样丢人现眼了嘛。他好歹也是我们皇帝老儿的叔大人呀,他们就是把他给毙了。报纸整版整版不谈别的,专谈此事,唉,总之是够丢人的了!”
帅克大大喝了一口,接着又说:“您认为皇上会忍气吞声吗?那您对他就太不知晓了。同土耳其人开战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哼!你们竟敢杀了我的叔大人,那我就先给你一嘴巴子。仗是一定要打。塞尔维亚和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不知谁要挨一顿好打。”
当帅克预卜未来的时候,他的神态着实壮观动人。他满脸一片纯真,焕发着热忱。对他来说,一切事情是那样的清楚、明白。
“可能,”帅克继续描绘着奥地利的前景,“我们同土耳其开起火来,德国人就会来进攻咱们,因为德国人同土耳其人是绑在一起的,他们都是些下流胚子。但咱们也可跟法国联合呀,他们从一八七一年起就看德国不顺眼。等着看热闹吧。仗那是要打的,更多的我就不说了。”
布雷特施奈德站起身来庄重地宣称:“更多的您也甭说了,您跟我到过道那儿去一下,该我给您说点什么了。”
帅克随便衣警察来到过道,一个小小的惊异在此发生了:
刚才还是他邻座酒客的人,现在却掏出秘密警察的双头鹰证章宣称要逮捕他,并立即送往警察署。帅克竭力想解释,准是那点事上使这位先生产生了误会,而他是个全然无罪的人呀,连一句可能得罪、伤害别人的话都不曾说过呀。
而布雷特施奈德却对他说,他已经犯了好几桩刑事罪,叛国罪就是其中之一。
随后两人又返回酒馆来了。
布雷特施奈德掏出双头鹰证章给巴里维茨先生看,对他望了一阵子之后说:“您就把自己的老婆叫到这里来吧,把生意交给她,那我们晚上就来拿您。”
“您一点都不用担心,”帅克安慰他说,“我也只不过为了一桩叛国罪才被抓到那边去的。”
“可是我又为哪桩呢?”巴里维茨先生抱怨道。
“为您曾经说苍蝇在皇帝画像上拉满了屎!我要您把对皇上的种种该死的想法统统从脑子里挖出来。”
于是帅克带着他那满脸一副愉悦、亲切的神情,跟着便衣警察离开了杯杯满酒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