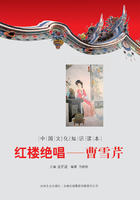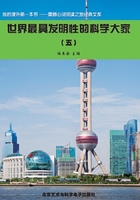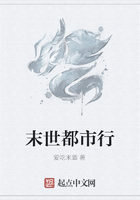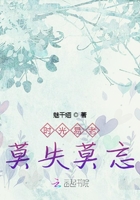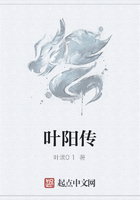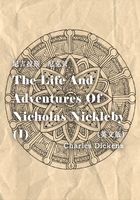第一节
山嶂叠翠,溪水潋滟,柳枝泛绿,桃花吐艳。这是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的第一个春天,自然景色清新,人的精神爽朗,预示着一切都很美好,新皇帝将会有个顺顺当当的开局。武帝少年登基,急于了解和熟悉各个方面的情况。他举行朝会,听取大臣们奏事。他召见官员,商谈兴国安邦大计。他走遍许多重要官署,检查那里的公务,考察官吏的政绩。他还爱微服私访,有时扮作派头十足的公子王孙,身着锦缎,手提鸟笼,穿行于大街小巷和坊里之间;有时又化装成卖货郎,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到长安近郊走村串寨,体察农民的生活。当然,武帝更多的时间是待在未央宫里。他要阅读很多很多的简策,处理很多很多的奏章。这时,他面临着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怎样看待父皇景帝的遗诏。那份遗诏就放在案头醒目的位置,他看了不知多少遍了,既有启示,也有困惑。遗诏告诫要“恤黎民,重农桑,轻赋役”,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民乃国之本,农乃民之本,舍此必然会动摇国家的根基。遗诏还告诫“外和匈奴”,“安分守成为要务”,这使武帝感到不解。匈奴屡屡侵犯大汉的国土,杀害人民,抢掠财物,为什么要跟它“和”呢?安分守成实是黄老之学,只求满足现状,不思进取发展,为什么要视它为“要务”呢?更要命的是前边一句话:“祖制不可轻改。”如果一切皆遵循祖制,那么,自己的手脚就会被捆得死死的,如何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呢?武帝不停地在思索和权衡着事关国家和未来的重大问题。武帝生性好动,尤爱标新立异。越年,他命改元,启用年号,称作“建元”。
建元元年,就是公元前140年。中国古代利用年号纪年,自此开始,其后垂为成例,这恐怕也算是武帝的一大发明吧?新年伊始,武帝颁布圣旨,命丞相、御史、列侯、二千石以上官员,以及诸侯王的相国,大力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备择优选用。他要通过此举,改变朝廷官员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补充新的血液。圣旨颁布,全国为之轰动,一大批学有所长的士子云集长安,跃跃欲试。武帝大喜,逐一接见,亲加策问,主题是为政之道,治国方略。各位士子见皇帝年少英武,礼贤下士,无不感动,遂将寒窗所学,生平抱负,尽情地抒发和展示出来。士子所言,就其思想类型划分,黄老之学的道家占了主流,此外还有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武帝听后,头脑发胀,莫衷一是,反倒不知孰是孰非,孰优孰劣了。这一天,他又策问一个名叫董仲舒的士子,但见他年约40岁,身穿长袍,头戴儒冠,宽额广颐,长眉秀眼,举止庄重,温文尔雅。经问,知他是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汉景帝时已为博士,专心治学,精通《春秋》,曾经三年不窥园中景色。武帝面向董仲舒,虚心地问:“关于治国宏旨,请问有何见教?”董仲舒胸有成竹,答:“最重要的在于确立国家的统治思想。”
武帝眼睛一亮,忙问:“这是怎么说?”董仲舒不慌不忙,回答说:“统治思想是一个纲领,是一面旗帜,有了它,国家才会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政令才会有感染力和号召力,从而使国人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否则,必是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武帝点头,说:“先生所言,正合朕意。那么,我朝应有怎样的统治思想呢?”武帝不知不觉地称董仲舒为“先生”了。董仲舒说:“儒学,只有儒学,方可使我大汉国富民强,长治久安。”武帝大感兴趣,说:“哦?请先生往细里说。”董仲舒目不斜视,从容镇定,说:“自孔子创建儒学,至今已有四百多年,但它的精髓和内蕴,一直无人认识。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学只是其中的一花一家,难以显示威力。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实行法家路线,铸就了辉煌,也铸就了罪恶。秦始皇统一中国,法家独霸,滥施刑罚,做出了焚书坑儒之类的愚蠢之事,这正是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高祖皇帝建汉以来,崇奉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以传说中的黄帝、春秋时的老子为祖师而得名,其思想核心是‘贵清静而民自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无为而治’。我朝初建,经济凋敝,国力衰微,民心思安思定,实行这种思想是必要的,实践中也取得了成效。但黄老之学,归根到底是一种消极颓废的学术流派,鼓吹清静无为,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现在看已不合时宜。陛下登基,万象更新,正应用新的统治思想来取代黄老之学,大展宏图,威服天下。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确立儒学为统治思想,着眼于天下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重视教化,兴学求贤。这样无需多年,大汉肯定会更加强盛,陛下也肯定会创立不朽之功业,名垂青史。”武帝听了这番话,字字合心,句句中意,直觉得浑身燥热,激情洋溢。
他兴奋地说:“先生说的太好啦!朕是听了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是不是这样,先生且留于京城,将言犹未尽的经纶写成策论,待后详议,如何?”董仲舒意识到自己遇见了一位具有雄心和胆识的英明之主,满心欢喜地说:“遵旨。”武帝转而对侍立在一边的丞相卫绾说:“将董先生安置于公车,好生照应。”“是!”卫绾恭敬地回答。公车,相当于驿馆,属卫尉管领,置有令史,凡朝廷征求的四方名士,皆由公车接送,故名。董仲舒在公车住了下来,卫绾动开了花花肠子。卫绾在汉景帝时曾任太子太傅,原是黄老之学的忠实信徒。他的为官之道是惟皇帝的意志为意志,竭力表现出敦厚老成的样子,因此官运亨通,先任御史大夫,再升任丞相。他还仰承太皇太后的鼻息,有事无事,每天都要去长乐宫请示问安,显示忠诚。他回答皇帝和太后的问话,总爱说三个字:“对”,“是”,“行”。因此,时人都称他为“三字丞相”。这时,他看到武帝重视儒学,觉得应当有所表现,讨好地奏言说:“各地所举贤良,有人治商韩(商鞅、韩非)之学,有人好苏张(苏秦、张仪)之言,无关盛治,反乱国政,请予一律罢归。”武帝说:“没错。跟儒学有关的士子留下,待诏公车,其他人就让回去吧!”卫绾表现自己,原想迎合武帝意旨,没料想武帝早就厌烦他的为人,心中骂道:“老庸物,惯于见风使舵,滑头!”几天后,武帝颁下旨来,卫绾的丞相职务被罢免了。
第二节
武帝利用皇帝权力,第一次罢免了一位大臣,而且是堂堂丞相卫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太皇太后不愿意了,派人传召武帝到长信宫,她要问个究竟。武帝应召而至,跪地叩头,说:“孙臣给太皇太后请安。”窦太后年逾60,常害眼病,视力一直不好。她端坐于自己习惯坐的软榻上,手拄那根从不离手的楠木拐杖,威严地说:“坐吧!”武帝坐于一张圆杌上。窦太后说:“听说你把卫绾罢免了,这是为什么呀?”武帝说:“一件事情牵连到他,不能不罢。”“哦?”“事情是这样的:父皇晚年多病,卫绾负责处理政事。廷尉大牢里关押着上百名无辜的囚犯,亟待审理。廷尉请示卫绾,卫绾奉行什么‘无为而治’,总是说‘对’、‘是’、‘行’,可就没个具体的意见。事情一拖再拖,一直拖了一年多,以致上百名囚犯,十成死了七成,最后只有二十多人无罪释放。最近,那些已死囚犯的亲属鸣冤叫屈,要朝廷给他们个说法。所以,孙臣只能罢免卫绾,否则无法面对国人。”窦太后听武帝批评“无为而治”,心中略显不快,只是没有说出来。她停了停,又说:“卫绾可是你父皇器重的老臣,还任过太子太傅,教授过你的学业呢!”武帝说:“老臣也好,新臣也好,关键要尽职尽责。卫绾为相数年,关于国计民生,未见献一计进一策,遇事只会哼哼哈哈,占着茅坑不拉屎,要他何用?”窦太后看到眼前的这个孙子皇帝颇有些锐气,想为卫绾辩解几句,也不能够了。她转变话题,说:“卫绾罢就罢了,那你打算任用谁为丞相呀?”武帝说:“孙臣尚未想好。”
“我倒有个人选,窦太后眯着眼睛说,“窦婴,就是我的侄儿,你把他叫舅舅。他曾参加平定七国之乱,立了功的,封魏其侯。经过这些年的历练,各方面都有长进,可以担当大任了。”武帝是知道这位舅舅的,还知道父皇景帝对他的评价:“沾沾自喜,轻薄无检,难以为相持重。”现在,窦太后既然提出任用窦婴为丞相,他也不好反驳,答应说:“孙臣一定考虑太皇太后的意见。”武帝从长信宫出来,顺便到了长秋殿,看望母亲王太后。王太后听说窦太后提名窦婴为丞相,反应很快,说:“太皇太后这不是要重用外戚,扩张窦氏的势力吗?”武帝说:“谁说不是?”王太后说:“这不行!窦氏外戚一旦得势,还不把人吃了?儿呀!你可得慎重点。不过,倒也有办法,她要重用窦氏外戚,你为何不重用王氏外戚?娘有两个弟弟,你把他们叫舅舅,也可以重用呀!”王太后所说的两个弟弟是指田蚡和田胜。王太后的嫡胞哥哥王信已死,同母异父弟弟田蚡和田胜却很健壮,上年分别被封为武安侯和周阳侯,就连王太后的生母臧儿也被尊封为平原君。田胜封侯,只知吃喝玩乐,没有什么出息。田蚡却有些能耐,伶牙俐齿,善于雄辩,官任中大夫,算是一名新贵。武帝暗暗发笑。在长信宫,出了个窦婴舅舅;在长秋殿,又出了田蚡、田胜两个舅舅。自己哪来这么多的舅舅呢?一边是祖母太皇太后,一边是母亲皇太后,都想让外戚显贵,自己又能怎样呢?武帝自有武帝的手段,回到未央宫后,马上颁旨宣布,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一人管政,一人管军,窦氏和王氏外戚在朝廷上平分秋色。
这样一来,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不吭声了。窦婴和田蚡都是时髦派人物。他俩看到武帝尊重董仲舒,尊重儒学,心领神会,亦步亦趋,共同检举儒生赵绾和王臧,使前者当了御史大夫,后者当了郎中令。汉朝,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合称“三公”,郎中令则是宫廷中的侍卫长。他们都成了儒学的支持者,那闹腾劲儿可就大起来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鼓动武帝建明堂,开辟雍。明堂是皇帝宣明政教的地方,辟雍是学校。武帝说:“好啊!儒学注重教化,此事可办。你等可仿照古制,从速施行。”可是,窦婴、田蚡等人不知古制,如何仿照?赵绾、王臧推荐一人,就是他们的老师,鲁国人申培。申培,人称申公,信奉儒学,教学授徒,门下弟子,超过千人。武帝同意。于是,赵、王驾着朱轮马车,携带金玉绢帛,亲自前去迎聘申培。申培应聘,全不推辞,来到长安,拜见武帝。武帝见他年近八十,精神矍铄,道貌高古,格外尊敬,说:“申公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不胜荣幸。而今,朕欲兴国兴政,但不知有何见教?”申培注目武帝,见他年轻而又谦恭,暗暗赞叹,一字一顿地说:“为治不在多言,贵在身体力行。”说完便即住口。武帝还想听下去,却无下文,未免失望。转而一想,申公的两句话,恰也是金玉良言,“身体力行”四字,不正是自己所要遵循和坚持的作风吗?武帝任命申培为大中大夫,任务是和赵绾、王臧一起,按照古制和儒家规定,规划建明堂、开辟雍,以及制订各项礼仪等事务。窦婴、田蚡做的第二件事,是建议取消各诸侯王国之间设置的关卡,以显示国家的统一,便于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接着,他们开始纠察皇亲国戚的不法行为,以维护国家纲纪。窦太后的弟弟窦广国,封章武侯;窦太后另一个侄儿窦彭祖,封南皮侯。这二人依仗是皇亲国戚,横行霸道,作恶多端,民愤很大。即使窦婴,对于本族人仗势欺人、无法无天的行径,也觉气愤。窦婴、田蚡决意纠察皇亲国戚,原本是件好事,不想却触动了窦氏外戚的利益,闯下了大祸。
第三节
建明堂,开辟雍,取消关卡,纠察权贵,诸事走上正轨。年轻的武帝又想到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北方的匈奴。边境上时时传来奏报,都是匈奴侵边扰民的消息。这使他不安,更使他气愤,堂堂大汉,怎能容忍外敌如此猖狂?他听说过,汉朝的西方,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以外,曾经有个强大的月氏国,多年前被匈奴攻灭,匈奴单于砍下了月氏国王的头颅当作酒器,双方结下了世仇。月氏国被迫迁徙,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么,这个月氏国到底去了哪里呢?大汉能不能和月氏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匈奴呢?再说,玉门关以外,泛称西域,那么,这个西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是山是海?有人无人?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这个情况是必须搞清楚的。自己作为大汉的皇帝,不清楚大汉境外的情况,那是井底之蛙,不足称道。武帝雄心勃勃,在朝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派遣使臣,出使西域。任务有二:一是联络月氏国,商讨共击匈奴的可能性;二是考察西域,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朝臣们对于武帝的主张,赞成的多,反对的少。可是当决定谁为使臣的时候,却无人吭声。因为西域是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出使等于送死,谁也不愿冒那个险。武帝并不勉强朝臣,说:“你们不愿冒险,情有可原。那好,朕就颁旨出榜,招募勇士出使,如何?”“皇上圣明!”朝臣们齐声高呼,没有异议。次日,长安城门悬出皇榜,黄帛黑字,写得分明:“大汉皇帝昭示臣民:招募勇谋智识之士一人,出使西域。凡有志者,即日到大行署报名,经审查合格,即为大汉使臣,奉命出使。钦此。”
一时间,全城为之轰动,人们争相议论,说:“皇帝出皇榜,招募出使人,亘古未有,真是太稀奇太罕见啦!”武帝出了皇榜,心中喜悦,相信一定会有揭榜的勇士,前去完成艰难的使命。这天,他又到长乐宫拜见祖母太皇太后和母亲皇太后,顺便到了永寿殿,拜访王夫人。王夫人即王姁,武帝称她为皇姨。王夫人见武帝前来拜访,欢喜连天,脸上笑成一朵花。礼数略过,王夫人命侍从回避,坐下和武帝说话。王夫人问:“见过母后了?”武帝答:“刚刚见过。”“你母后没说什么?情绪怎样?”“没说什么,她老人家情绪可以呀!”王夫人看着武帝,说:“你母后有桩心事,你知道吗?想跟你说,却又无法开口。昨天我去见她,她还流泪来着。”武帝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说:“母后有心事?为何不明说呢?”王夫人觉得这件事只有自己好说,便问:“皇帝知道自己的大姐吗?”武帝一怔,说:“大姐?不就是平阳公主刘玫吗?我当然知道。”王夫人轻轻摇头,说:“不!刘玫前面还有一个。”武帝诧异,说:“怎么?还有一个?”王夫人点头,说:“对,还有一个,叫金俗。”于是,她从姐姐第一次婚姻说起,将其入宫前后的详细情况说了一遍,最后说:“金俗和你同母异父,实是你的大姐。这么多年,不知是死是活。你母后经常惦记着她,却又不便跟人说起,心里苦啊!”武帝陷入沉思,没想到生母入宫前还有这样一段情事,够滑稽的。武帝是个孝顺儿子,当下说:“既然有这个大姐,自当迎她入宫,以解母后思念之苦。”王夫人说:“这事,你得斟酌。皇宫里除你母后和我之外,大概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个金俗。迎她入宫,别人会怎么想怎么说?会不会影响你父皇和母后的声誉?”“皇姨放心”,武帝毫不在乎地说,“人生在世,亲情为重,管他别人怎么想怎么说。再说了,我是皇帝,说话办事,天经地义,谁敢说半个‘不’字?”武帝返回未央宫,当天就派了好友韩嫣去咸阳一带密访金俗。这个韩嫣是弓当侯韩颓当的孙子,年龄和武帝相仿,聪明灵巧,眉目清扬,长得像美女一般。武帝为胶东王时,就和韩嫣亲密,及至即位后,韩嫣官任上大夫,仍侍在侧,有时同吃同睡,犹如自家兄弟。密访金俗之事,交给韩嫣去办,那是再合适不过了。数日后,韩嫣回来报告,说咸阳长陵有一女子,姓金名俗,确金王孙之女。
武帝大喜,当即乘坐御辇,带着韩嫣,前引后随,从骑如云,前往长陵。长陵乃汉高祖刘邦的陵寝,位于咸阳北原,设有县邑,徙民聚居,街巷店肆,人烟稠密。百姓看到御辇前来,以为是扫陵祭祖,纷纷回避,不想御辇径入小市,拐弯转角,停于一金姓人家门前。武帝侍卫,呼令开门,连叫不应,咚咚敲门,亦无反应。难道家中没人?非也。原来金俗是个女流,独自在家,听得大呼小叫,当是役吏抓人,吓得浑身发抖,筛糠似的,蜷缩在房角,气都喘不过来。武帝等候许久,下令破门。侍卫抬脚将门踢开,一拥而入。金俗吓得连滚带爬,钻到床下藏身。侍卫四处搜寻,发现床下缩作一团的女子。韩嫣料定她是金俗,唤她出来见驾。金俗魂飞魄散,那敢出来?侍卫们七手八脚,使劲拖出。韩嫣悄声对她说:“去!快去见皇上,包你有荣华富贵。”金俗惊魂未定,半信半疑,拭去脸上尘垢,且行且却,好不容易出得门来,什么也没有看见,战战兢兢地跪地,不知该怎样称呼,干脆一声不响,屏住呼吸等候发落。武帝见金俗粗布衣裙,蓬头垢面,跪在地上,仍在发抖,赶紧下了御辇,向前几步,微笑着说:“大姐不必害怕,快快起来说话。”金俗微抬双眼,只见面前一位华贵公子,竟叫自己为“大姐”,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听他声音柔和,语气亲切,料无恶意,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因而徐徐站起。武帝依然微笑,拉起金俗的双手,说:“大姐!弟弟接你回宫,看望母后去!”弟弟?回宫?母后?金俗越发惶惑,如坠云里雾中。武帝盈盈而笑。金俗猛地想起什么,不大相信地说:“你说的母后得是我娘?怎么?她还活着?”武帝含笑点头。“哇——!”金俗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喊:“娘!娘啊——!”金俗是从别人口中知道有个娘的。当初,王!和金王孙离婚的时候,金俗还在襁褓之中,长大后,金王孙说她的娘早就死了,而邻居们却说,她的娘和金王孙离婚,进了皇宫。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现在,华贵公子说她的娘还活着,而且是什么“后”,她怎能不惊喜不伤心呢?武帝请大姐上车。
金俗返身回家,匆匆梳洗,换了一身半新半旧的衣裙,再出来登上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车上的韩嫣告诉她,御辇上的华贵公子乃当今皇帝,其实是她的弟弟。金俗惊得目瞪口呆,一路思想,莫非做梦不成?不到一个时辰,便到京城,仰望是高宫华殿,平看是宽街通衢,还有一班官吏,分列道旁,毕恭毕敬,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片时进了一座巍峨华美的皇宫,直至一座大殿前。韩嫣请金俗下车。武帝迎了过来,笑着招呼,并引着她走进殿内。殿内金玉辉映,香气氤氲,简直就是天堂。武帝让金俗止步稍候,先行进入内室。不一时,出来七八个花枝招展的宫女,簇拥着金俗,亦进内室。金俗凝神看去,但见正面端坐着一位雍容华贵的老夫人,左侧站立的正是引她入殿的皇帝。武帝告诉老妇人说:“母后!儿臣前往长陵,把大姐金俗给接回来了!”随后招呼金俗说:“大姐!快给母后叩头!”老妇人和金俗的心都为之一震。金俗快步走至老夫人座前,跪地叩头,说:“娘!你想得女儿好苦啊!”王太后和女儿分离20多年,根本记不得女儿的模样,俯身,颤颤巍巍,说:“你就是俗女?”金俗应声说是。王太后抚摩着金俗粗糙的脸庞,左看右看。金俗想到邻居们所说的生母,悲从中来,泣不成声。王太后一把将金俗搂在怀里,热泪纵横,呼唤说:“俗女!苦命的孩子!”母女意外重逢,只是抱头痛哭。武帝早命宫监吩咐御厨,速备酒菜,设宴庆贺。同时派人去请皇姨王夫人和平阳公主刘玫、南宫公主刘玢、隆虑公主刘玟,前来团聚。三位公主皆已出嫁,俱住京城。王太后见金俗衣饰粗劣,引她至另室,予以更换。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金俗经过宫女们的梳妆,涂脂粉,抹口红,簇新衣裙,琳琅珠翠,居然也像一位公主,与前判若两人。只是金俗贫穷惯了,乍一那样打扮,显得把拙别扭,很不自然。这时,皇姨和三位公主渐次到来。王太后引着金俗,一一相见,彼此开心,一片欢声笑语。酒宴摆出,王太后首座,王夫人次座,武帝居左,金俗居右,举杯共饮,全家合欢。王太后乐得心花怒放,她一生中的惟一缺憾,因金俗失而复得,被熨得平平展展。当夜,金俗陪王太后住在长秋殿,母女俩个说了一宿悄悄话。金俗告诉母亲说,父亲金王孙早已病死,自己无兄无弟无姐妹,招赘了丈夫,生了一儿一女。目前家境贫寒,勉强糊口。王太后唏嘘嗟叹,又流了不少眼泪,说:“孩子!真苦了你了。从此,你会苦尽甘来,我和皇帝都会呵护你的。”第二天,武帝颁旨宣布,封大姐金俗为修成君,赐钱1000万缗,田100顷,府第一座,奴婢300人,另加汤沐邑一处。金俗千恩万谢,几天后即回长陵,将丈夫和儿女接到长安居住,一家人蒙受浩荡皇恩,大亨其福,再不为吃饭穿衣问题发愁了。
第四节
转眼一年过去。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武帝18岁,标志着少年时代已经结束,大步跨进了青年时代的门槛。青年是人一生中最具想像力和最富挑战性的年龄段。武帝雄心勃勃,意气风发,决心以充沛的精力治理国家,振兴大汉,做一个超越前人、名扬后世的真龙天子。皇榜招募勇士出使西域的大事已经有了眉目。负责外交事务的大行令王恢报告说,一个名叫张骞的人揭了皇榜,经过审查,各方面的条件不错,符合使臣的要求。武帝大喜,亲自接见张骞,他要把出使的目的和任务交代清楚。张骞,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人,二十四五岁,时为皇家禁军的郎官。身材魁伟,体格健壮,勇于吃苦,敢于冒险,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品质。当他揭那皇榜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西域是怎么回事,只是为了去尝试,去冒险,用实际行动报效国家和朝廷。武帝在未央宫宣明殿接见张骞,见他高高大大,相貌堂堂,眉宇间有着一股逼人的英气和豪气,兀自欢喜。武帝说:“张骞!你出使西域,知道自己的使命吗?”“知道”,张骞响亮地回答说,“一是联络月氏国,二是探明西域的情况。”武帝点头,说:“不错。我们联络月氏国,是为了共同对付匈奴;探明西域情况,是为了扩大视野,强我大汉。此行山高路远,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有思想准备吗?”“有!臣既然敢揭皇榜,那就做好了葬身大漠的思想准备,无怨无悔。”“不!朕不要你葬身大漠,朕要你活着回来!”“是!”“此去西域,道路不熟,语言不通,你是怎么打算的?”“回皇上的话:臣已物色了一个匈奴人,名叫堂邑父,又叫甘父,忠实可靠,他可以充当向导和翻译。”“很好!”武帝见张骞把事情做在了前头,更加欢喜,停了停,又说:“张骞!你知道出使西域,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张骞回答说:“维护大汉尊严,不辱君命。”武帝非常满意这个回答,加重语气说:“对!维护大汉尊严,不辱君命。你是大汉的使臣,代表国家,代表朝廷和朕,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都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始终保持一种气节,一种精神,克服困难,不负朕望。”张骞抱拳,宣誓一样地说:“臣谨记圣谕!”“好!”武帝兴致高昂,说:“朕提升你为中郎将,赐予节仗,拨给百人,以作随从。你可抓紧做好准备,待命出使。出使之日,朕要亲自为你壮行!”“谢皇上!遵旨!”就在这时,韩嫣匆匆忙忙进殿,在武帝耳边说了些什么。武帝心里一惊,脸色略变,接着迅速恢复常态,对张骞说:“好啦!你回去准备吧!”张骞退去。武帝连忙问韩嫣说:“怎么回事?”韩嫣说:“赵绾和王臧被逮捕下狱了。”
武帝说:“这是怎么说的?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是郎中令,没有朕的旨意,谁敢逮捕朝廷大臣?”“听说是太皇太后的命令。还有,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恐怕也要……”武帝脸色由白转红,由红转青,说:“她管的也太宽了!”韩嫣说:“此事风头不小,陛下需要谨慎对待才是。”二人正说着话,长信宫宫监进殿,向着武帝叩头,说:“奴才奉太皇太后懿旨,宣召皇上去长信宫议事。”武帝警惕地问:“太皇太后要议何事?”宫监答:“奴才不知。”武帝一挥手,说:“你去吧!朕随后就到。”宫监离去。武帝摇着头说:“秋风乍起,山雨欲来呀!”韩嫣陪着小心说:“臣的意见还是四个字:谨慎对待。”武帝乘辇,前往长信宫。路上,他想起太皇太后以前的一件事。汉景帝在位期间,太皇太后还是皇太后,信奉黄老之学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打心眼里厌恶儒学。一次,她召儒生辕固讲解《老子》。辕固崇尚儒学,贬斥黄老,猝然回答说:“《老子》有什么可讲的?那里面不过是家人常言,庸人见识。”窦太后听辕固这样贬绌《老子》,勃然大怒,命将辕固置于野猪圈中,狠狠地说:“你一个儒生,不学无术,有何能耐?既然你口出妄言,我就让你和野猪格斗。胜了,是你的造化;败了,或被野猪咬死,活该!”可怜辕固,一句话招来了祸殃,面对凶悍的野猪,不知如何应对。幸亏景帝心地仁慈,命人给了辕固一柄利刃。辕固鼓起勇气,孤注一掷,拼死格斗,好不容易将野猪刺死,这才保住了性命。武帝想着想着,御辇进了长乐宫,到了长信宫前。武帝下辇,步入长信殿,只见太皇太后手拄拐杖,正襟危坐,古板着脸,威严阴沉。母亲王太后也在,坐在一边,显然是受了训斥,眼圈儿红红的,强忍泪水。武帝跪地,向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请安。太皇太后说:“起来吧!”跟往常不同,她并没有让武帝坐下。武帝只好站着,等候问话。窦太后用手指抹了抹眼睛,说:“我已下令,将赵绾和王臧逮捕下狱了,你知道吗?”武帝说:“孙臣刚刚听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
“这二人存心不良,挑拨皇家关系”,窦太后气呼呼地说,“他俩不是在你跟前说过吗?‘陛下年少有为,各项举措深得人心。你如果想成就超越先皇的大事业,就要敢于独断,不要受制于人。太皇太后已经老迈,朝廷大事,不必向她请示,更不必请她决断。’是不是这样的?”武帝暗暗吃惊,心想这些话是赵绾和王臧私下跟自己说的,她太皇太后是怎会知道的呢?“哼!他俩是在挑拨我你祖孙的关系,引导主子不孝,这样的小人不该逮捕下狱吗?”窦太后理直气壮,继续说:“你父皇的遗诏里专门有句话,叫做‘遇事多请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决断’。赵绾、王臧居心叵测,鼓动你不向我请示,不让我决断。这样的人,惟恐天下不乱,岂可重用?岂可留在你的身边?”武帝默然。窦太后话锋一转,更严厉地说:“你,也该检讨一下你的作为了。你父皇遗诏说的明确:‘祖制不可轻改’,‘以安分守成为要务’。可你是怎么做的?不知天高地厚,忘记祖宗教诲,听信那个董仲舒的蛊惑,竟想用儒学取代黄老之学,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这能行吗?我朝自高祖皇帝以来,一贯实行的是黄老之学,这有什么不好?我且问你,你知道‘萧规曹随’的典故吗?”武帝回答说:“孙臣听说过。”窦太后没好气地说:“听说过不行,还要领会它的实质。那是高祖皇帝驾崩以后,惠皇帝刘盈继位。丞相萧何死了,曹参出任丞相。曹参一天到晚只顾饮酒,不问政事。惠皇帝很不满意,批评曹参。曹参回答说:‘请问陛下,你同先帝相比,谁更圣明?我同萧何相比,谁更贤明?’惠皇帝说:‘我比不上先帝,你也比不上萧何。’曹参说:‘对呀!既然如此,我们就遵从先帝确定的治国方略,贯彻萧何制定的法令制度,不就很好吗?何必另出什么新花样?’——这就叫‘萧规曹随’,核心是遵循祖制,安分守成,不出新花样。惠皇帝以后,你曾祖母高后、祖父文皇帝、父亲景皇帝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才有衣食滋殖、天下晏然的大好局面。你倒好,登基才几天?就要实行什么儒学,建什么明堂,开什么辟雍,还把那个糟老头子申培从千里之外请到长安来,修订什么礼仪制度。你这样做,说远点,是违背了祖宗的定制;说近点,是违背了你父皇的遗诏。”“我……”武帝意欲分辩。窦太后一摆手,说:“你不用分辩,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想说,现在世事变了,国力强了,百姓富了,总该有新作为新气象,对不对?不过,我要告诉你,新作为新气象,不会靠改变祖制得来,你若胡乱折腾,只会断送祖宗开创的基业。”
“我……”武帝张了张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窦太后又抹了抹眼睛,说:“还有,我听说你专门出了皇榜,招募勇士,出使西域,企图攻打匈奴,荒唐!”她重重地将拐杖顿了顿,戳得地板咚咚作响,说:“匈奴就是那么好打的?想当年,高祖皇帝曾亲统30万大军,攻打匈奴。结果怎么着?先锋部队反被匈奴单于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七天七夜,险些全军覆没。那是冬天,天寒地冻,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饥寒交迫,困顿至极。后来,亏得陈平想出一计,用重金厚礼贿赂了匈奴单于的阏氏,阏氏说服单于撤兵,高祖皇帝才得以突围。”武帝说:“高祖皇帝时,我朝的国力还不如人家嘛!再则,高祖皇帝用兵的时间不对,战术上也欠妥,犯了孤军冒进的错误……”“大胆!你诋毁高祖皇帝不是?”武帝吓得一吐舌头,说:“孙臣不敢。”窦太后接着说:“从那以后,我朝对于匈奴,一直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实行和亲政策。和亲政策好啊!用一个女人,换取边境安宁,免得两国兵戎相见。假若匈奴容易征服,文皇帝、景皇帝早就出兵了,何必等到今天?你父皇遗诏里特别有‘外和匈奴’一句话,那是我朝的对外方针,是国策,懂吗?你呀,年纪轻轻,难道比你祖父、父亲皇帝还高明不成?”武帝心中不服,意欲争辩。王太后朝他挤眼示意,意思是说忍,惟有忍,方可平息太皇太后的怒气。窦太后言犹未尽,又说:“我把赵绾、王臧逮捕下狱了,一定要从严惩处。还有窦婴和田蚡,也该罢职。他俩上台,不务正业,竟然纠察起权贵来了,岂有此理!章武侯窦广国是我的弟弟,南皮侯窦彭祖是我的侄儿,平日里是失于检点,仗势欺人,横了些,但毕竟是皇亲国戚,纠察权贵,先拿他俩开刀,不是存心抽打我这老脸吗?皇权皇权,就是要为皇家谋取福利。我若连自己的弟弟和侄儿都保护不了,那还算什么太皇太后?”武帝说:“窦婴任丞相,是太皇太后推荐的,怎能说罢就罢了呢?再说,他也是皇亲国戚呀!田蚡也是……”窦太后打断武帝的话,说:“彼一时此一时也。
我将赵、王下狱,将窦、田罢职,就是要让人知道:太皇太后还活着,跟太皇太后作对的人,不配拥有权力!”她觉得有必要顺便对武帝发出警告,特地加重语气说:“包括你,别以为你是皇帝,我就奈何你不得。你若一意孤行,惹恼了我,我照样会……”她本想说“废了你”,可这三个字到了嘴边,没说出来,改口说:“你给我记住,遵从你父皇的遗诏,好自为之。小事,你可以自行处理;大事,你必须向我请示,由我帮你决断。”这简直是恫吓,是威胁。武帝心火突突,刚想发作,一眼看到王太后示意的眼神,立刻控制住了激动的情绪,嘻嘻而笑,说:“行!我的祖母奶奶、太皇太后大人!从今往后,大事小事都向你请示,都请你决断,总可以了吧?对了,现在就有一事,你得决断:罢了窦婴和田蚡,那么由谁接替他俩的职务呢?”窦太后见武帝服软了,心中得意,想了想,说:“柏至侯许昌可任丞相,武强侯严青翟可任御史大夫。至于太尉和郎中令二职,暂且空着,以后再说。”许昌和严青翟都是黄老之学信徒。武帝感到恼火,嘴上却说:“行!孙臣照办便是。”窦太后痛痛快快地训斥了武帝,人事安排又达到了目的,只觉得浑身爽朗,说:“好啦!今天就到这儿,你们去吧,我也累了。”王太后和武帝巴不得已,告辞,如释重负地出了长信殿。武帝没回未央宫,随着母亲进了长秋殿。进了殿,武帝摘下帽子,往桌上一摔,大发其火,说:“倚老卖老,欺人压人,这算什么?好端端的四位大臣,两人下狱,两人罢职,这还是朝廷吗?尊重儒学不对,攻打匈奴不对,出使西域不对,纠察权贵不对,反正都是不对,就是她的黄老之学是对的,世上哪有这个理?而且还恫吓我和威胁我,我倒要看看,她究竟能把我怎样?”王太后赶紧捂住武帝的嘴,说:“我的小祖宗!谨慎为好,不敢这样口不择言。”武帝坐于杌上,内心不平,呼呼喘气。王太后说:“儿呀!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你要明白,太皇太后在位40年,朝廷大臣多是旧人,根深本固,枝叶缠绕,她的势力大着哪!而你呢?即位不久,脚跟未稳,羽翼未丰,鸡蛋不能硬跟石头碰啊!俗话说:‘忍一时,乾坤大;退一步,天地宽。’眼下,你只能忍,只能退,学会收敛锋芒,不必顶牛任性,懂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日方长啊!”武帝忽然想起什么,问母亲说:“她得是为难母后了?”“唉!也不算为难”,王太后叹口气说,“还不是金俗的事?太皇太后嫌我隐瞒入宫前的经历,欺骗了先帝,还说接回金俗,是丢了皇家的体面,你给金俗的赏赐,忒多忒重了些。”“老不死的!怎么什么事都管?”武帝又冒出一句不敬的气话。“不许谩骂太皇太后!”王太后制止武帝。“这……这……”武帝觉得憋气,直想大吼一声,把压抑在胸中的郁闷统统发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