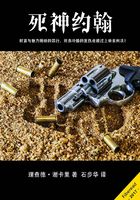沉香的焚烧是一片大火,蓝色的烟雾是焚后的残香。这之前有一场未曾被人目见的火雨,它曾经统治着这片幽阴的原始森林。
细辨那火雨之后沉寂的穿行,神明的穿行,分明有一个声音:“我活着是什么,死了还是什么。”
这声音无处不在,像是不死如缕的魂灵,顽强地缠绕在树林、在空气、在河谷的每一沙砾,随着向山外奔涌而去的河水,不知流向何处。这声音时强时弱,似有若无,如黄钟大吕,又如游丝萦回,像厉鬼叫啸,又似病女娇喘。一定是男鬼和女鬼,在时光中行走。有一百年的时间了吧?在我出生之前的几十年间,他们就已经存在于这大岭大山之中。这种景象传说了好几代人,从爷爷到孙子,孙子又成了爷爷。传说在民间不胫而走,有好多版本,好多梦境,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地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谁都希望故事应该是完整的,但谁也都知道所有的传说都是不可能完整的。这似梦非梦、似真似幻的故事,就永远活在传说中,尤其是山里的森林里的传说中,就很不可靠。
雅加的时间,总是由夕阳时分开始的。这个有些古怪的说法,顽强地沉积在我的习惯里。自从来到雅加,我都是在夕阳时分,才开始一天的工作。这种看起来怪诞的行事习惯,让我的学生备觉疑惑。
白天族人们自有自己的劳作,很难有充分的时间接受我们的访问。我的学生们过惯了城市的节奏,朝九晚五的生活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千古习俗看似相同,其实大谬不然。夕阳之后的时光,才是族人们真正享受生命欢娱的时光。
据说史图博在进入族人村落时,也往往选择了夕阳满天的时间。这也是我遵循这个时辰的一个理由。
我没有任何理由不遵循这样的原则。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所有同龄的中国人中,我是最早听说过史图博这个人和他的事情的,早在我15岁时的1966年,我就知道史图博这个德国人,并喜欢上他。这种说法没有一点吹牛的成分,尽管听起来太有吹牛的可能。所以我从来都不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这件事和瘌痢头得到沉香的幸运一样,太有民间故事的意味。而我从来都把这种所谓的幸运当作一种无法回避的命定,正如我在童年时遇到了中尉和他的灯塔,然后便有了我后来的雅加的远行。我之所以在本不该遇到史图博的年龄,却早早地知道史图博这个与我的生活完全无关,而后来却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的人,并非是一种偶然。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实,都陆陆续续地证明了偶然是并不存在的,所有的偶然其实都指向一种必然,只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能够跟随这种偶然走到最后而已。
我数度进入雅加,又数度离开的全部经历,都与史图博这个名字相关,许多莫名其妙的人和事,都与这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确信这就是命运的指向。
中尉给我讲述有关史图博的事,他其实并非在说史图博其人。他意在跟我介绍一个与史图博事件有关的人。那时我对这个人并无深厚的兴趣,相反,却对史图博这个名字铭刻于心。
史图博是一个德国人,我对德国人的好奇皆出于我家中的一口小铁锅,那只小铁锅用铝合金制成。这口小锅,听母亲说,它随我家族的迁徙历经百年以上。从曾祖父那一代人起,它就顽强地留存在四处流浪的家什中,许多珍贵的家传都在流离之中遗失了,反而是这口不起眼的小铁锅,一直跟随着家族的兴衰,从北向南,又从南向北,在四处流转中磕磕碰碰地幸存下来。
我见到这铁锅时,它已经老旧不堪,可是从没破漏也不需修补。锅盖早已在流转中不知丢失于何时何地。这口铁锅上镌刻着几行德文,其中标明制于1840年,汉堡的一家铁工厂。它大约也就是那时进入我们的家族。这口铁锅在“文革”时被当作“崇洋媚外”的物证,被抄家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许多年过去,有时我还会想念它,想念那些在这口铁锅里舀饭吃的日子。
这口历经160年而不需修补的铁锅,令我对德国工匠有一种由衷的敬意。由物及人,史图博和德国铁锅,就这么简单。
2010年的冬天,据说是百年一遇的寒冬,报纸上这么说,我自己是并不相信的。元旦刚过,天气奇冷倒是真的。雅加的天气很好,由于海拔很高的缘故,尽管地处热带,但雅加山区一年四季,夜间和清晨都比较寒凉。在一天之中,雅加最好的时光是夕阳将尽未尽的时候,那是集结了雅加所有温暖的时刻,也是雅加的所有生物最为活泼和满足的时刻。我想人类也理应如此吧。
在雅加中部,一个叫沟谷的县城,县委书记是我80年代的学生,我到雅加的时候,他恰好到中央党校去学习,据说新近要提拔到省民宗委去。我对他别无他求,只希望他安排属下,给我们派个向导。他指令宣传部长和我们接洽。宣传部长是个女的,中央民族大学90年代的毕业生。在沟谷已经任职多年,从镇文化站到县文化局,新近才升任宣传部长。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下午下班之后,到县委招待所见面。
宣传部长如期而至,矮胖、健壮,见面握手,落落大方,自我介绍姓名王艳丽,是本地族人。无须客套。她说县委书记的老师来了,理当热情接待,有什么问题尽管吩咐。我也不客气,简单把来意说明,希望派位族人,熟门熟路做个向导就可以,她当即说,那就派党史办主任吧!
党史办主任?这和我们此次的专业调查有些隔。我向她提出几个人选,这些人都是我们从有关资料上获得的。她有些为难,这些人她闻所未闻,不知要到哪儿去寻觅。我问起其中有叫王佬龙的,问她认不认识。她一愣,忽然有些警觉。“这人……”她欲言又止。
“认识?”我试探着问。看出她的犹疑。
“嘿!这人不太好办。关系很复杂。你们认识他?”宣传部长的口气里透露着阶级斗争的信息。起码我是这么感觉的,至少是我曾经熟悉的一种官方口吻。这反而使我有了某种进攻的意味。
“不认识,但是多少知道。他父辈是个传奇人物。”我想先试探她的意思。
“我们不想去碰这些人,很麻烦的。教授,你有所不知,民族问题很敏感的,我们都很小心。弄不好,很容易出问题。”她年龄不老,可思想挺老到的。这是我对这位70后的宣传部长的基本看法。也难怪,在沟谷这种地方待久了,很难不作如是想。
这几年在基层游走多了,碰到这样的情况不少。我很想将她一军,但想想在人家地头上,她的上司又是我的学生,还是和谐一些罢了。
我还是忍不住:“很麻烦是什么意思?”我明知她所指为何,但还是想追问到底。
“有人在为他出头,向政府要待遇,民政部门也很为难,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解放前好几十年的事,谁说得清楚。你说对吧!”她说得很在理。我所说的这个王佬龙,确实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宣传部长所说的有人,指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我一无所知。她的话反而撩起了我的好奇心。其实,我对这位叫王佬龙的了解,仅止于知道他是一位族人名人的后代,他的先人曾经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峒主,他和雅加的革命史有极其复杂的关系,至今评价不一。要讲雅加的革命史或民族史,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此人,可现实却是,谁都在想方设法回避他。
这些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之选择了王佬龙,其原因仅仅是,他的先人,曾经于二三十年代面见过史图博、黄强将军、萨维纳和左景烈。这些人和我所主持的研究项目《史图博研究》有关联。黄强将军曾是广东南区善后公署参谋长,1936年曾当过雅加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他写过《五指山问黎记》。萨维纳是法国人类学家,他曾于1925年随黄强将军入雅加,于次年出版了《海南岛志》。而左景烈则是国立中山大学研究农林植物的教授,他也于20年代来过雅加,写作有《海南岛采集记》。这些人都与王佬龙的父亲有过接触。而王佬龙的父辈出身行伍,又是峒主,他于1926年出版了著作《琼崖各属黎区调查》。
选择王佬龙作为向导,是我非常成熟的想法。宣传部长的疑虑与推诿,更加重了我寻找王佬龙的决心。非王佬龙不可。
看来要找到王佬龙,只能指望远在千里之外的县委书记了。我当即给县委书记打电话,无人接听。
没过多久,县委书记从北京来电,说明天傍晚,党史办的符主任会把王佬龙带到,我们只管签收即可。我顺便问起王佬龙的事,他满口答应,说等他学习归来,他会亲自处理善后。但是,我从书记的口气里也听出另外的意味。王佬龙的事绝对不简单,他的事自然和他父辈的评价密切相关。其实,我也并不知道宣传部长所指王佬龙的麻烦之事,究竟为何事?
所谓麻烦之事,肯定地说,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处于好坏之间的事,也便是左右为难,奈何不得的事。这些事真正是棘手。我想,王佬龙一旦陷入如此境地,此生此世要想彻底解放也难。
王佬龙明天傍晚才到,我便想抽空到坦桑的墓上去看看。有好些年了,不知坦桑的墓是否已经让荒草淹没,或让人开山辟地魂归异处。
宣传部长很是热情,听说我要去雅加六连,说可以陪同,我婉言谢绝。我已领教这位年轻部长的思想意识,她是位阶级斗争仍在弦上的人物,起码是观念仍然停留在她出生的那个年代的人物,说是陪我,极可能是我奉陪不起。
碉楼自然早已不在,那棵硕大的金丝楠已经让人连根挖起,不知于何年何月被卖到何处。原始森林也早已成了荒山秃岭,40年间,几千年形成的原始森林,又回到史前的蛮荒。这是我在离开雅加之后,就再也寻找不到雅加的伤痛之一。
记得那时雅加的流水是清冽如同冰雪,那是一个由纯美的大自然共构而成的纯美的世界。大地如同一块饱吸了清泉甘霖的水绵,随便在哪儿都可以踩出甘甜的水流来,有丰盈流水的土地,自然生育着最为丰满的物事。而现在,在雅加,所到之处,呈现着干裂与干涩。
我记得坦桑的墓地就在沼地边缘的山坡上,坦桑去世时我已离开雅加多年。他去世时的许多细节无法寻考,也并非常人可能知晓,这也是我最为伤痛之处。一个和你亲近的人的故去,他的故去居然是并不明朗且有许多的迷茫之处,而你又永远无法解开这些谜团。
在早晨或是夜晚,岭顶总是有人在唱歌,唱着黎歌或是苗歌,很幽怨的曲调,如泣如诉。我问信宜老鬼听到没有?信宜老鬼不置可否,他对此没有兴趣也并不关心。问得多了,信宜老鬼说一定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他知道有一种病叫幻听,他的阿姨是赤脚医生,“没错,你一定得了幻听!”他很肯定地说。
我不知道幻听是什么病。我的母亲是个英文老师,之前做过妇产科外科医生,我从来就没有听她说起过幻听的病症。不过,我可以写信时顺便问问她。
我和龚伟在碉楼时,又听到岭顶有人在唱歌,我问龚伟听到没有,龚伟正在玩一只刚逮到的小松鼠,他心不在焉地回答:“有啊!天天都唱歌呢。”我说是个女人在唱歌。
龚伟轻声说:“我在唱啊。”
我问坦桑。坦桑说,山里到处都有人唱歌,没有什么奇怪的。“你怎么这么留意唱歌的事?”他说这话时看我的目光很疑惧。
“我总觉得有人在唱歌。那声音从岭顶传来,却在我的耳朵里转啊转的,永远找不到出口。”我说。
“那是什么歌?”坦桑很关切地问。也许在他心目中,面前这个知青,和龚伟有太多相似之处,“不要胡思乱想,没有人在唱歌,也不会有人在唱歌。”
一连好几天,我会在半夜突然醒来,看到黑黝黝的山影里,站着好些唱歌的人,穿着很奇怪的衣服,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这种衣着。他们没有头,只有躯干,声音就从空洞洞的脖子里涌出来,连着血喷出来,我看见带着血的歌声,在空气中飞溅着。他们迈着坚定的整齐的步伐,在我面前轮番走过,唱着无字的歌,哼着相同的音调。我不知不觉地走进他们的行列,尾随着他们,一起在唱歌行走中。我顽强地相信,岭上一定真有人在唱歌。
那天,我又赶着牛橇,驮着大米和蔬菜,在沼地边缘的山路上,慢悠悠地跟在老牛后面,向山上爬行。鬼沼非常宁静,空山看不到行人与生物,连平时常有的狗吠,猎人赶狗的狗吠都没有。空气里有烟火味,看不到刀耕火种的山坡和人。我忽然又听到了歌声,那是一首我有些熟悉的黎歌,我是说那音调,我似乎在哪儿听过。我确信这是我曾经听过的歌声,我不知不觉身不由己地循着歌声而去。不,应该说是老牛跟着歌声,我跟着老牛一起,让歌声引领着前行。
过了不知多久,我忽然觉到已经走了好多时间,周围是我从未到过的山岭。我不知道这儿是哪儿。歌声似乎依稀可辨,哀怨的余音留存在我耳朵里,久久没有散去。我似乎看到山巅的树草中有人影,艳丽的筒裙,非常秀丽的形影在我不远处的树草中隐隐约约。歌声就是从那儿传来,是那人在唱歌。
她明显知道我的存在,她在用歌声诱惑我的去路。我想我是碰上女鬼了。应该说是碰上放蛊的人。传说会有懂得放蛊术的族人,把迷魂药藏在指甲里,碰到中意的人,便轻弹出去,中蛊的人,便会在黄昏时自觉到放蛊的人那里去过夜,这种所谓蛊术,通常都是男人对付女人的。
从没听说女人对男人放蛊。我一点都不害怕。那艳丽的形影让我兴奋同时心安,我确信那是某个族人女孩,在山中行猎采摘,她们都是些热情大胆、善良而又美丽的女孩。六连就有许多这样的族人女孩,从不知道城里人的那些虚情假意,把说出来的、做出来的任何事情都当真。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说的就是想的,丝毫也不知什么叫做扭捏和做作。我只想跟着她去看个究竟,释怀我多时的疑惑。我真的害怕得了信宜老鬼所说的那种病。
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转回来的,我又回到刚才的山道上。沼地就在旁边,那里依然静悄悄的。从这儿往山下望去,看得见六连和藏在茂树中碉楼的屋顶。
好多年后,我偶然在一本古书里看到类似的记载,那是晋王嘉的《拾遗记》卷四。里面写道:燕昭王七年,沐胥国有道术人名尸罗,至燕郊,“善炫惑之术”。能指端出浮屠,喷水为雾,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或化为老叟,或为婴儿,神怪无穷。
我自然不轻易相信这种无稽的方术。但是,那些被以为方术的东西,不都是人类的梦想与有意为之的伪托吗?虽然如此,原始森林里的许多幻象,还是存在的,往往在山林里迷路的人,最终会从另外的方位,无意识地回到原点。
我确信在雅加的大山里,那个让我听到她唱歌的人是存在的,她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只是出于种种理由,她始终没有让我们真正地寻觅到她的踪迹,或许,她别有不愿轻易示人的用意,山林本身就孕育了神妙。岂止是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
还是龚伟说出了其中的奥秘:我在唱啊!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了龚伟的真言。他其实是童言无忌地说出了这个世界的真谛。
信宜老鬼李前平告诉我一个骇人的消息,坦桑让大陆来的公安人员抓走了。我不相信。他说得千真万确,是他亲眼所见。我和他一直赶到沼地的山坡,从这儿可以远眺坦桑的碉楼。
这天的阳光格外灿烂,天空湛蓝湛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我们是在午后赶到沼地边缘坦桑放牛的山坡的。每天夕阳时分,坦桑会在这儿拢牛,他会敲击硕大的木制牛铃铛,分布在草丛里的牛们会慢悠悠地回到他身边。他会一头一头细细辨认和点数,把不是自己的牛只小心剔出,又四处寻找未归走失的牛,待到所有的牛都找齐了,他便把牛群赶到河边的牛栏里去。这时,已是暮色苍茫了。
离夕阳时分还远。山坡上果然没有见到坦桑的牛群,也没有见到坦桑的身影。信宜老鬼的话不是全无根据。从这儿到碉楼,还有很远的路,看似在眼前,走路差不多要两三个小时。我决定到碉楼里去。
应该说,对坦桑,我早就有预感。他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和中尉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总让人觉到他们有太多的秘密,他们的经历里也有太多令人疑虑的东西。我总感觉他们这些人始终处于危险之中。这些危险好像不是出于外部,而常常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内心孕育了他们的危险。我明白自己的这种想法本身就很危险,但我无法阻止这样去想问题。
认识坦桑,是在我刚到六连不久。我正在沼地清理沉木,中午时分,正准备歇息,我燃起一堆篝火,煨上几根刚刚挖来的木薯,用炭火煨出来的木薯,外皮焦黑,剥去外皮,再在炭火上烤得焦黄,薯肉却是雪白的,非常好吃。我刚要美餐一顿,坦桑就站在我面前。
“你叫亚雷!”他很肯定地问。
我没有正面回答,用心地审视着面前这位不速之客,我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我知道他叫坦桑,知道他是专职放牛的下放干部,知道他有一个碉楼。我请他吃木薯。他却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一根香肠。他把香肠递给我。
我没有接。香肠很诱惑,自从到六连来,几个月了,没有吃过一口肉。我知道这香肠一定很宝贵。
他把香肠放到我面前的草地上。也不说什么,从火里挑出木薯,剥皮,吃了起来。我闻到了木薯的香气。他手里有一个装满酒的瓶子,那种装咳嗽水的扁瓶子:“喝一口?”
我迟疑了一下,接过瓶子。扁瓶里的酒看起来很多,实际上也就一两口。我一口气把酒喝光,有些不好意思。
“果然不错,很好。男子汉,要能喝几口才好。”这是迄今他对我说过最长的一句话了。
他的话令人觉到我们认识好久了。
“你咳嗽,不能喝酒。”我说。
他笑笑,并不回答我。
“我听见你咳嗽的声音,很厉害,那样会死的。”不知为什么,我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关切,这不太合乎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交流。
“你说得对,是不能喝。不过,这种土造的酒度数很低,没什么酒精含量,偶尔喝喝,不碍事。何况,人的生死,与酒无关吧?”他像是在说道理,又分明在说着一些什么。我见他说这些话时,那双妩媚的眼睛里闪过一些阴影。
“那天我看见你和你的牛在沼地里!”我试探着说,对那天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怀疑那天是不是我在山坡上做了一个梦。
“哪天?我天天都在沼地里呢。”
“我说的是沼地里怎么能够走牛和走人呢?”
我不明白何以固执于这个话题。这样的话题此后我又问过坦桑好多次,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置可否。就是没有答案。连事实本身也受到质疑与否定。我究竟想要证明什么?我只能承认在那样的年代,每个人都有一种偏执的病症。我也毫不例外,始终处于一种人类的病相之中。
我和信宜老鬼赶到六连连部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今夜连长说批斗会暂停一天,理由是这几天大会战,大家都累了。批斗会改在白天工地上举行,那时团首长会到现场来参加批斗会。这无疑是一个喜讯。但信宜老鬼却不这样认为。好不容易从山上下来,连队里却冷冷清清,太不过瘾。信宜老鬼有自己的见解,批斗会一开,连队里的男男女女都到球场上来,那也是调笑调情的大好时机。那些民族女孩才不管你批斗会什么的,她们自有自己的放纵情感的方式。信宜老鬼有些沮丧,他甚至忘记他和我到六连来的主要目的:求证坦桑是否给大陆公安抓走了。
我连问几个人,直到无人可问。都说不清楚,没听说过。下放干部随时被叫走,或押到什么地方,这是常有的事,他们归连里管理,却不是连队职工,归团部的工作组直接领导,只有连长才有权知道他们的去向。
没有批斗会的连部就不是连部,家家户户早早关门闭户,冬天的夜晚就更是如此。球场上空无一人,昏暗的灯火透过草屋的窗棂影影绰绰,四野充满着一种说不出的鬼气。球场旁边电线杆上有一盏15度的电灯,灯泡吊在灯绳上,在风中摇晃,像林中的鬼火。山林中不时传过来各种莫名其妙的声音,是虫鸣,是小动物的叫声,这些声音在林中窝棚和篝火边,我们早就习以为常,可是在人烟集中的地方,就不免让人想起毛主席《送瘟神》中的诗句:万户萧疏鬼唱歌。这种诗句在那个年代,是连3岁小孩都并不陌生的。
坦桑的碉楼里没有灯火,远远望去,那棵金丝楠犹如横空出世的怪物,黑黝黝地耸在河边。我把握不住该不该到碉楼里去看看。未经坦桑允许,我从没有贸然去碉楼。信宜老鬼却不以为然,他是个没心没肺的家伙,他极力主张到碉楼去。他从没有进入过碉楼,他对碉楼也很好奇。
我想坦桑一定真的被抓走了。我一时想不出他被抓走的理由,可是,中尉不是也毫无理由地被抓走吗?
雅加河这一夜非常宁静,甚至听不到它往常淌水的声音。刚才还是黑沉沉的夜空,月亮升起来了,山野便显得清幽同时有一种更加鬼魅的印象。所有的树木和物件,在清幽的月光下,显得很迷蒙,分不清边界也就变形了原初与真相。原来柔和的也许就很粗粝,原来明丽的也许变得狰狞,世界在月光下完全幻变了原来的模样。我对雅加野外的夜晚从来都有一种很顽强的惊悸,也许与此地族人对鬼的崇拜与描述有很大的关系。族人视鬼为自己的敌人也是朋友,既是祖先的魂灵也是福音的来源,多解与矛盾的说法,令鬼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因之,从来对雅加发生的任何奇事怪事深信不疑,我总以为这与迷信无关,而与人对世界的认识过于浅陋有关。鬼有恶鬼也有善鬼,这与人世间的情形,大致都是相同的。这也是既是敌人又可以是朋友的缘故。族人的观念实在是非常入世同时非常高明的。我对鬼从来都没有恶感,只有深深的敬畏。
坦桑的碉楼,门没有闩上,虚掩着,我小心地推开那扇我很熟悉的树皮门。随着树皮门的开启,一缕月光投射在屋子中央,风吹进屋子,掀动屋子中央火盆里的火星,眼前的情景差点把我吓个半死。
没有坦桑的允许,我不敢和信宜老鬼贸然进来,我让信宜老鬼在树下等我,刚才我是独自上碉楼来的。
面前的情景,在多年以后,都久久地震颤着我的灵魂。
我犹如见到女鬼。
临窗那张我熟悉的黄花梨木做成的方桌旁,坐着一个白衣白裤的女人,面对窗口,背对屋门,漆黑的长发流泻在脑后,直至腰身。从门口射进去的淡淡月光,照在这个女人的背影上,有一种很凄凉惨绝的青白釉色。这个背影一动不动,仿佛凝固了一般。我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惊悸。有一种投错了门,进入陵室地宫的惶恐。这不是坦桑的碉楼么?坦桑的碉楼何以进入了女鬼?聊斋里的女鬼,电影和小说里的女鬼,就是这样的形象与情状。连月光也是如此青白。
她分明觉察到我的声息。
我想拔腿回跑,但已挪不动双脚,喉咙好似堵塞了木头,或被鬼扼住一般。我听得见自己心脏狂跳的音响,我听见信宜老鬼在树下狂呼我的名字。我已无力去关心信宜老鬼的存在,我只想马上离开此地。我相信今夜我一定撞上了鬼。
我陷于极度的惊恐之中,脑袋却一片空白,身体的所有功能瞬间离我而去。
冥冥中我听见擦火柴的声音,女鬼点燃了吊在窗口的马灯,碉楼里一片光明。
女鬼转过身来,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坦桑,长长的黑发,妩媚的美目,宽松的白衣白裤,若隐若现地显现着她非常美丽的胴体。非常飘逸的女人。
我更加相信这是一个女鬼,直到她叫出我的名字,我所熟悉的嗓音,令我回到了人的世界。我晕眩。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的脑袋依然一片空白。直到她走过来牵住我的手时,那手的温暖才使我回过神来,确认面前这个女人就是坦桑。
她听出我的疑惧与疑惑,她笑起来,非常迷人。这种迷人只有女鬼才有,人世间是不可能有这样迷人的笑靥的。直到今天,我依然这样认为。
“你不是男人吗?”我慌乱,唐突而且十分弱智地问,这比较符合一个16岁的男孩的知性。
“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不是女人。”她笑得很勉强也很凄楚,但很令人心动。我得承认,她是一个女性,这正是我所希望的。这种下意识的希望,其实早就萌生在我们第一次的见面中。
信宜老鬼在下面等得不耐烦,他自己跑了上来,他也愣住了。继而冒冒失失地问:“你是谁?坦桑不是被抓走了吗?你是他妹啊?”
此刻我才真正回过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