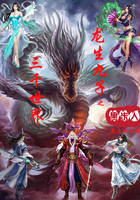林辰年的来访是郁欢意料之外的。他带了一束花来,由阿南引进门到别墅后的花园里。郁欢正坐在椅子上用手摸索着学习盲文,正摸到一个不认识的字。来人出声招呼,郁欢的手落在那个字上愣了一下没有动,随后又继续摸索着试图解读出来。
“那是‘颜色’的‘颜’字。”林辰年出声。
“应该是‘厚颜无耻’的‘颜’。”郁欢勾了勾唇角,似有些笑意。
林辰年把花束递过来,郁欢却抱着书册没有接。他倒也不意外,自己在桌子另一侧的椅子上坐下,同时将花束放到桌上。
“你应该知道,这里并不欢迎你。”郁欢说。
“不欢迎,并不代表不应该来,我带了一些东西给你。”林辰年从旁边拿过一个手提袋放到郁欢的手上。
郁欢接过袋子摸索了一下,发现是几册书和笔记本,都有些泛旧了,所以手感算不得顺滑,有一种时间沉淀的感觉,从中间散发出淡淡的余味。郁欢知道这是谁的东西,停在册子上的手不由得停下,指腹轻轻抚摸,不愿收回。
“我搬家的时候找出来的,全是她的遗物。我……我觉得自己不太方便保留,想来想去还是交给你比较好。”林辰年搓着手掌解释。
“你是不敢见孟家的人吧,否则你应该交给他们的。”郁欢收起袋子冷语反问。
“是的,我不敢,心怀愧疚之余也不想再掀波澜。我要结婚了,想以最小的影响处理一切。”林辰年坦然承认,站起身来取出一张名片放到桌上,告诉郁欢这是他联系的眼科医生,如果需要的话她可以联系。
林辰年离开,在廊下走出几步后又停下,像是心有不甘地回头,说:“即使你把自己困在黑暗里,有些事情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人总要朝前走,向前看的。郁欢,还记得当初我所认识的那个你,是多么勇敢无畏,一往无前。如今你变得懦弱胆小,仅仅因为一些人的离去,你就要把自己的整个人生否定吗?”
“你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懂的,所以也不要问。”
“是,我是不懂,你们的爱恨情仇就像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戏,我的确不懂也不感兴趣。所以,当年早早地选择退出,选择另一条并不是自己最喜欢却最合适的道路,我才拥有今天的一切。如果再选择一次,我还是会那样做。”
“你想说什么?”郁欢淡淡地反问。
“我想说,你与我是不同的人,从心底里就不同。我现实而理智,你感性而固执,我永远不懂你的世界,如同你永远不屑与我这种人为伍一样。但是有一点,活着的人不要以死去的人为借口而心安理得地退缩溃败,把自己变成一个懦夫,却将这一切的原因归结于别人,这是对那些人的亵渎。别以爱的名义为自己的懦弱找借口,还活着就应活出该有的样子,不要欺负那些离世的人无语还击,孟清是,苏卿远更是。”
“够了,这里不欢迎你,出去!”郁欢冷喝,伸手指向门口。
“郁欢,你这样作践自己,也改变不了任何事实,记住这一点。”
林辰年离开了,郁欢握着手中的盲人书册,五指紧紧扣住,骨节发白。她桌上的花香和旁边袋子的纸香混合着,原本是好闻的味道,此时却让她生出阵阵恶心,唤了一声阿南之后起身摸索到桌角俯身呕吐,将今天吃下的一切都吐了出来。
张蕊在周末的时候带郁欢出去,开车到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购物。她一直戴着墨镜,由张蕊牵着手行走。张蕊极力地想要讨好她,向她讲解着一路的所见所闻,询问她要不要吃冰激凌,要不要吃小吃,要不要喝茶,要不要街边的彩色气球,俨然将她当作牵在手心里的小女孩。
最终,张蕊选择买了一个冰激凌给郁欢,然后要她站在原地等待,自己去旁边的甜品店里再买一些东西。
听到旁边有人在弹唱,郁欢挪动几步下台阶,摸索着走到弹唱的人的前面停下。
那是一首很老的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将永远爱你》),郁欢驻足听了半首,直到感觉眼眶微微发痛,抬手忍不住轻揉。却不料一个接电话匆匆走过的行人撞上了她,将她的墨镜打落在地。那个人也不知道是根本不在乎还是不曾留意,片刻不停地远去,只留下独自在地上茫然摸索寻找墨镜的郁欢。
有人握住了她的手腕,示意她不要再乱摸,然后将墨镜小心地架回她的鼻梁上。郁欢说谢谢,然后打算抬手扶墨镜。却又被那个人握住手腕示意稍等,他用轻柔的帕子在她手上擦拭,把沾染的灰尘与杂物拭去后才将她的手放下。
“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郁欢微笑着询问。
那个人没有回答,只是将手帕放进了她的掌心。郁欢下意识地明白了,原来对方是个不方便言语的人。
“我不能视物,你不能讲话,看来我们还真是有缘。”郁欢调侃地笑言。
那个人将郁欢握着帕子的手轻轻地握了一下,意思是让她保留这块手帕,然后转身离开。郁欢却想起了一件事,对着空气唤了一声。
“等一等。”郁欢按照自己猜测的方向伸出手去。她并不确定那个人是否还能听到或理会自己,不过她愿意一试,将自己还没有吃的冰激凌递出去,说:“谢谢你,我请你吃这个吧。”
半晌,一只手接下了她的冰激凌。郁欢开心地笑了,将帕子在手里挥了挥,告诉对方自己会清洗干净,有机会还给他。
张蕊拿着甜品回来寻找郁欢。郁欢站起身回应,待张蕊松了一口气走近后,郁欢才发现身边的人不知何时离开了。
张蕊带郁欢在商场内闲逛一圈后去了一处僻静的地方。进门后郁欢被人脱去了鞋,换上一双舒适的拖鞋,走在回廊下,她听到有水声和鸟叫声,猜测这里应该是一处园林内部。在进入一处房间闻到熏香后,她确信了自己的猜测。
祁凤义从室内走出来笑着打招呼,郁欢这才知道原来今天并非只是出门闲游,而是有一定目的的,甚至她怀疑一切都是祁凤义给张蕊的建议。
“你今天看起来不错,是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了吗?”祁凤义笑问。
“没有。”
郁欢撒谎了,但祁凤义并不介意,邀请母女二人入座喝茶。那是龙井绿茶,清新而香醇,非常应景的搭配。
“你喜欢我的院子吗?”祁凤义问她。
“我看不见,所以不知道。”
“你看见了,而且喜欢,所以你在说话时才会唇角上扬。去走走看吧,这个院子很有趣。”祁凤义揭穿她,然后唤了一个人的名字,告诉他带郁欢去逛园子。
“好的,哥。”来人出声,郁欢当即听出了这是个熟悉的声音。她侧过头朝声音传来的地方看过去,也毫不意外地令对方发现了自己。
阮知秋没有向她直接打招呼,而是客气疏离地请郁欢跟自己出去。
“我们还真是有缘分,又见面了。”
“见面?我可从来没见过你,我看不见。”郁欢不以为然地摸着一处廊柱在栏杆上坐下,打算就此止步。
不过,阮知秋并没有停下的打算,而是拉着郁欢起身,催促她不要偷懒,说这个园子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她一定要去看看。
阮知秋拉着郁欢的手穿越回廊,又拐过一处拱门庭院,一路描绘所见的景色。假山湖水,竹林黑石,最后到了一处有沙沙树声的院子里,她被拉到一处树下坐到一个秋千上。
“你坐好,轻轻地晃一下听听。”
阮知秋推动郁欢所坐的秋千,即时头顶上鸟鸣四起,栖在树上的数百只鸟儿四下飞散,翅膀在空中发出声响,树叶也哗哗作响之余零星落下。
“这棵梧桐真的非常神奇,总有许多鸟儿不分时节地喜欢待在上面,太神奇了。”阮知秋惊喜地说着。
没等郁欢多说什么,她又被拉起来去了另一个院落。那里有水声,阮知秋告诉她这是一处活水泉,泉眼处立了一座假山,山上有一汪清池。他在池里养了一红一黑两条锦鲤,会用长竹竿制成的投食器每天喂它们。
喂完鱼,阮知秋也不管郁欢是否愿意,就又拖着她上了阁楼,把窗户推开让她听外面的风声,闻花香。像是桂花的香气,她猜测后面的院子里应该有一棵极大的桂花树,但又觉得这个时节是不对的。
阮知秋忙碌着,翻腾了一会儿,然后将一幅画拿出来。
“是因为我看不见,不能看见秘密,所以才带我来的吗?”郁欢倚着窗户笑问。
“你总是介意自己的眼睛,但要知道很多事情不是用眼睛就能欣赏的,比如外面的香气和风声。”阮知秋说着将那幅画拿到了郁欢的面前,立到架子上,告诉她这就是那天在野外写生的画。
阮知秋告诉郁欢画上的色彩和线条,还告诉她自己如何对这幅画进行后期精修,等等。郁欢看不见,却在脑海中凭着他的描绘有了一个概念,好像真的勾勒出了一幅画面。
随后,阮知秋又拿出几幅其他的画给她讲,讲那些画的时间与故事,告诉她在画那些画时的感觉与心情。他的故事里充满了青春与洒脱,一个自山清水秀的南水吴地出生的人,来到一个临海的城市上大学。他的画里有自己昔日的同学,有严厉的老师,当然也有学校里曾经风靡的学长学姐,等等。他用自己的画笔记录下了昔日过往,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至宝。
这让郁欢听着不自觉地入神,仿佛看见了一个白衣男孩,青葱玉立,干净爽朗。恍惚间,她将面前讲话的人当成了另一个人,好像就是当年郁湖边上的男孩。
故事最终被楼下寻人的声音打断,郁欢与阮知秋下楼。张蕊和祁凤义一起走过来,祁凤义说要让郁欢以后尽量多出门,与人接触对她有好处。张蕊也认同这一点,互道了再见后出门离去。
张蕊在家陪了郁欢几天,然后在郁欢睡下后又一次悄然离家,奔赴大洋彼岸。如同怕小孩儿因为父母离家而哭闹一样,她小心翼翼地对待郁欢。不过,虽然在张蕊看来是自己守到了女儿入睡,但当司机开车离开花园时,郁欢是坐在窗前听着的,她只是假装睡着而已。
清晨有人敲门,郁欢以为是阿南叫自己起床吃早餐。她挥了挥手表示不用叫了,自己其实才睡下不过两个小时,好不容易有些睡意,想多休息休息。
“我特意带了张妈家的豆浆和煎饼,你一定要起来吃,否则就凉了。”阮知秋的声音在门口响起,让郁欢的睡意消失。
郁欢下楼坐到餐桌前时阮知秋已经在那里了,他把带来的早餐放在桌上,要郁欢马上试吃。他告诉她,这是他在F大附近试过那么多家早餐店后评出的最佳早餐,错过就是她的损失,而她也不能拒绝自己清早排队买下然后用保温盒一路捂着送来的美食。
因为厌食症,郁欢对食物有一种抗拒。但她还是勉强尝了一些,随后又被阮知秋扣了一顶帽子,催促她换鞋子出门。
“去哪儿?”
“去钓鱼,我都买好工具了。”
“我……”
“你不要说看不见,钓鱼不用看得见,要用心听。”
郁欢被拉出了门,怀中被塞进钓竿和一只小桶,再被扶着坐上了自行车的后座。一声提醒坐稳后,阮知秋骑着自行车出发。风在耳边轻拂,清晨的露水与阳光的味道在四周弥漫,身下的自行车偶尔有些颠簸,却很平稳。郁欢仔细地想了想,自己似乎很多年没有这样坐在一个人的自行车后座了。
在湖边摆好石头搭成凳子,放线钓鱼,阮知秋如所有表现欲正强的男生一样,精力充沛地跑前跑后,郁欢则是坐在那里握着钓竿沉默。
阮知秋说他在写生时发现对面的树林里有一种花很漂亮,然后就将自己的钓竿交给了郁欢看管,他骑上自行车沿湖离开。郁欢觉得这个人是想一出是一出的,多动又跳脱,但也没有拒绝对方。
郁欢继续坐在湖边等待,听到有脚步声靠近。她以为是阮知秋回来了,但没有车的声音,所以她猜测对方是想要恶作剧,于是自己也悄然做了准备,将手伸进旁边装了水的小桶里。等到来人靠近时,她先发制人,将水洒到对方的脸上。
郁欢笑着出声,对方却毫无反应。她这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认了人,赶紧出声道歉,并摸索着从包里取出纸巾递给对方。
对方依旧没有说话,几秒后才接过纸巾。在这期间,郁欢能感到对方在审视自己,同时她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她害怕,她的心底逐渐升起一个名字,一个称谓,一如多年前她第一次见到他时的一丝心悸惊慌,然后无限放大,以至于她下意识地想要退后避让,却从石凳上滑落,好在对方及时伸手拉住了她的胳膊。
“郁欢,你瘦了。”凌锦呈开口,声音如当初一样沉静冷淡。虽是一句问候,却没什么感情,像是寒冰凝成的利刃划过冰冷的丝绸发出华丽的声音。
凌锦呈将不停向后退缩的人扶正,坐回石头上,手却没有松开,似乎上下又打量了郁欢一遍,手指落到了郁欢的墨镜边沿,说:“你的眼睛又复发了,多久了?”
“不关你的事。”郁欢扬手将凌锦呈的手冷冷挡开。
她摸索着扶住石头起身,走到旁边试图将钓竿收起。但是那渔钩似是钩住了什么东西,怎么也拉不起来。
凌锦呈走近,用双手握住郁欢的手,要她将线放松一些,先抛出去再将线拉动收回,轻松地就解决了一切问题。
郁欢自他的手碰到自己时就在抗拒,但凌锦呈的力量足够将她的挣扎抹平,不紧不慢地收回了线与竿后才松手。
“你应该知道我不想见到你,见一次就厌恶一次。”郁欢握着钓竿出声,表情冰冷。
“你又何曾喜欢过我呢,不是一直如此?”凌锦呈笑了笑。
郁欢不想再与他多交流,转身连石头旁边的鱼桶都不要就打算离开,却又在与凌锦呈擦肩而过时,被抓住手腕。凌锦呈低沉冷清的声音响在她的耳旁,叩动她的神经。
“下周清明我会去扫墓,也许你会愿意一起去。”
稍有两秒的停顿,郁欢还没有说什么之前,有自行车轮碾压石子与石板的声音,伴随着铃铛一路而来。随后是阮知秋的声音响起,询问凌锦呈是谁,为什么要拉着郁欢。
凌锦呈没有回答阮知秋的问题,而是侧目打量这个大男孩。清爽干净的黑色头发,刘海儿斜过好看的眉梢,一双明亮而充满活力的眼睛,脸上带着些警惕与倔强。身上的白衬衫配着黑长裤与球鞋,看起来与当年在郁城见过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他竟生出恍惚。
“你是谁?要干什么?”阮知秋将自行车停下走过来,也上下打量面前这个身着西装的男子。
他看起来很年轻,却有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内敛,静得如同一口幽深古井,神秘而危险的气息无处不在。
两个人直视对方,也互相审视。最后,凌锦呈松开了郁欢的手腕,却没多说一个字,自两个人之间擦肩离去。在不远处等待着的司机驱车上前来为他开门。
黑色的车身在阳光下划出优美的弧度,泛着流动光润的线条经过他们身边,凌锦呈的面容消失在逐渐升起的黑色车窗后。郁欢立在原地,侧着身子不为所动,阮知秋却疑惑地蹙眉。
在车子离开后,阮知秋迅速将这件事情抛到脑后,回到自行车旁边,从兜篮里取出一束自己采的花递给郁欢,告诉她这花有几种颜色,上面还沾着清晨的露水。
“对了,我还做了一个礼物送给你,猜猜是什么。”阮知秋卖着关子问她,语气中的小小得意让郁欢在看不到他脸的情况下,依旧可以想象得出他此时的自信和小傲慢。
“不知道。”郁欢握着手里的花束嗅了嗅回答,尽管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答案。
“是顶花冠,这种藤条柔韧又有曲线,非常适合做花冠……”阮知秋笑说着,将一个编制的花冠戴到郁欢的头上,然后帮她梳理调整了齐肩的短发。之后,他像是十分得意于自己的作品,让郁欢站着不要动,要给她拍一张照片。
“真后悔没有带上画架,只能退而求其次对着照片取景了……”阮知秋拍着照片笑说。
阮知秋拍完一张,又上前替郁欢调整了发梢。在返回去重新拍照时,他说了一句话,让郁欢原本配合着上扬的唇角瞬间僵硬了,如一颗石子丢进了平静的湖心。
“你应该留长发的,一定很漂亮。”
一样的话,从一样青春飞扬的大男孩口中说出,郁欢听在耳中,却如听闻远山空谷回音,从记忆的深处传出回响。她已经很多年不曾留过长发了,但凡长过肩膀一点儿她就会立即剪掉,甚至曾经的中分也特意改成了偏分,颜色不是当初的纯黑色而染成浅浅的棕色,一切不再与学生时代的自己有丝毫重样。
郁欢垂下头,将手中的花束摸索着放回车前篮子。正欲再取下头上的花冠时却被阮知秋阻止,告诉她不要摘下来。
“我带你去游湖吧,沿岸的风景非常美,你一定不会失望。”阮知秋笑着说,一贯地不由郁欢拒绝推辞,将她拉着安顿到车后座上,收起钓鱼的工具,让郁欢提在手中。然后他抬高了声调告诉郁欢这个唯一的乘客:“请扶紧坐稳,‘知秋号列车’就要发车了!”
知秋号,郁欢忽然觉得阮知秋这个名字真是不错,如果在深秋时节听来会感觉非常贴切,知秋,知秋,不知已深秋。
“你是在秋天出生的吗?”郁欢坐在车后面问道。
“很多人都因为我的名字而这么问我,不过我是夏天出生的。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妈妈想秋天快点儿来吧。”阮知秋一边踩着自行车向前,一边说笑,话语声与笑声迎风向后散落。
“你没有问过她吗?”郁欢好奇地问。
本是随口一问,没有料到气氛就此发生了变化。阮知秋踩着自行车的双脚逐渐慢了下来,最后点地停住,扭过头来看还微伸着脖子询问自己的郁欢。虽然郁欢看不到他眉眼间流露出来的落寞与悲伤,却还是从这停止与沉默间意识到了什么。
“我是个孤儿,被哥哥的父母抱养长大。他们跟我说,那时候我的襁褓里只放了一张写着我出生年月和名字的字条,这个名字是他们唯一留给我的东西。”
“对不起,是我多问了。”郁欢微微垂首,有些尴尬。
“没事,祁家对我特别好,像对亲生儿子一样,哥哥也特别照顾我。我很知足,也很感恩,非常幸福地长大到现在,所以没有什么不能谈及的。”
阮知秋解释着,也宽慰了在自责的郁欢。在笑声过后,他要郁欢坐稳就继续骑车向前,甚至在郁欢没有问及的情况下讲了更多关于自己的事情。
阮知秋出生在江南的一个城市,自小被祁家抱养,有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哥哥祁凤义。他自小学习成绩优异,高考后本有机会去北京上学的,最后却选择了上海的F大,原因是想离家近些,离亲人近些。
因为生在江南,他家不远的巷子里曾住有一位名角,每日清晨总喜欢唱上几句戏。他自小就对此很入迷,闲暇时间就喜欢去听。那位角儿看他聪明伶俐,也教了他一些。
“有机会你一定要去听玉老爷亲自唱一回,那才是真正的江南韵味。”说起这位教过他戏的玉老爷,阮知秋的语调上扬,带着无比的自豪。
阮知秋说了自己的一些琐事,有些沉默。郁欢觉得他有些问题想问。果然,不一会儿他到底还是沉不住气了,问:“今天那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不是。”郁欢简单平静地给出答案。
许是这语气太过冰冷,阮知秋感到这个人的一切对于郁欢而言是个禁区,所以不再提及,又唱着歌继续前进。迎风临水,晨风习习,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美好的了。
三天后,郁欢离开了别墅。尽管阿南一再劝阻,提出想要随行前往。郁欢还是拒绝了她的陪同,只让她替自己收拾了一套换洗的黑色衣裙和一些日常用品,告诉她自己三天之内一定回来。
门外,凌锦呈立在台阶上,负手背对着大门,正在眺望远处的树林与山地。那里是一片高尔夫球场,有湖有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有着大片的留白,如一幅水墨写意山水画,徐徐勾勒之间隐藏着气象万千。
郁欢站到台阶上感受着晨风,初暖还寒的空气中还透着一丝湿气,有着露水与草木的味道。一个冷冬败退,万物复苏,衰败与新生更替并存的时节,也是一个谁也逆转不了现实、需要接受命运拂过的时节。
凌锦呈伸手从阿南那里接过行李,将一只手递到郁欢面前,欲扶着她下台阶。但是郁欢倔强地侧过了身子,凭着对这所别墅的了解自己试探地迈步下台阶朝前行去。此时,她在心底感谢祁凤义那个有些无礼又不专业的心理医生,和他那个青春开朗到耀眼的弟弟阮知秋。他们一直要自己出门的目的就是让她真的可以有这样自由行走的时候。
坐上凌锦呈的车,司机关上门,平稳地驶离这片别墅区,朝机场而去。
一辆车,三个人,两个并排坐在后座的人都很安静。郁欢戴着墨镜朝向前方,凌锦呈坐在旁边,似乎是在翻阅资料,时不时有纸页翻动的声音在空气中带过。最后他将文件合上放到旁边,又打开电脑工作。
到机场后,郁欢抵达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她依旧试图凭自己的能力独立行走。但在下车之际就踩中台阶的边沿,好在凌锦呈及时将她扶住才没有摔下去。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怜,就像是你手里随时可以捏玩的一个小泥人?”郁欢站直身子问。
“没有,我只是觉得你比从前更讨厌我了。”凌锦呈松开扶她肩膀的手,但握着她手腕的手却没有放开,带着她朝机场内行去,接着说出了另一番话。
“不过,此时此刻你只有与我相依为命,我也只有你这一个伴。你要信任我,而且必须只能信任我。那个小男生,甚至所有那些后来的人都与你不一样。过往像一口深井,你困于其中,我是你唯一的同伴。”
郁欢心有不甘,五指紧紧握拢成拳。凌锦呈带着她前去办理登机事宜,走的VIP(贵宾)通道。郁欢厌恶又不得不忍受着凌锦呈的一路照顾。
当空姐递过毛毯时,凌锦呈接过来替她盖上。她终于做出了反抗,扬手将其挡开,却冷不防将桌上的水打翻到凌锦呈的身上。
空姐忙不迭地要替凌锦呈擦拭。他淡淡地挡开了对方忙碌的手,解开安全带起身,在离开时告诉郁欢他去洗手间处理衣服,稍后回来,要她别乱走动。
“小姐是和男朋友吵架了吧,您男朋友对您可真是贴心又温柔。”空姐蹲在地上一边擦拭水渍,一边笑着感叹,言语中多是羡慕。
“你想多了,他不是我的任何人。”郁欢尽量客气地一语带过。
“怎么会呢?那位先生看您的眼神里面全是爱意,他一定非常爱您,您就不动心?”
“他不配。”郁欢侧过头去,言语冰冷。
热情的空姐意识到这两个人的关系并非如自己所想,又感受到郁欢身上的冰冷,知晓自己不能再多说,低下头赶紧认真地处理事情。
凌锦呈坐回来时手中又多了一条毯子,再次盖上郁欢的膝头,并且在郁欢要扬手挡开之前将她的手按住,凑近了些低声开口。
“郁欢,就算你不肯承认,你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那条毯子最终还是盖在了郁欢的身上,凌锦呈甚至还替她贴心地调整了腰上的安全带以便她坐得更舒适,最后将一个小枕头垫到她的脑后,告诉她好好睡一觉,落地的时候会叫醒她。
“凌锦呈,你真是一个恶魔。”在凌锦呈收回身子坐稳前,郁欢面带微笑侧头吐出一句,随后安然地闭上眼睛侧头休息。
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在A城的墓园里,郁欢一身黑裙立在墓前。一方黑色大伞撑出一片天空,替她挡去雨水,但那随风斜入的细雨还是沾湿了她的鞋袜,正在搬家的蚂蚁从她的脚下成群结队地经过。
她手上捧着白菊,花茎已经在手心有了些许温度,上面青绿色的汁液将她手心染绿。但她就是面朝着那块灰黑色的墓碑,迟迟不敢再靠近去将花放下,或者说拿不出离那墓碑上如花的青春笑靥再近些的勇气,尽管她根本看不见。
那张照片她知道,因为孟清的父亲孟军当时没有孟清合适的照片放在墓碑上,只能向郁欢讨要一张。于是,她从一堆从前的旧照片里挑出了一张孟清满脸笑容的照片交给孟军,希望这个世界最后能够定格住的是她的美丽与幸福,天真和清纯。
那张照片是高中时照的,孟清乌黑的长发垂下肩头,身着白色衬衫,是学校统一的夏季校服。她甚至记得这张照片是在学校旁边的影楼里拍的,当时她们正聊着高中毕业后的计划与未来的理想。
“她说过,她毕业后想当播音员,要上《新闻联播》的那种。或者当个摄影师,给《国家地理》杂志拍封面的那种。”郁欢有些入痴一般地开口,似是与身侧的凌锦呈对话,又似是与自己。
最终,郁欢还是迈出了一步,走上前去,越过脚下的蚂蚁军团组成的搬迁长龙,蹲到墓碑前与那张照片直面相对,迎视那张笑脸。
唇角微弯,眼角上扬,明朗靓丽,神采飞扬,一切恍如昨日,但一切也只如昨日了,前尘往事不可追寻,不能回头。她一次次地在梦中看见往昔,又一次次地自梦中醒来时跌进现实的深渊。
郁欢伸手轻轻抚摸那张照片,用手指将墓上的尘土清除,最后扶着墓碑久久闭目不语,任由细雨淋湿了裙摆。
林辰年会来扫墓不意外,这几年的清明节他都过来。这次他还是带来了一束百合花,因为孟清最喜欢的就是百合,她也很像这种花。
在孟清的墓碑前,郁欢蹲着,两个男子立着,一人手执一把黑伞。越过雨幕与伞沿,他们四目相对。他们从未真正见过面,却都知晓对方的一切;从未谋面交手,但已经各自抽刀拭血数回。
“久闻凌总大名多年,幸会。”林辰年开口,伸出手去。
凌锦呈并没有与他握手,只是淡淡地侧目转身后蹲下,与郁欢一道将墓碑前的杂草与尘污清理干净。然后,他将郁欢扶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去。
“凌总,你这样未免有些失礼。郁欢有资格,你又凭什么,你才是害死孟清的元凶。”在擦肩而过时,林辰年开口。
凌锦呈的脚步停下,林辰年以为他被自己击中而勾动唇角,转身打算正视他再说些什么。但是在转身后,他发现凌锦呈停步并非为了自己,而是另有原因。
孟军苍老了许多,人还未靠近就先听到一连串的咳嗽声。他坐在轮椅上,被一个护工推着过来,尽管撑着伞,但他膝盖以下的鞋裤已经湿了大半。在轮椅停下后,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看清墓碑前的三个人,之后那浑浊的眼中有光掠过。出身军人的他有着极好的情绪控制能力,但还是露出了愤慨与厌恶。
“你们都走,我女儿不需要你们虚伪的吊唁。”
郁欢似有话想说,凌锦呈却暗中握紧了她的手腕示意不必,拉着她从旁边离开。林辰年也随后离去。
“把东西也带走,不要弄脏了我女儿的墓地。”孟军冷声道。这是个尴尬又无奈的场面,所有人都无所适从,但没有人会在此时此地与孟军争辩或解释什么。林辰年回身将自己的那束百合拿起先行离开。
“郁欢,你也走吧,我想一个人和女儿待着。”孟军没有回头去看,但在感到郁欢不愿意离去且欲言又止后开口。
郁欢在凌锦呈的引领下离开墓园,在出门前最后回望了一下那片墓碑林立的墓地。
有一刹那她似乎看清了眼前的场景,见到那照顾孟军的护工也走到了树下避雨。孟军坐在轮椅上,独自撑着一把大大的黑伞,像是一团在死亡中心地带的阴影,孤独而绝望地坚守着他终生不肯释怀的情感。
而在她眨了眨眼睛后,发现世界依旧一片黑暗,不知道那是片刻的幻觉还是自己的眼睛已经发生变化。
来到墓园外,林辰年居然没有离去。他提出要与郁欢单独谈一谈,凌锦呈不置可否让郁欢自己决定。
几分钟后,凌锦呈独自撑着伞立在路边等待。郁欢与林辰年共撑一把伞,在另一侧的路下相对而立谈事情。
“我要结婚了。”林辰年开口。
“这个不必告诉我。”
“对方很爱我,她的父亲对我的事业也有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昨天我向她求婚了。一切很顺利也很成功,她在鲜花和戒指面前感动落泪,说这辈子都只爱我一个人,只相信我一个人。她急切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的亲朋好友,还上传了所有的社交网站,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她要嫁给我了。”
“你想告诉我什么?直接点儿。”郁欢打断他。
“我希望从前的事到此为止,我以后也不会再来这里了,你也不要再向人提起了。我不希望年少轻狂时的事情对她造成伤害,她是个好女孩。”林辰年说。
郁欢笑了,泛着冷,又带着嘲讽,说:“林辰年,你真可怜,当年是,现在依旧是。”
“你这是答应还是不答应?”林辰年问。
“不答应,你永远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承诺,我也无须给你任何获得安心解脱的承诺。”
郁欢转身自伞下离开,在雨幕里朝着凌锦呈行去。细雨随风拍打在她的脸上,浸入肌肤的寒凉让她清醒无比。
尽管她眼前一片荒芜黑暗,每迈出一步都有可能摔倒,但她一步不停地挺直后背前行。直到凌锦呈来到她面前,将她的手腕抓住,把伞撑在她的头顶带她离开。
一场春雨连绵不绝,各地连续发出了洪涝预警。返回上海的飞机遇上强烈的气流,飞机晃荡间让空姐们都下意识地蹲在地上扶紧四周的椅子,或是跑回后排系上安全带。有胆小的女生哭了起来,随后带起传染的效应,更多人开始轻声呜咽。
郁欢坐的是头等舱,与身后经济舱的人有帘子隔着,但那里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拉长越发清晰地传递过来。
郁欢紧紧地抓住自己座位的扶手,闭上眼睛调整呼吸要自己不去多想不去害怕。而旁边的凌锦呈相对于其他人的混乱惶恐更是冷静得可怕,甚至还在翻看着工作文件。
“你一点儿都不怕死吗?”郁欢发问,并不是关怀,而是一种疑惑。
“有很多事情比死还要可怕,我见过。”
凌锦呈淡淡地回答着,合上文件放到一边,侧过头来将郁欢身上下滑的毯子朝上拉了拉,顺势握住了她紧紧攥住座位扶手的手,将她的手握进掌心。
“不用怕,会没事的,老天爷是个贪玩的孩子,他还没玩够,所以不会这么简单地就要我的命的。”凌锦呈轻轻地拍她的手背笑着安慰。
几分钟后,飞机终于穿越了气流区,一切回归平稳,各种杂乱的声音消停下去。空姐在广播里发出了即将分发晚餐的消息。
人们放松神经,又享受起轻松的飞行旅程。
“你们这一对可真是镇定,好像一点儿都不怕死,真是厉害。”同排通道那边的白发老者擦着额头的汗渍感叹,其他同在头等舱的人也笑着附和。
“你们一定非常相爱吧,所以想着两个人在一起,就算死了也不可惜,感情真是好。”一位年轻的女士满脸羡慕地感叹。
说话的人多了,两个主角却一直没有言语,似乎他们不说些什么就结束不了这场议论。最后,凌锦呈开了口,微笑地望着已经编写好一个旷世蜜恋故事的众人,说:“是的,我很爱她,至死不渝。”
众人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后一脸满足,在他们眼中,有情人终成眷属是皆大欢喜、众望所归。他们自以为聪明地不再追问,甚至还为自己的聪明而扬扬得意,却不知那外人眼中的如花美眷,只是当事者的相看两厌。
月夜,郁欢被送回别墅。尽管才离开三天,阿南却像是多年未见一般急匆匆地迎上来,扶住她的胳膊,接过司机手里的行李后要领她进屋。
不过郁欢却让她先进去,阿南看出她是有话要对凌锦呈说,就先进去,司机也返回车内等候。
两个人在门外台阶上一上一下地立着。
“凌锦呈,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
“如果我不答应呢。”
“你凭什么否决,你我之间已没有任何情谊。”
“那是你的想法,不是我。”凌锦呈迈步登上一个台阶,与她靠近一点儿。
郁欢安静地立在那里,看不见任何事物,四周也一片寂静,静到她甚至可以感觉到对方轻轻的气息。
半晌后她微微前倾身子,凑近凌锦呈的耳边,说:“我真诚地祈祷你永远得不到所爱,也永远不被人所爱。你的一生都将孤独冷清,世人皆欢,唯你无欢。”
听到这样的决绝之语,凌锦呈没有愤怒,甚至轻笑出声,又朝前迈进一步,与郁欢站到同一个台阶上,逼得她不得不后退一步。
同样,凌锦呈也前倾了身体,靠近郁欢的耳边,留下了一句话。
“你看,我们注定是一个世界的人,多情又无情。”
凌锦呈坐进车内,驶离白色的别墅区域,远离光明的领域向无尽的黑暗前行。那车像是一道孤独前行的微光,渐行渐远,最终也被黑暗吞噬。
郁欢站在台阶上,任凭夜风吹乱自己的发,久久伫立,最后转身要回屋时却不料被台阶绊倒摔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