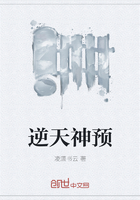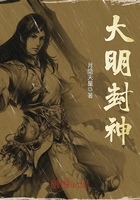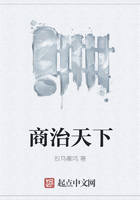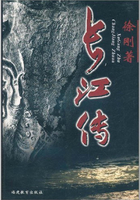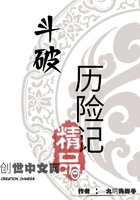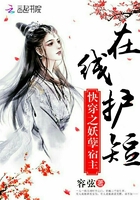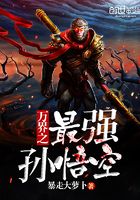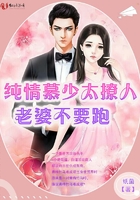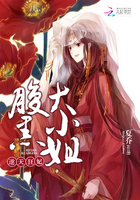乡试考的内容并不非常复杂,寒篁从小饱读诗书,连《皇乾经解》《续皇乾经解》也在手头经常翻阅。作诗吟赋对于她来说更是小菜一碟,没有什么难度,但毕竟是国家的考试,寒篁没有懈怠,她有心事缜密的习惯,无论做什么都会付出百分之两百的准备,以做到万无一失,两个月来,她已经高效率作了准备,不仅不断锻炼自己的作诗能力,有时候还背书到半夜。
三年一次的乡试即将开始了。乡试是科举的第一道门槛,要成为一名进士,有三道门槛:乡试、会试、殿试。只有通过了乡试和会试,方才能成为一名贡士。
乡试考期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八月九日,当天边浮现一抹光亮的时候,贡院里也渐渐有了动静。院役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看到屋外摩肩接踵的人群,脸上没有任何惊奇之色,显然是已经见惯了的。贡院考棚,全部坐北朝南,大小相同,因而考生坐在考棚里,是看不到其他考生的,这样也是为了避免打手势作弊。前一排考棚和后一排考棚之间间隔甚宽,且杂植各种花木,挺赏心悦目的。
考棚最南有东西辕门,辕门外面用木栅栏围了起来,将所有的考棚圈起来,建成一个大院子。院子的北面有一扇大门,这个门就是人们常说的“龙门”,取“鱼跃龙门”之意。这个院子除了考棚外分成了三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个院子,供衙役们进行第一道检查,中间一部分供考生站立等候喊名,后面一部分是一个房间,考官坐房间西边,面对东面点名唱保,确认无误之后方能进入最后边的考场。此时院役们停在最前面的院子里,他们分成六队,检查考生们的证明和随身携带的行礼。这些院役检查得都很仔细,学子证明上要有姓名、年岁、及冠、体格,以及容貌特征,同时还要写清楚父母三代的履历。像戚寒篁的证明上,写的就是“年二十,体貌端庄,面白无须,身高七尺……”。也有考生证明上写的“无须”,而因为长期不打理蓄起了胡须,衙差们会当场拿剃刀帮他剃了。考生带的行李,纸是不准带入场的,哪怕是一张白纸都不行,砚台都不能过厚,以防中间空心携带小抄,衣服和袜子都必须是单层,水是不能带的,考场里面凉水不要钱,水壶要钱,热水更是要四十文一壶。允许带食物,但所有的食物都要经过院役的检查,戚寒篁庆幸的是,衙差没有直接上手,而是拿专门的刀具,将食物切成小块。之所以检查得这么仔细,就是怕考生作弊,夹带小抄之类的东西,如果院役们在外面没有检查出来,在考场里面被查出来,院役们也要担责任,轻则仗罚,重则开除公职。
朝阳升起之时,戚寒篁和秋素石终于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防线。考棚非常简易,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座位,十分简单,戚、秋二人坐下来,要了一个小火炉和一些木炭,这些花费了不少银钱,又托了院役将带来的小锅盛好凉水,待升起火来后,再将笔墨砚一一摆好,磨好了墨之后,方才不疾不徐地打开封卷。这试卷上没有题目,是十几页红格子宣纸,每页十四行,每行十八字,以及一些草稿纸。
戚寒篁肃然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右手一屏之隔的正是秋素石,两人虽服饰上都差不多,气质却大为不同,经过命运的悲惨洗礼,戚寒篁也蜕变成了一位外柔内刚的坚毅“男子”,秋素石却更为平淡一些。
不多时,试卷便发下来了。寒篁看了看试题,抿嘴一笑。
此场考试是乡试的第一场,叫做正试。这一场考题为四书文二篇、五经义二篇、内容、体裁不限的咏物诗二首。这些题目都不难,类似于现代的填空题,一些句子去掉中间几句,或者干脆整段挖空,考生需要在答题纸上默写出正文并解释其意,正试录取比较宽松,只要默写正确、语句通顺、字迹端正就可以录取。戚寒篁这些日字天天琢磨着写诗,还是很有用的,做出两首押韵的诗不难。
戚寒篁见贡院号房前杂种着豆蔻、白玫瑰、茉莉花、石榴等花木,她最爱的是豆蔻花,绿叶瘦如碧芦,每一花穗有数十花蕊,淡红鲜妍如桃花,花蕊下垂如葡萄,又像火齐璎珞及剪彩鸾枝,于是写了一首《豆蔻花》:“绿叶蕉心展,红苞竹箨披。贯珠垂宝络,剪彩倒鸾枝。且入花栏品,休论药里宜。南方草木状,为尔首题诗。”又写了一首《闻茉莉香》:“青琅玕里白玫瑰,不受尘氛天自开。茉莉一如知我意,并从轩外送香來。”
秋素石见石榴花烂漫开放,艳如缨绂齐集,红光浮泛,灿若阳羲驻驾,火龙耀鳞,便写了一首《安石榴》:“轩前轩后安石榴,株株相映花枝稠。有如牙门集缨绂,碧油幢外红光浮。又如青天驻羲御,火龙鳞鬛惊人眸。无穷功名姑且置,赏花不觉日西收。”然后也写了一首《茉莉花》:“冷艳幽芳雪不如,风露翠藤叹扶疏。书生浑作寻常看,曾侍君王白玉除。”
天色还早,已经有人陆陆续续的交卷,戚寒篁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又检查了几遍答卷,自觉没有问题,通过第一场应该稳了。乡试都是当天结束的,不会发蜡烛,因而戚、秋二人出考场的时候,还看到许多考生正在奋笔疾书。
走出考场,戚寒篁觉得突然轻松了许多,试题对她来说比较简单,但她没有将喜悦之情显露出来。
此后十二日和十五日的考试也不在话下。
乡试得中的榜单放了出来。
“噫!快看呐,解元果真是那戚寒松啊!”
“你也不看看之前人家的名声是多么的大哟?”
“就是就是,之前就流传出他的诗篇,那写的真叫一个好!!!”
“唉,我怎的又没上榜!”
……
无数举子围簇在榜单前,有中榜欣喜若狂、手舞足蹈的,也有落榜哀呼惨叫、神色颓废的……
众人的喜怒哀乐,都系在眼前这张榜单上。
“寒篁,恭喜啊!”
“同喜,同喜。贺喜哥哥得中乡魁。”戚寒篁、秋素石两人就在一旁的茶馆里坐着,早些时刻便看到了榜单,如今正悠然自得地坐着喝茶,看那些百姓们挤在一块儿,也落个清闲。
乡试对戚寒篁来说可能只是开胃小菜,此后,还有会试,殿试,那是国家级考试,寒篁想到这里,她将喜悦的心情压了下来,一次乡试而已,不必如此兴奋,自己将来毕竟是要成大事之人,格局比别人要开阔些,寒篁暗下决心,一定要过关斩将,完成自己的使命!接下来,就看会试一战了。
乡试过后几个月便是第二年春季二月的会试。会试与乡试有所不同,考试内容重策论,轻诗赋,对于时务的知识储备要求也更高得多。会试参考人数是乡试的一倍,应考者为各省的举人,自然都是有备而来,满腹经纶者,不可小觑,虽说如此,但肯定也混杂着些死记硬背之人。会试一锤定音,能否当官就在于此,选出来的贡士直接服务于国家,死记硬背自然不行。
戚寒篁读书甚早,对于史书、志书、各种会要也读得不少,对子书、集书中有关施政方针的议论相当熟悉,但她并不止步于此,时常买些杂书闲书来看,喜欢和朋友谈论奇闻怪论,无所不谈,有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意思,但会试是否能轻松通过,还是个未知数。
张尚书和陈老师担忧戚寒篁和秋素石年纪太轻,不谙世事,也不知道关心国家大事,便在考前的频频召开小型社集,请来一些士子,就经世济民之道高谈阔论,但担忧明显是多余的,他们常去茶楼酒肆、市坊街巷听取民意,朝廷里的事情也了如指掌,自己有疑惑的地方就会请教陈老师,或者彼此讨论一番,但此中必有她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