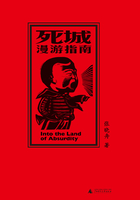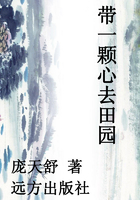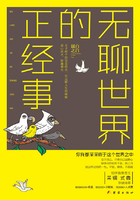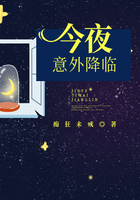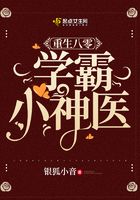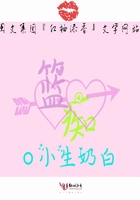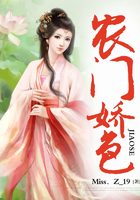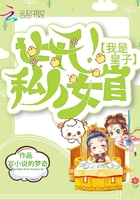《鲁迅还在》出版之后,责编李黎又来“敲门”,问我正在写什么,是不是可以继续合作。我只能回以惭愧二字,诸事繁杂,学问是需要静心思考、潜心来做的,只能期待未知之来年了。说起来真是十分怀念十多年前,毕竟时间一大把,只要有人约稿,就有可能会动心动手。当年的《鲁迅与陈西滢》就是如此写成的。《鲁迅与陈西滢》?为什么不能重新出版呢?鲁迅与诸论敌的笔墨官司不断被人评说,“鲁迅和他的论敌”几乎是鲁迅话题热点中的热点,有一本专门讲述鲁迅与其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论敌陈西滢的书,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其中的往来、冲撞、恩怨,与之相关的人物、事件、反响,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这是李黎的观点。
我以为这是一个好建议,不是我的小书写得有什么出彩处,而是当鲁迅与其论敌逐渐被演变成文人之间吵架的“标本”,“骂人”成了鲁迅的性格标签的时候,尽可能以符合当时情形的态度,谈一下鲁迅与其论敌之间的笔墨往来,努力更真切地认识到鲁迅论战的由来、过程以及文章做法,更具体地知道,鲁迅的论敌既非“反动文人”,也不是风雅无尘。鲁迅在论战中最终都会处于上风,这其中有一半的原因,实在是鲁迅比他的论敌更会做文章,更懂得“论辩”之道。后来的风云不断地为此涂抹上种种多余的颜色,剥离这些不必要的“加码”,却也并不能改变鲁迅在论辩中彰显文章魅力的事实。
陈西滢是鲁迅的第一个论敌,也是他真正没有宽恕,论战过后仍然经常“捎带”的论敌。鲁迅杂文的文体风格,我以为是经过《坟》的“长”、《热风》的“短”的探寻之后,从《华盖集》开始确立的,而《华盖集》里的文章大多涉及与陈西滢的论战。也可以说,正是从与陈西滢论战开始,鲁迅找到了既有具象又每每推至类型化的杂文形象,抓住了与己相关的事件又进而论及历史、国民性、智识阶级的虚伪性,等等。鲁迅与陈西滢之争,实是一个大话题。
反观陈西滢,其实也是了不起的深谙文章之道的人物。我现在重新回过来看自己写的这本小书,意识到对陈西滢的描述还不够充分,这主要是因为对其经历、文章、性格等等了解不深。不过在鲁迅与之关系的话题下,能获得的更新资料也是非常有限的。其实我在写作时已经意识到,研究“鲁迅与陈西滢”的难点在于资料太少,但也迫使你必须深入解读两人文章,探讨其得失、胜败所致因素。他们二人没有私人间的交往,都是“靠作品说话”,有难度也更有价值。有些话题,可能因文章之外的恩怨因素过重,阅读者通常会关心谜底何在,八卦如何离奇等等,而忘了文章才是根本,如讨论鲁迅与周作人。
此书能有机会重新出版,当然首先要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信任,感谢李黎的坚持。重印之际,又怀想起与此书有关的不少朋友和前辈。感谢原任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李良元,他曾在酷暑之际坐长途大巴从石家庄奔波到太原,就为了当面交流修改意见。此书当年是受董大中先生提议开始的,其间先生还在学术上给予我多方面帮助。此书出版后,孙郁、陈漱渝等学者都曾热情推荐和鼓励,其情令人感佩。
希望这本“新书”能在新面世之后让读者果真能有一点新收获。
作者
2018年4月29日
我对“鲁迅与陈西滢”这个题目开始感兴趣并决意要做一回梳理和研究,是近一年来的事。凡关注鲁迅研究动态的人都会发现,近年来,学术界对鲁迅和他的论敌之间的论争文选、鲁迅的笔战经历,已有多种著作和论文进行过梳理和描述。除了鲁迅与高长虹、鲁迅与梁实秋、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论战和恩怨被大书特书之外,一些与鲁迅曾经发生过论战,但个人经历并无多少新鲜材料可以公布的论战对手,专题研究与论述尚有开发余地。鲁迅与陈西滢之间的论战究竟有多少可以挖掘的资源,研究这样一个题目对鲁迅研究来说有多大的意义,是我在阅读相关作品、资料时反复思考的问题。鲁迅与陈西滢,并无个人间的实际交往。他们是一对纯粹的笔战对手,他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以笔战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关系,在鲁迅和他所遇到的论敌当中,算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情形。
单纯的笔战是否可以成为一个以人物关系研究为主的论题?从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和得出多少具有特别意义的主题和内涵来?这同样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在鲁迅研究领域当中,想要寻找到一种前人未曾发现的话题实在是太难了,想要在一个既有的话题下找出新的研究材料也一样很难。近几年来,关于鲁迅与他的论敌的恩怨是非,学术界谈论较多,一时成为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片新天地。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鲁迅多年来与其论敌之间争论起因、争论过程和争论结局的分析,粗线条的描述和鲁迅与其论敌间的论战文章辑录占其中的绝大多数,深入的研究著作尚不多见。近年来,已有论者对鲁迅与高长虹、鲁迅与周作人等专题进行过个案分析和详尽论述,在这一领域,仍然有许多值得后人进行认真研究的论题。鲁迅与陈西滢,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陈西滢是鲁迅的第一个论敌
陈西滢,本名陈源,曾留学英国,一九二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是“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文名因创办《现代评论》杂志并开设“闲话”栏目而大起,更因这些“闲话”引出同鲁迅的笔墨官司,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重要文化人物。鲁迅的《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中的多篇文章就是针对陈西滢的“闲话”而写。鲁迅曾指出,陈西滢曾说他的杂感“无一看的价值”,只要看看《华盖集》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陈西滢一生除后来结集的《西滢闲话》和少数散文与译作之外,著述很少,但他因此带来的“名声”却很大。研究鲁迅与他的论敌,陈西滢是首先要遇到的重点人物。
说“首先遇到”,是我以为陈西滢是鲁迅认真对付、刻骨铭心的第一个论敌。翻读《鲁迅全集》会发现,在“五四”初期,鲁迅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尽管在白话文运动及“青年必读书”等方面,鲁迅的观点与言论受到来自守旧派的攻击和批评,但并没有什么具体人物成为鲁迅穷追猛打的对象,林纾、陈铁生、柯柏森、梅光迪等,鲁迅对他们的反驳也都是始于言论,止于言论,并没有发展到纠缠的地步,也没有形成足称“事件”的规模,都属于正常的言论之争。而陈西滢,则是鲁迅遇到的第一个值得认真对付的“论敌”。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鲁迅杂文半数以上的篇什,都与陈西滢及其所代表的“现代评论派”有关。可以说,鲁迅的第一个论敌,正是陈西滢。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鲁迅的杂文《并非闲话》,这是鲁迅与陈西滢的第一次正面“交火”,从那以后,一直到一九二七年,鲁陈之间的论战就从未间息过。促发鲁迅与陈西滢交战的直接事件,是发生在一九二五年的“女师大风潮”。在支持还是反对学生运动方面,鲁迅与陈西滢之间发生了重大分歧,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论战主题。“学者”“公理”“正人君子”“流言”等等鲁迅论战中的名词,从这时开始大量出现,鲁迅笔战的风格,“不能带住”的韧性战斗精神,正是通过与陈西滢的笔战确立下来,并为世人所熟悉。
陈西滢同时也是鲁迅最为耿耿于怀的论敌。“五四”初期,鲁迅的杂感多集中于“国民性”的批判,言论也多以中国历史、文化和一般社会现象为批判对象,涉及时人时事的并不多。与陈西滢交战后,杂文中的“私怨”成分明显增加,而这“私怨”,又常常是为“公仇”而发,并归结为“公仇”,使鲁迅杂文更显战斗的“火气”,且不失深广的主题。鲁迅终其一生都未能对陈西滢稍加原谅,这与他同梁实秋、林语堂甚至高长虹之间的恩怨都有所不同。这些针对具体人物和事件展开的论战,不因具体的是非而流于文人之间简单的好恶之争,这是鲁迅的高明之处,也是鲁迅论战文章不可效仿的地方。研究鲁陈之间的笔战,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运动史,研究和理解鲁迅的笔战风格和他的“韧性的战斗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以为“鲁迅与陈西滢”这个研究专题是可以成立的。本书试图专注于鲁陈之间论战始末的分析,将笔触深入到双方论战的最细部,进行文化的、文学的、政治现实的分析与研究。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陈西滢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他作为文学家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著述,《西滢闲话》是他一生最主要的作品集;作为学者,他主要是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难以称得上是成果显著的专家;作为文化运动中的人物,他参与创办《现代评论》杂志,主要在初期负责编辑文艺稿件。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陈西滢都算不得多么突显的人物,然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陈西滢却是鲁迅笔下最突出的论争对手,一九二五年一年间,鲁迅的大多数杂文都与陈西滢相关,《华盖集》及其《续编》,是这场论战的集中体现。而一九二五年这一年,在鲁迅的一生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一年鲁迅的社会活动、文学创作、个人生活,都有很多令人玩味之处。一九二五年一年的风风雨雨,对鲁迅一生都有着深刻影响,陈西滢在这样的时候出现在鲁迅的视野里,自然成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鲁迅时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这也是我之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目,切入鲁迅世界的出发点。在进入对两人的论争分析之前,有必要对人们相对知之较少的陈西滢,他的生平经历、创作活动做一个简单的交代,也有必要将鲁迅在一九二五年的主要活动和创作情形,做一点具体的描述,以使以后的论述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背景。
陈西滢何许人也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生,江苏无锡人。幼年入上海文明书局附设的文明小学就读,后转学到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属小学。一九一一年毕业,升入中院。十六岁时,受其表舅吴敬恒鼓励,赴英国留学,从中学读到大学。在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与文学,并苦学英文,打下了深厚的英国文学功底。在伦敦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期间,受到名师拉斯基的指导,并获博士学位。一九二二年二十六岁时,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即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后联合好友王世杰、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杨振声等创办《现代评论》杂志。编辑过其中第一、二卷的文艺稿件。围绕该刊及《新月》杂志,与胡适、徐志摩等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
一九二四年泰戈尔来华,徐志摩接待并任翻译,陈西滢参与了接待工作。女作家凌叔华时为燕京大学学生,也参与其中,陈西滢因此与凌叔华结识。一九二七年,与凌叔华结婚。这年夏天,两人以北京大学研究院驻外撰述员身份到日本旅行。一九二九年五月,王世杰出任武汉大学校长,聘请陈西滢为教授并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因抗战爆发,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陈西滢随校前往。王世杰当时信心十足,决心要把武汉大学办成同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等并列的世界名校。陈西滢也十分投入,除行政任务外,还开设了“短篇小说”“英国文化”“翻译”“世界名著”等课程。一九四三年赴英,在中英文化协会任职,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由于巴黎物价昂贵,不久即迁往伦敦居住。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国际地位受到威胁,加上台湾政府经费紧张,连年积欠会费,陈西滢的处境十分狼狈。一九六六年,台湾被联合国取消成员地位,陈西滢在法警干预下被迫迁出巴黎办公处。其间因抗争而心脏病突发,当场昏厥,被送往医院急救。同年,以国民党政府外派文化官员身份退休,定居伦敦。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因脑溢血客死于伦敦,享年七十四岁。在担任教科文组织职务期间,他曾帮助台湾地区文人恢复了跟国际笔会的关系,一九五九年,同罗家伦、陈纪滢、曾恩波等出席了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笔会。
陈西滢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并集中发表于《现代评论》《新月》等刊,他翻译过梅立克、曼殊菲儿的作品。一九二八年六月,新月书店出版《西滢闲话》,一九七〇年,台湾萌芽出版社出版了《西滢后话》。
陈西滢的一生,经历复杂曲折,文学活动在他一生中所占比例并不很大,正是由于同鲁迅的论争,才使他的文名在当时远扬,直到今天仍为研究者所关注。
一九二五年的鲁迅
一九二五年,鲁迅四十四岁。这一年对鲁迅的一生来说,都显得十分重要又十分特别。无论从社会活动还是创作经历,抑或是个人情感经历而言,一九二五年都是鲁迅一生中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第一天,鲁迅写下了散文诗《希望》,并在这一年里完成了《野草》的写作,这是一部记录作家心灵轨迹的重要著作,也是鲁迅艺术探索途中的经典作品。
一九二五年的鲁迅,继续他的小说创作,《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离婚》等都创作于这一年。他的杂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在这一年结集出版,杂文创作也呈现出短兵相接的特点。
一九二五年对鲁迅来说是多事之秋,“女师大风潮”中,他因公开支持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于八月遭到教育部长章士钊的“革职”,为了讨还公道,他迅速向北洋政府平政院递交了诉状,控告章士钊并在次年一月得到复职,回到教育部任佥事职务。也由于“女师大风潮”,鲁迅与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文人学者展开笔战,充分展示了鲁迅韧性的战斗精神,杂文笔法更显锋芒,确立了杂文文体参与现实的品格和论战的风格。《华盖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就写作于这一年。
这一年的鲁迅,肺病复发,这对他以后的生命历程有着潜在的影响。而对鲁迅人生命运发生根本影响的,还是他在这一年结识了许广平,许当时为女师大的进步学生,曾因参与“驱羊”(杨荫榆)运动而受到校长杨荫榆的开除处分。鲁迅不遗余力地为许广平等六名学生伸张正义,许广平则从这一年开始,频频去鲁迅寓所探访,两人从此建立了通信联系。一九二五年是《两地书》的第一个年头。
一九二五年的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认识更多地与现实结合,《野草》是一个思想者和一位艺术家积郁在灵魂深处的“地火”的喷发,《伤逝》《离婚》等小说在艺术上更臻“圆熟”,结尾却少了《呐喊》时期的“亮色”。这一年,鲁迅结交了笔战的对手,与陈西滢、徐志摩等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文人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论战。身兼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数校教职的鲁迅,还必须应对来自教育部“上司”的威吓和“手脚”。带着肺病的他,又在这样的心力交瘁中寻找到了生命的亮点:许广平。
一九二五年的鲁迅,在年初的二月,因《青年必读书》这篇不足千字的文字,成为文坛上的议论中心,守旧者的反对之声并不是最可怕的,许多青年对他“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言论的误解,才真正让他产生内心深处的悲凉。
一九二五年的鲁迅,还继续翻译厨川白村的作品,《出了象牙之塔》就在这一年年底完成。这一年,他还与韦素园、李霁野等组成“未名社”,出版《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书”。
无论站在何种角度看,一九二五年的鲁迅,都显得那样意味深长,鲁迅的思想、情绪、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都在这一年浓缩,生发出许多让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鲁迅传记我们已经见到过许多种,并还在继续增加,而我以为,把一九二五年的鲁迅抽取出来,在显微镜下一点点放大,那会得到多少“线性”描述难以发现的内涵和深度,这样一种描述,对读者了解鲁迅精神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对陈西滢其人有了一个大概了解,又重温了一九二五年这关键的一年中鲁迅的主要活动和生活处境后,再来确立“鲁迅与陈西滢”这一话题,就显得相对容易一些,我的着眼点,就是从一九二五年出发,以鲁迅和陈西滢为视角,描述和分析鲁陈之间的纷争恩怨,并从中探讨这场论战生发出来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文学观念的诸多意义,努力为切实、深入地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杂文的创作特点,提供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