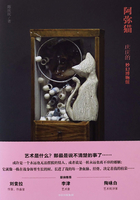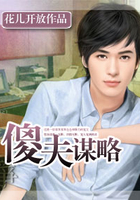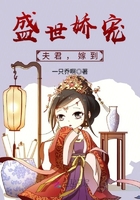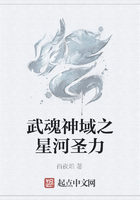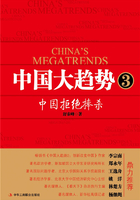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新年的第一天,鲁迅在北京家中写下了一个充满亮色的标题:希望。但在这样一个充满乐观向上的题目下,鲁迅为我们描述的却是一种悲凉的心境。这简直是《野草》里色调最灰暗的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心分外地寂寞。”而这寂寞的内涵,是因为内心里“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在这新年到来的一刻,鲁迅想到自己“大概老了”,不但“头发已经花白”,“手颤抖着”,而且怀疑自己“灵魂的手也颤抖着……”然而鲁迅最感到寂寞的原因,还在于他突然觉得,“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鲁迅在《英文译本序》中说道:“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正因为有感于青年的消沉,所以才使他感到一种绝对的“虚妄”。鲁迅的心境,在这新的一年到来之际,竟至于如此绝望,如此空虚。
在紧接着的二月十日,因为要应答《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作《青年必读书》。这是一种填表式的写作,在“青年必读书”和“附注”栏内,鲁迅写下了寥寥数语,以为回答,却不想因此卷入一场论争中,鲁迅从中看到的,正是《希望》中所写到的可悲现实。一九二五年一月,《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书目。鲁迅应编辑请求,对“青年必读书”作了应答。在“青年必读书”一栏内,鲁迅没有按要求写下一部书目,而是以“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作答。麻烦出在“附注”栏内的文字,鲁迅发表了自己对读中国书和外国书的截然相反的态度。主要内容是: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是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鲁迅的这篇应答在二月二十一日的《京报副刊》发表后,立刻引起一片哗然。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熊以谦的《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赵雪阳的《青年必读书》中引用某学者的话,都是对鲁迅应答内容的疑问甚至反驳。这些人或者把鲁迅的回答视为“偏见”,或者将其视为“武断”,而暗里的含义,还有指责鲁迅有“卖国”倾向,误导青年“不学无术”等等。鲁迅在《聊答“……”》《报(奇哉所谓……)》及《这是这么一个意思》等文章中做了毫无保留的回应。鲁迅从开始就没有打算以导师的资格来指点青年,以他当时对中国青年的认识,所谓“必读书”之类的指点,并没有什么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虽然主张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但他连外国书也没有开出一本,这正是基于他重在“行”而非“言”的立论基础。
在经过这样一场论争之后,鲁迅感受到的并不是战斗的兴奋和胜利的喜悦,而是一种莫名的无聊。顽固派的守旧和诬蔑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青年中有对鲁迅误解和不以为然者。鲁迅的文章发表后,还有署名“瞎嘴”者给鲁迅去信,攻击鲁迅道:“我诚恳希望:一、鲁迅先生是感觉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所以敢请你出来作我们一般可怜的青年的领袖先搬到外国(连家眷)去,然后我们要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二、鲁迅先生搬家到外国后,我们大家都应马上搬去。”(转引自《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其言辞之刻薄与恶毒可见一斑。可以说,《青年必读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风波,让鲁迅验证了自己在新年第一天里感受到的气氛。
除此之外,鲁迅在这一时期的杂文,还在继续着《热风》中的主题,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一句话,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还在进行着。《忽然想到》《战士与苍蝇》《夏三虫》等文章,都是愤世嫉俗的文字。尽管《战士与苍蝇》里对孙中山等革命者的称赞和对“奴才”式的小人的不屑,被熊以谦之流看作是对文坛是非的影射,但鲁迅的目光和深度,的确在那一时期为许多人所不解、误解、曲解。鲁迅的寂寞可想而知。
在这一时期,鲁迅还在任教育部佥事职,并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职。让鲁迅不曾料想到的,是在文章引出攻击,不得不一一反驳之外,又因为他的社会活动而引来一连串的麻烦。陈西滢就在这样的时刻闯入鲁迅的视野,从此,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成了鲁迅笔下或直接或间接地纠缠在一起的人物。
那时,陈西滢正以北京大学“陈源教授”的身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运动中的一员。鲁迅和陈西滢“交手”的起因,是在一九二五年成为中国文化史重要事件之一的“女师大风潮”。鲁陈之间交战的方式,是文人们最常用的打笔墨官司。
“女师大风潮”的始末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前身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创办于一九〇九年,一九一二年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一九年改名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二二年七月,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被任命为校长,在此之前,校长一职更换过十次之多。许上任后,对校务及教学事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订定本校组织大纲,改革本校全部行政系统,并从新厘定课程,由是评议会成立,周刊出版,各种行政委员会亦次序设立。”(见《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第27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期间还酝酿改办“女子大学”事宜。就在这一切正在顺利进行,学校发展方兴未艾之际,教育部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任命杨荫榆为校长,而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宣布成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从此,这所中国女子大学中的最高学府进入了一个极不平静的动荡时期。
杨荫榆,江苏无锡人,一九二〇年,以学监主任的身份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后不久即掌校长之权。她上任后的所作所为,逐渐引起学校学生的不满,在女师大,“驱羊”运动成为一个重要主题,风波不断。几乎所有我们看到的资料,对杨荫榆的态度都是众口一词的不满和愤怒。作为女师大的学生,许广平称她为“一个劳什子的杨荫榆”,并这样描述她的言行举止:“她整天的披起钟式斗篷,从大清早出门四处奔走,不知干出什么事体以外,回到学校,不是干涉一下子今天用几多煤,明天撤换什么教员,一屁股往卧室一躺,自然有一大群丫头、寡妇,名为什么校中职员的,实则女仆之不如,然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有时连食带闹,终宵达旦,一到和各主任教员周旋,和学生接谈,都是言语支离,问东答西,不得要领的胡涂虫,学生迫得没法,由各班推举代表去见她,要求她自行辞职。……”(许广平《校潮参与中我的经历》)而女师大的学生在驱逐杨荫榆的《宣言》中,多次列数杨的劣迹,其中对她学术浅薄也不乏描述:“彼漫游美国时,不过为哥伦比亚之一英文补习生。求学工具,尚未具备,遑云研究。”(《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第309页)此外如批评她“不谙礼节坠落校誉”“援引私人排斥异己”“敷衍校务遗误青年”等等,都可看出杨荫榆在学生心目中地位之低。
杨荫榆上任以后的种种行为引起了女师大学生的不满,这所当时仅有两百名学生的大学掀起了一股反对杨荫榆的浪潮。一九二五年一月,女师大学生赴教育部请求撤换校长。杨荫榆恼羞成怒,声称:“此校为我终老之所,我无儿无女,岂能他去乎?”一九二五年四月,教育总长章士钊声言要“整顿学风”,女师大学生与章士钊、杨荫榆等人的矛盾激化。五月七日,正逢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最后通牒,要求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杨荫榆借机搞了一次演讲会,请校内外名人来校演讲。一方面她本人仍以校长名义出席,以示权威;另一方面则安排亲信,如果学生有反对行为,就以破坏演讲会为名加以惩罚。演讲开始前,学生们高声呐喊,要求她退场。杨荫榆在计谋不能得逞之后,以秩序混乱为名中止演讲会。这天下午,杨荫榆在西安饭店宴请若干教员,并形成开除六名学生自治会成员的决议。这份名单上,有被学生公推为自治会成员的许广平和刘和珍。五月九日,决定一经公布,立刻在校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驱羊”之声更加猛烈。
杨荫榆孤注一掷的行为只能引起学生们更加激烈的反对,一九二五年五月,原定的校春季运动会无法按期举行,杨荫榆因为学生阻拦她以校长身份出席运动会,于是强令取消。她的这一系列行为举动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五月十一日,学生代表要求杨荫榆当面呈情,不料她却躲逃而去,其狼狈之状可见一斑。
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杨荫榆开始向学生动手。此前,七月二十九日早晨,校内突然贴出公告,借口修理校舍,迫令全体学生搬出学校,并于三十日晚再次贴出公告,下令取消学生自治会。八月一日一大早,女师大校内布满军警,杨荫榆指挥军警,大打出手,驱赶学生,学校一时交通阻断,伙食停止,电话不通。社会各界对杨荫榆的行为公开指责,无奈之下,军警才退出学校。教育总长章士钊不顾学生意愿,于八月七日下令解散女子师范大学,而学生依然不予理睬。八月二十二日中午过后,章士钊的部下、教育部专门司司长刘百昭带领数百名军警包围学校,并雇用一批被学生称为“流氓老妈子”的人物,强行拖拉、绑缚学生出校。
女师大学生和杨荫榆及章士钊等人的斗争到这时可以说发展到了惨烈的程度,她们一方面向章士钊兴讼,试图以法律手段取得胜利,并向全社会寻求声援;另一方面另觅校地,继续学业。九月一日,反对杨荫榆的学生迁往西城宗帽胡同,在那里租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九月二十一日开学,鲁迅及其他部分教师前往义务授课,以此支持学生。
直到这一年十一月,女师大学生才全部迁回到原来的校址石附马大街,正式复校。学生们拆毁了章士钊书写的校匾,尽管仍然受到当局骚扰,但秩序逐渐缓和。一九二六年一月,原来的校评议会主席易培基被任命为校长,一月十三日,校务维持会欢迎易培基就职。鲁迅以校务维持会名义发表了欢迎演说。而这一天正是女师大学生“发表反杨宣言的周年”纪念日(《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第371页)。
经过这一年的风风雨雨,女师大成为当时北京及全国各界关注的焦点。这场斗争中,“校务”是非占了事件进程的大半成分,且大多针对杨荫榆、章士钊等人,历来学术界对这场斗争本身的研究与意义的挖掘并不充分。事实上,“女师大风潮”发生在“五四”高潮刚过的一九二五年,又发生在现代中国年轻的知识女性中间,其中表现出的强烈的个性自由的要求,民主意识的自觉,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顽强抗衡,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些意义,正好通过鲁迅与陈西滢等人的论争而片段式地保留了下来。鲁迅有关“女师大风潮”的言论,同时期中国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对事件的议论,尤其是鲁迅与其论敌间的论战,为这场“风潮”增添了一幅特别的风景。
“风潮”刚过不久,一场更为惊人的悲剧发生在女师大学生身上。一九二六年三月,由于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北京各界爱国群众集会于天安门广场,并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然而段祺瑞执政府竟然下令卫队开枪射击,用大刀铁棍追打请愿群众,当场及事后因伤而死者达四十七人之多。女师大进步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在惨案中丧生。事件使鲁迅等文化界人士深感震惊,鲁迅就此写下充满悲愤之情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都为此写了文章,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陈西滢也曾对“三一八”惨案发表过议论,由此,他与鲁迅等人立场的对立达到极致,且完全不能以个人恩怨来解释这种立场分歧。
可以说,发生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内外的一系列事件,就像一场强劲的风暴,又像一块试金石,对当时的文化名人、作家学者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鲁迅在这一年陷入笔战的漩涡,并将杂文创作更多地转向现实的批判,与发生在他周围的这些不平静的事件,有着内在的关联。我们大致勾勒出“女师大风潮”的过程,就是为了加深对鲁迅与陈西滢等文化界人士论争的理解,并增强我们对这场论战思想和文化意义的认识。也将有助于理解鲁迅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内涵。
“女师大风潮”中鲁迅的行踪与是非纠缠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始终站在同情和支持学生的一边,但初期时他只是一名旁观者,并没有在行为上投入学生运动中。随着事件的发展和情况的日益严重,鲁迅也逐渐地进入到风潮的漩涡中来。就女师大校内来说,鲁迅多次以不同方式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他不但坚持带病到宗帽胡同为因反对杨荫榆而迁到那里的学生上课,而且还在校务维持会里负责教务工作。一九二五年五月,鲁迅执笔,以国文系数名教师的名义撰写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其中明显表露了鲁迅等教师代表对女师大学生与校长间纷争的立场,尤其对杨荫榆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六名学生自治会成员的行为,给予了公开谴责,“宣言”全文如下:
溯本校不安之状,盖已半载有余,时有隐显,以至现在,其间亦未见学校当局有所反省,竭诚处理,使之消弭,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教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部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文预科四人理预科一人国文系一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校长之事变,而杨先生亦遂遍送感言,又驰书学生家属,其文甚繁,第观其已经公表者,则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使不谙此事始末者见之,一若此次风潮,为校长整饬风纪之所致,然品性学业,皆有可征,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遂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同人忝为教员,因知大概,义难默尔,敢布区区,惟关心教育者察焉。
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
这份《宣言》公开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它对“女师大风潮”的是非曲直产生过相当强烈的影响。鲁迅公开参与女师大校务并表明自己对风潮立场的文字记录,还有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女师大复校,校务维持会主席易培基出任校长的欢迎会上,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所致的欢迎词。从这份演讲词中不难看出,鲁迅对杨荫榆的不满,以及对学生反杨行为始终支持的立场。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鲁迅的欢迎词全文:
今天原定总务主任马幼渔先生代表了本会,来致欢迎词的,可惜马先生忽然病了,所以又由树人代替了马先生来说几句话:欢迎校长,原是极平常的事,但是,以校务维持会欢迎校长,却是不常有的。回忆本校被非法解散以来,在外有教育维持会,在内,有校务维持会,共同维持者,计有半年。其间仍然开学,上课,以至恢复校址。本会一面维持,一面也无时不忘记恢复,并且希望有新校长到校,得以将这重大的责任交出。现在政府居然明令恢复,而且依了大家的公意,任命本校的教育维持会正主席易先生为校长了。易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所钦佩的。当恢复之初,即曾公推为校长,而易先生过于谦退,没有就,但维持仍然不遗余力。同人又二次敦请,且用公文请政府任命,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同人认为自己的责任已尽,将来的希望也有所归属,这是非常之欢喜的。从此本会就告了一个结束,自行解散。但是这解散,和去年本校的解散很不同,乃是本校更进于光明的路的开始,为什么呢?先经说过,因为易先生是本校全体所希望的校长,而这希望的达到,也几乎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到的创举。所以今天的盛会,实在不是单用平常的欢迎的意思所能表现的。憾自己不善于言语,就只能将以上的一点话,作为欢迎词。
鲁迅的演讲中,除了对易培基出任女师大校长一职表示欢迎和支持外,也表达了他对女师大一年来风风雨雨的态度。事实上,鲁迅已经认识到,“女师大风潮”尽管事件本身在学校内部,而它的胜利与否却与中国大学希望所在密切相关。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场艰难而曲折的“驱羊”运动,迎来了自己希望的校长,这是她们的胜利,而鲁迅同时指出,“这希望的达到,也几乎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到的创举。”这从一个方面,提升了“女师大风潮”的意义,这层意义在当时还是很少有人意识到的。
鲁迅因女师大而带来生活上的很大变化。因为在女师大任教,所以有幸结识了进步学生许广平,并从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因为支持女师大学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革职,鲁迅为此还打了一场官司。可以说在动荡的一九二五年,尽管鲁迅有教育部的职位,并同时在三四所学校任教,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从一九一二年三月到一九二六年八月的十四年间,鲁迅一直在教育部任职。一九二五年八月,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在女师大校址石附马大街成立中国女子大学,就在章的命令下发当日,即八月十日,女师大部分教师成立了校务维持会,鲁迅被推举为委员。当时的社会气氛实在可以说是互不相让。在此之前的五月,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日的爱国活动,在学生的反对浪潮中逃往天津。在他重返教育部之后不久,就又做出了激怒学生的极端行为。鲁迅身为教育部职员,在学生运动中,始终站在反对章士钊、杨荫榆,支持学生运动的立场上。章士钊在鲁迅出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成员一职后,立刻决定罢免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职务。这对鲁迅来说失去的虽只是教育部的俸薪和一点“区区”小职,但他为了坚持正义立场,于八月二十二日向平政院递交了诉状,起诉章士钊。这一诉讼行为直到一九二六年一月方有结果。在一月十三日易培基出任女师大校长,校务维持会解散后,鲁迅也获得胜诉,并于一月十七日恢复了在教育部的职务。
鲁迅从来就没有陶醉于教育部的职位,他对章士钊等军阀政府中的官僚,有着清醒的认识,从不因顾及“上司”的脸色而改变自己的社会活动。在写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的《答KS君》一文中,鲁迅这样谈论自己对章士钊的看法和评价:“章士钊将我免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智识阶级的领袖来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发生不平,其实是作茧自缚;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这是鲁迅对章士钊的基本评价。在“女师大风潮”问题上,章士钊与鲁迅的立场相反,直接透露出他们对社会时事的态度与看法。身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对女师大进步学生进行了污蔑,其中有“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从而推波……”等语。鲁迅敢于与其“顶头上司”公开作对,表明了他对“女师大风潮”的立场,也显见出他的战斗性格。
一九二五年,对鲁迅影响至深的另一件事,是他结识了女师大国文系学生、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五日,鲁迅请许广平等数名学生到家做客吃饭,鲁迅的心情因许广平的出现而显出亮色。可以说,在女师大任教和发生在这所学校里的一切是非风云,对鲁迅来说,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从“风潮”的旁观者到公开支持者,因“风潮”中的立场和行为而招致恶势力的报复和打击,在这样的环境中却寻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一九二五年和女师大,对鲁迅而言,意义十分特别,十分复杂。更不用说,他从此还遭遇到了一个接一个的论敌,也正是从这时开始,鲁迅的笔墨官司就没完没了地打了下去。
陈西滢:何以卷入“风潮”
在鲁迅已经观望并逐渐卷入“女师大风潮”的时候,陈西滢事实上还只是北京大学的“陈源教授”。一九二四年,他同一批曾经留学欧美、同时也是北京大学教授的文人学者们共同创办了一份刊物:《现代评论》。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们通过这份刊物而全面介入到了中国文化界当中,陈源以“西滢”为笔名撰写的《闲话》系列,就全部出自《现代评论》,也因为这些文章,陈西滢成为鲁迅的主要论敌之一。
陈西滢对发生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自然不可能不关心,他在“闲话”里的议论待后面详细剖析。除文章之外,陈西滢也与“女师大风潮”有程度不同的关联。当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后,北京大学评议会立刻召集会议,决议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宣布独立,以此表明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和对教育当局的不满。但以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现代评论派”为主的部分教师,却坚决反对这一决定,理由是北京大学“应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在教务会议和评议会联席会议上,他们以“退席”等方式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女师大复校刚过,校内又起一番风波之后,陈西滢等三十二人联名起草了“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信中对女师大学生的行为颇多指责,并对鲁迅等教员对学生的支持不无污蔑,此信的内容如下:
敬启者: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拦入校内,强力霸占,
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一完善整饬之女子高等学府,无端遽被摧毁,学生三百数十人,弦诵顿辍。其事不惟大违法律,抑且轶出政治常轨,贻教育界以莫大之耻辱。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等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否则群乘政变,自由仇复,弱肉强食,相率而为,败法乱纪,北京学校将从此多事,教育非全陷破产不止。是于本月十四日,公议组织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冀以群策群力,共扶正义,而戢凶焰。贵联席会为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之代表机关,对于少数人此种暴行,疾恶仗义,宁复后人,应请发摅谠议,力持公道,为舆论之制裁,褫暴徒之胆魄,对于此次女师大非法之恢复,决不能迁就事实,予以正式之承认,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为社会存是非,即为教育界清乱源,谨布腹心,伏维公鉴。
这封信由陈西滢(署名陈源)等三十二人共同署名,并自称“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京报》。陈源与鲁迅在女师大问题上态度的相反,已到了相互敌对的程度。同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也发表了“致教育界维持公理会书”,“陈源”的名字列于其中,信中对这些人不分是非,居然为章士钊等人撑腰打气表示失望和不满,并期望他们在得知女师大实情之后,能够“内愧于心”,并做出“改头换面之举”。陈西滢与鲁迅的对立,即使在文章之外,也是昭然若揭。有了这样的背景交代,我们梳理和理解鲁陈之间的纷争,就获得了一个可靠的现实背景。无论鲁迅与陈西滢之间在论战过程中引发出多少主题,但我们仍然可以说,“女师大风潮”是这场论争的最原初的导火线和最大主题。
“三一八惨案”:截然的立场分界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可以说是当时北京乃至全国瞩目的是非之地,不但学生运动事件不断,更主要的是引来了当时中国文化界许多著名人物的参与和议论,由此生发出许多话题。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群众集会天安门,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的无理要求和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本来,群众集会的目的是“反抗各国通牒,做政府之后盾”,
(《女师大教职员宣言》,《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第
391页)谁也没有想到,当万余名群众集会后赶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时,却遇到执政府卫队士兵的开枪射击,死亡人数达四十七人之多,伤者更逾百余人。这可以说是一次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合谋屠杀中国人民的大惨案。惨案发生后,立刻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女师大的两名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也在被屠杀者当中,她们都是国文系的学生,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都是她们的老师。消息传来,立刻在北京文化教育界引起强烈震动。事发当日,鲁迅就难忍心头之痛恨,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这篇札记式的文章也许不是在同一种心境下写成的,前三节还在议论陈西滢的《现代评论》和章士钊的《甲寅》,从第四节开始,就意识到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大杀戮了。”鲁迅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在文章的末尾署上时间的同时,鲁迅还特别注明,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在鲁迅的文章中是极少见的情形。在紧接着的一周时间内,鲁迅又写下了《“死地”》和《可惨与可笑》,除了对执政府的暴行表示愤慨外,还对某些报刊发表污蔑被害学生的言论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惨案发生后,《晨报》就曾发表过数篇文章,对群众的抗议行为进行公开污蔑,说这些青年都是出于意气,铤而走险;甚至说是“共产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鲁迅针对这些言论针锋相对地指出:“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引起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死地”》)这些言论事实上是对“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身心的双重屠杀,是鲁迅最不能容忍的。
对于死难的学生,鲁迅深怀同情与钦佩,《记念刘和珍君》这篇被许寿裳喻为“伟大的抒情文”的回肠荡气之作,就是鲁迅表达对死难者的怀念与敬佩之情的作品。刘和珍曾是鲁迅的学生,又和许广平一起同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成员,曾同许广平一起被杨荫榆划入被开除学生的行列。鲁迅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
周作人、林语堂等许多文化名人都对此事件发表了看法,周、林二人的文章同样表达了自己对死难者的追思和怀念,对军阀暴行的抨击。陈西滢也用文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但他的论调却是另外一种味道。这篇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上的“闲话”文章,总体上与《晨报》上的那些社论和文章的观点十分接近,即认为学生死于冲动,死于受人利用。更有甚者,陈西滢直接说道,杨德群在集会时本来就不想参加,平时也不爱参与社会活动,完全是被别人拉去,半路要返回,又被某教员强留下进而赴死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来女师大师生的不满。有雷瑜等五位女学生联名致公开信给陈西滢,对他的一系列说法进行驳斥与“辩诬”。杨德群平时就是“大有作为”的“革命女青年”,三月十八日也是她自愿同同学们一起出校的,完全是“爱国心驱使”的结果,她们要求陈西滢“履行更正之责,速为披露,以明真相”。(《致现代评论记者》,《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
陈西滢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公开表态,何况学生的信件已在同一天的《京报副刊》上发表。陈西滢在发表信件前的“按语”中承认,关于“杨德群女士事件”,学生们的说法是“可靠”的。但他同时认为,所谓青年,不一定非得要上街游行参加运动才是“大有作为”的,因为“许多‘富有思想’‘大有作为’的青年是简直不参与任何运动的”。他也为自己辩解说,他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就是试图为执政府“减轻罪恶”。陈西滢还迂回地说了一段别有意味的话:
可是雷女士们的思想也并不为奇。他们比较有些的人已经和缓得多了。因为那“杨女士不大愿意去”一
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卫队还大!比军阀还凶!(读者如果没有读过我那段惊天动地的闲话,赶快翻出来细细地鉴赏一下罢)不错,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难道四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现代评论》第三卷第70期)
陈西滢的这一段话,立刻成了他从暗里射向鲁迅的一支“冷箭”。鲁迅曾在《可惨与可笑》一文中,借用“流言”“啸聚”“优美的差缺”等陈西滢的言论,将他对“三一八惨案”的言论划入到与执政府同流合污之中。《记念刘和珍君》中,更将段祺瑞执政府的残暴与阴险文人的嘴脸作为抨击的对象。“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在《空谈》一文中,鲁迅更直接引用“陈源教授”的那篇高论中的观点,即劝告中国“女志士们”或“未成年的男女孩童”,“以后要少加入群众运动。”鲁迅也表达了对无辜死者的哀伤,认为“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但他既面对这样的惨案,就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并努力寻找死难者的死对后来人的意义。“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可以说,鲁迅同陈西滢的争论发展到此刻,通过“三一八惨案”就画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一件如此严重的、残酷的现实事件,两人的态度如此不同,鲁迅与陈西滢的争论已经不能说是文人之间的“相骂”,话题也远远超出了文学、文化和具体的是非。他们明显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阵营。陈西滢即使没有完全滑向与执政府蝇营狗苟的地步,但他的言论已经比胡适的《爱国运动与求学》更显不合时代潮流,加之他对女师大、对鲁迅的成见,他的观点已经暴露出错误甚至反动的一面。并且从此事件之后,鲁迅由于受到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不得不离开北京,前往厦门大学任教。他与陈西滢之间的论争也就这样在不可调和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