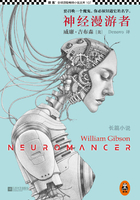“贴左边是很深的山涧,右边是塘。那个岭特别陡,走刘家铺过的人都晓得。”父亲后来对村子里的人叙说着。
“车子既没有后刹又没有前刹,幸亏我在路上将龙头上紧了,将前刹修了一下。那岭真陡!我一跨上就止不住了。还好,我这时非常清醒,先将小娃子颠了下来,然后一扳龙头向山上撞去。我一下子摔倒后,就什么也不晓得了。”
“嘴唇绽开了吗?”
“从这上面内外全部绽开了。”父亲将头稍仰,用手指着给别人看。嘴唇早已愈合,留下缝的针脚和疤痕。
“哎哟!好危险喽!”
“小三鬼差点把他爸命都送掉了!”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当和村子里妇女们谈话时都这样叙述道,“幸亏后面有两个男劳力,一个是做粉丝的,一个是做篾匠,是当地人,认得他,把他扶起来……他仍然坚持走到医院,在医院里缝了七针!”
“牙齿掉了两颗?”
“掉了两颗门牙,在这儿呢,一边一个。”母亲在自己的嘴上比画着。
“是的。小姐夫进村的时候,我看他戴着个大口罩,头上戴着个猴头似的帽子,就感到奇怪。小三鬼由另一人背着,一点也不作声。那个人是谁呀?”
“是公社里的,公社派人送的。真吓人呢!我一看到他们从田畈里走来,就知道不好,心就往下一沉……”母亲心有余悸地说。
“我知道后,身上直打战。现在好了,破一次灾星,以后就好了。”
“小姐,我看小姐夫是命大福大造化大。他命硬!”
“嗯……。”
我和父亲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父亲叫人通知了公社里。家里一点也不知道。
当回到公社,父亲向他们叙述自身经历时候,那个长得很漂亮的阿姨,洁白的脸上现出一副惊讶的面容,眉头紧锁着,不时发出“哎呀”的声音,两只小虎牙不时地闪出来。一个长得胖胖的、白白的,穿着灰色中山服,比爸爸显得稍小一点的叔叔用那样“咝咝”的不是本地的声音说着惊讶的话,“木会计、木会计”地不时地喊着,他是公社的秘书。
一个月后,我和父亲在公社派人护送下回到家。家里人和周围知道的人都惊呆了。
外婆从自己家里急匆匆地赶来,她穿着黑色斜襟土布褂。
屋子里围了很多人,孩子们在大人中间来回地窜着,他们仰着头,望着大人们的脸,听他们讲话,隐隐约约地知道一些,但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外公将孩子们赶出去,嫌他们讨厌。
母亲惊恐着,将戴着口罩(口罩下面的边缘被伤口上涂的黄药水染黄了)、猴头似的帽子的父亲迎回家,其他人也一齐帮忙,将父亲安置在堂屋的大椅上坐下。母亲站立着,将手臂弯起遮着眼睛和脸,嘴里泣不成声地说着:
“这是怎么搞的?这是怎么搞的呢?”
护送我们回来的人叙述着事情的经过,其他人围着他,杂七杂八地问这问那。那人说完后,便动身走了。家人客气地挽留一下,可他还是离去了。
不久,父亲被扶到东面的床上躺下。东面是父母亲的房间。
村里人陆续走了,临出门时都回头劝我母亲别难过。大哥先大声地哭着,靠在墙壁上,用手臂擦着泪水,然后跑到锅底下架柴烧锅,显得十分懂事的样子。二哥也吓得大哭,在别人的吓唬和指引下,抱着两岁的五妹,牵着五岁的四弟出门躲到别处去了。
母亲和外婆守在床前,二舅母到锅间烧饭,二母舅也来了。外公坐在外面堂屋的大椅上皱着眉,不时地叹着气。
不久,母亲又带我到碧波湖医院找本草老神医看病。
碧波湖医院坐落在碧波湖区区公所。区公所这里有一条老街,称橡林老街。碧波湖区区公所距我家近30里,在我家的正东方,中间经过父亲的老家木家庄。
母亲是和大姨一道带我走的。大姨是外公的第一个孩子,1937年出生,比母亲大三岁。在母亲和大姨之间本来还有一男孩子,不幸在刚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大姨名叫左忠芳,属“忠”字辈。大姨在刚解放时上过三年学,读完初小,这在那个年代,在农村,又是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受到这样的教育,是十分少见的。上完初小,大姨便以童养媳的身份出嫁到本乡牛岭村大树庄(1958年牛岭村改为光辉大队)。这是一个小村庄,只有十户人家,坐落在一座山脚下,在我们村庄的正东面,与我们村庄中间只隔一座小山冈,相距有四百余米。大姨是老亲开亲,大姨夫是外婆的亲侄子。外婆姓柳,与柳庄的柳姓是一家,外婆的祖父是从柳庄搬迁到那里的,因此大树庄都是柳姓,都共一个老太太。
到大姨家是我们孩子们最快乐的事。每当我们跟随母亲翻过山岗,远远地,大姨村庄里的人便发现了,他们走出家门手搭凉棚仔细观望着,也早有人飞也似的去通知大姨家了。当我们从东面的村口跨过石坎,进入村庄(那时各个村庄因防畜禽到田畈糟蹋庄稼,村庄周围都围有大半人高的石坎子),家家户户都有人在门口迎接我们、与我们打招呼。他们露出真诚的笑脸,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坐。全村的孩子都一窝蜂地簇拥在我们周围。我们既是大姨的亲戚,也就是他们的亲戚。母亲一边打着招呼,一边笑着缓步向前走。大姨家在村庄的顶西头。
三舅爹(外婆的胞弟),一个四十余岁淳朴的庄稼汉,身穿洗得发白的粗布衣,眼里闪着善良和诚实的笑意,一边抚着我的头,一边催促着母亲到他家去坐一坐。三舅奶拉着母亲的手,说个不停。还有大舅奶、二舅奶(大姨夫的母亲)、四舅爹、四舅奶,大房的大舅爹、大舅奶等等。他们热忱地邀请着,拉着母亲的手话家常。母亲终于走到西边,而大姨也早已迎到村子的中央了。
我最喜欢吃大姨为我们下的面,特别是一种切面。在那时农村,每个村庄都做些挂面。在生产队的破磨坊里,一只被蒙着双眼的瘦小毛驴或黄牛绕着磨盘不停地转着,磨着洗净晒干的麦粒;磨坊的堂屋中放着一个大钵子,里面装着满满一钵发酵的面筋。做挂面的人将面做好后拉成长条挂在门外的挂面架上。孩子们围着挂面架偷偷地捡那些掉到地上的一两根挂面吃。挂面好吃极了,咸咸的,特别有味道。每年年底,家家户户都能分到十斤左右的挂面,供过年时吃。而切面只有公社的面粉作坊有一台机器能做,需拿小麦去换,农村的一般人家是从不舍得去换的。
大姨在面汤里很放了一些油,吃起面汤来,从嘴里直流到心里,味道鲜极了。有时还在汤里泡着炒米,那真是极大的奢侈呵!亲戚们见我们来后,都从家里送来些鸡蛋、挂面之类的让大姨煮给我们吃。
大姨因为识得字,出嫁后不久便在大队里担任妇女大队长。大姨夫原先也在公社里当通信员,1959年干部下放时,大姨夫回乡,便在大队里担任林场场长。他们有六个孩子,大孩子比大哥大一岁,我们都喊他“大姨(家)大哥”。
大姨身材中等偏上,面容和善,永远挂着一份慈祥的笑容,梳着当时农村妇女都喜欢的运动头发,身穿浅蓝色的斜襟竹布褂。大姨能说会道,待我们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母亲和大姨轮流背着我,有时也让我下来走走。我们来到龙口水库。水库坐落在两座大山之间,水库堤长约四百米,从堤库到库底有近七十米的斜坡,都是用大石块垒砌成,斜坡中间放有一层平台;水库埂的垂直高度有三十余米。远望水库埂建设得很壮观。
听大人们说,龙口水库是1959年建成的,是当地一位做大官的人想为家乡办点好事而建的,亲自过问调拨资金,还动用了劳改人员,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建成的。相传死了很多人。
水库的西面,紧贴虎头山山脚,是水库的出水口,出水口向下向正南方是涧沟,通向柳条河,通向长江。
这是秋天,枯水季节。天空瓦蓝瓦蓝的,阳光不很强烈地照在山上和原野上,库埂的斜坡上有青青的草滩和砌得很平的石块。我们从涧下通过,又斜着走上堤腰,最后才走上堤埂。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来到汪屯街上。这是一条小街,紧靠着马路,街上没有多少户人家和几间门面,是汪屯公社所在地。穿过小街,再走上一段很长的斜坡,弯上一段大弯后,便来到木家庄,父亲的老家。
老家木家庄也坐落在山脚下,地势很高,村庄很大很长,全村庄都姓木,但却分有三个房头,这可上溯到十几代之前了。我们这一房头在村庄的东边,在祖父的祖父辈建有一个大四合院,中间有天井,很气派很壮观,可是在太平天国后期,因东乡组织民团与太平军作对,“长毛”便对这一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四合院被“长毛”一把火烧掉了,后来又简易地搭盖起来。到祖父的父亲辈时,这四合院便分到各个房下,但祖先的牌位仍在正屋供奉着。
母亲和大姨在老家里吃了饭。饭是在四叔爹家吃的。四叔爹住在天井的正后面,他和我祖父共爹爹,位次是按年龄排下来的。四叔爹五十出点头,然而由于长期的劳作,脊椎已严重变形,身子向前弯曲,几乎成九十度。他身着黑土布褂,脸上皱纹一道道堆起,牙齿已落得差不多。他见到我们很高兴,用温柔的眼光看着我们,抚摸着我,用关不住风的嘴和母亲说着话。还有住在四合院东面的五叔爹,正耸起八字眉,瞪着鹰一般的眼睛,他和母亲说着话,不停地表扬着我。族中叔奶奶们“大嫂”“小红子”地喊着,抚着我的头,撩起衣服查看我背脊,发出同情的声音,并一致赞同到本草老医生处看看。母亲出嫁后曾在此住过一年多时间,跟这里的人很熟,这次见面便显得十分亲热和激动,大姨却拘谨地笑着。
下午我们继续赶路,大半下午的时候才来到大表爷家,便正式歇下来了。
大表爷是我祖母的娘家侄子,姓章,住在碧波湖区橡林公社天桥大队章屋生产队,一个离区公所只有三四华里的村前是马路、村后靠山的庄子。大表爷是天桥小学的校长。
大表爷不在家在学校里,大表婶将母亲和大姨迎进屋。大表爷家是三间瓦屋,坐北朝南,与东边的三表爷家共扇。大表婶比母亲年龄大得多,也老得多,脸上爬有很多皱纹。她用围裙打着桌边椅子上的灰尘,让大姨和母亲坐下,又将我安置在旁边的小木凳上,便下厨房烧茶饭去了。在我们农村,贵客临门,总是立即烧茶饭给客人吃,不算正餐。不久大表婶便端上糖打蛋,用勺子搅和着碗中的糖递到各人的面前。
大表爷从学校回来了。他穿着笔挺的深灰色中山装,口袋上插着两支水笔。他满脸堆着笑,皮肤从太阳穴、额头直皱向眼边。他的嘴唇很薄,像孩子般向上翘起,牙齿细密,随讲话而闭合。他打着“嘿嘿”的笑声,与母亲和大姨讲话,又不时地满脸堆笑地弯下腰,拍着我的头,夸奖我。
“小红子……老几?……老三?”
“呵!我来摸摸看。”听完母亲的叙述,大表爷表情严肃起来。他亲切地对着我,撩起我的衣服,用手轻轻地仔细地摸着我的背,眼睛和嘴巴认真地耸起。大表娘也从厨房里走出来察看。
第二天,大表爷带领着我们到碧波湖医院找本草老医生看病。本草老医生姓杨,是我们东面一带出了名的神医,什么疑难怪症只要他一看都能医治得好,人们都奉他为神医。他与大表爷的感情很好,大表爷在橡林一带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老校长,人缘极好。我们来到十分气派的掩映在人工特意栽植的树木之间的一排排高大的刷着白色粉墙的碧波湖医院,大表爷带领着我们来到本草老医生的诊室。一路上,他总是“嘿嘿”地笑着,嘴唇一翘一翘的,与任何人都很熟。“嘿嘿……”他笑着,讲着我不懂的人和事。他时常摸着我的头,不时地弯下腰,将薄薄的翘起的嘴唇送向我的耳朵与我说些悄悄话,逗我高兴,让我消除紧张和害怕。
我们在大表爷家住了几天。三表爷与大表爷相临,二表爷和四表爷的家在大表爷房子的前几排。我整天和表爷家的孩子们及村子里的小朋友们玩着,玩得十分开心。我们又在各个表爷家都吃了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