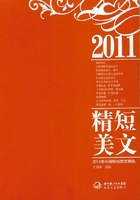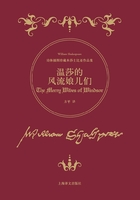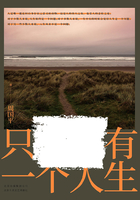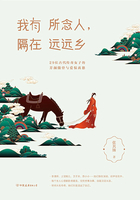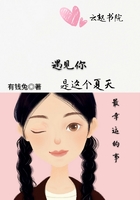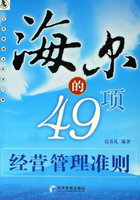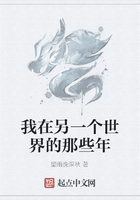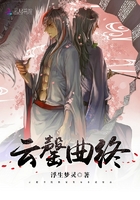第一辑 记忆的碎片
每个人心中都会留存一条小路吧?就像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一样。
我心中留存的这条路是农学院里的一条小路,当时这条路是农学院里的中心路,从北到南贯穿校园,大约有1000米长。它从前的路名叫什么不得而知,抑或就像我小舅说的——根本没看到有路名。我也无人可问。
但现在这条路的不同路段分别有三个路名。北段叫北槐路,概因路两边树高叶茂,槐树夹道。中间那段叫体育路,一看便知是源于旁边有一个十分醒目的体育场,不过这路名起得也太直白了吧?最南端的路名就更有些莫名其妙了,叫南元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这段路风景却最美。美在路边大片的绿植丰茂葱茏,美在掩映于青砖灰瓦里的那份清幽,更美在那一排排法国梧桐树的迎风摇曳。如果季节走到了深秋,那份美会来得更强烈——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成片的梧桐叶如蝴蝶的艳翅翩飞纷下。“落叶深千尺,不用带蒲团”,这是我父亲说的。
小时候,在我眼里,这条路好长好长,宽广而辽远,就像外面未知而又令人向往的大世界。
记得有一次爸爸让我去给他买一包“大红叶”香烟。五岁的我,要从农学院的北边顺着这条路走到南大门去,我怕忘了烟名,便一路走一路念叨——大红叶大红叶,没想到走到南门的商店门口,还是忘记了,沮丧的我只得又折回头硬着头皮再去问。有时回想起这段经历还很感慨,那时的治安真好啊!除了经常走这条路给爸爸买烟,我还喜欢往路边茂密树林掩盖下的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里钻,跟小伙伴们玩捉迷藏,疯累了,就自己走回家。父母根本不用担心年幼的我在路上被拐,还真有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感觉。
我童年的家就在这条路的西北侧几排靠近农学院围墙边上的平房里。平房第一排最右边就是我家,左边缓坡上连接着几栋两层青灰色的“蚕楼”。所谓蚕楼,就是过去养蚕的场所,后来不养蚕了,里面就住着一支部队,番号6408。童年的我经常跑到军营里蹦跳玩耍,若干年后我还在寻找这支部队的下落。蚕楼前面是一个操场,上面整齐地排列着十几门大炮,凛凛散着寒光。我家的右侧靠近围墙,地势较高,墙外边是大片的田野,春夏秋冬变换着不同的景色。印象较深的是油菜花开的那一幕场景——身手矫健的妈妈翻墙抄近路出门,我站在家门口不舍地望她,忽见她跳下围墙时一个趔趄,一屁股坐在了油菜地里,唬得我号啕大哭。不一会儿,又见她起身拍拍身上的花瓣,朝我挥挥手,走了。
越过操场再往前走几步,小路的右边就是一座礼堂。现在看上去已经破败萧条了,过去这座小礼堂却是我心中神圣的殿堂。小时候这里经常上演各种外面很难看到的节目,一般人是进不去的。隔着小路对面的坡下面就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场,这里曾是我和小伙伴们奔跑撒欢的地方,弟弟在这里踢过一场场球,我在这里看过一场场露天电影……
这条路上,还走过从老家来来回回被接送的弟弟。爸妈工作太忙,无暇顾及弟弟,只好把他送到皖北姥姥家去。姥姥每回来接弟弟,都是沿着这条小路走到南大门的长江中路上坐车走的。每次临走时都听到弟弟杀猪般的号叫,这叫声久久回荡在我幼时的耳畔。有一次,我正在路边玩耍,见到姥姥送弟弟回来,在蚕室旁边的路上大声喊我乳名,我看见后转身便往家跑,气喘吁吁地报告妈妈:“他……他回来了。”母亲嗔怪地问:“谁回来了?”愣了几秒,立刻冲了出去。那时候,书信很慢,日子很长,思念也很长……
父母心里该也有这条路吧!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因为缘分,踏上了这条路,继而在这里求学、恋爱、工作、结婚、生子,完成了人生的大部分事情。
父亲1956年从全椒考到了农学院蚕桑系读本科,四年后,因成绩优异留校当了助教。而在阜阳农校的众多学生里,独母亲被选拔到省城,冥冥中来到了农学院的蚕桑研究所。当年举目无亲,背着行李,甩着乌黑的大辫子第一次踏上农学院这条小路时,她内心一定是忐忑不安的吧!所幸,在这里,她遇到了我父亲。
父亲年轻时很文艺,在学校里也很活跃。两人认识的过程据说是母亲更主动一些。那时追父亲的女孩比较多,我曾在父母家老书柜里的一本旧书里发现了父亲当年的“蛛丝马迹”。一张女学生的照片,照片上的她脉脉含情妩媚地笑着。小照背后写着:送给亲爱的姚老师惠存。小字娟秀得很。母亲为此耿耿于怀,时常埋怨父亲年轻时的风流多情。
有一年,父亲回校参加校庆,我开车沿着这条路送他们进校区。那天,父亲的初恋也从外地赶来了。在父亲口中那么漂亮、那么曼妙的女子也终究敌不过岁月的无情。一同前往的母亲那天却很精神,和自己的情敌暗地里较量了那么多年,终究是母亲胜了。我记得母亲那天打扮得很漂亮得体,紫红色的低领薄羊毛衫,配上米色长裤,脖子上围一条同色系的碎花小丝巾。我观察到,聚会吃饭时,父亲不时殷勤地给母亲夹菜……
还有一年,我驾车带着已退休的父母四处转悠,开着开着,就来到了安农大校园里。其时,父亲已患严重哮喘无法步行,我只能开车并摇下车窗缓行在这条路上,他扒着车窗贪恋地看着外面曾经熟悉的风景。当他看到以前的住处以及他当年的蚕桑系——这些洒下他青春热血和激情的地方已不复存在时,眼里的光亮一下子变得黯淡,他伤感地挥挥手说:“回吧,回吧,不看也罢。”
父亲走后,我又独自去寻找过他当年的足迹,在这条路上,转了好几圈才依稀找到一些童年的痕迹。路还是那条路,但路边的风景早已改了旧日模样,校园越来越大,楼盖得越来越多。童年的家不知何时已夷为平地,变成安农大的大操场;曾经住着6408部队的几栋蚕楼,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侵蚀,只剩下一栋,像风烛残年的老人摇摇欲坠;曾经那么耀眼辉煌的小礼堂,如今已破旧不堪,里外搭着高高的脚手架,正在重新修葺,而礼堂周边,已被饭店、超市、网吧、打字复印店完全占领,不复当年的端庄高雅;曾经架着十几门大炮的操场今日已遍寻不见,茫然不知方位;曾经掩映在绿树丛里的十几栋神秘小洋楼,如今已人去楼空,楼前,植物攀爬、落叶无径。灰旧的砖墙上挂着几块牌子——安农大老年大学、《安徽园林》编辑部、安徽省民俗学会,也不知道可有人在里面办公了。只有路的中段,当年的运动场没有变,依然充满活力地继续醒目着。场上学生们生龙活虎的姿态,让人感到生命的蓬勃向上。
有时候回到老家喜欢去翻父亲的抽屉,试图再发现一些人生线索,能够拼接起他那不算太长的一生。每次翻找,总有收获。前不久又去翻,这次找到的是一本他在农学院的毕业证书。打开,上面赫然有他的毕业照。看着当年那张意气风发的脸,我竟有短暂的恍惚。
每次我们姐弟仨坐在一起聊天,说起往事,总是有些出入,甚至还会抬杠。的确,如今爸爸在天堂,妈妈在病房岌岌可危,家中也没有什么老人可以打听。
一直后悔从前没有想到要认认真真地陪父母促膝长聊,耐下心让他们讲讲那些湮没在历史里的过去,现在想知道更多,为时已晚。
回望来路,时光就像一片片纷飞的落叶,从童年、少年一路飘洒到中年,日复一日,飘在岁月里,飘在生命里,累积着、掩埋着……对于生在合肥、长在合肥的我来说,这一生也走过了很多的路——少年时的清溪路和樊洼路,青年时的巢湖路和寿春路,中年时的屯溪路和沿河路,现在的长江西路和天湖路……这些路构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背景。然而,不知为何,在我脑海里时常闪现的,却是这条相隔久远的童年的路。有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忘记。
离开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已经很久了,这条小路我也很少再回去。这么多年,它没有随着岁月的洪流滚滚而去,而是一直尘封在记忆的盒子里,等待着某一时刻突然被打开。
其实,我知道让我无数次感伤和留恋的不是这条小路,而是无法再重走一遍的岁月和不能割舍的亲情。
2016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