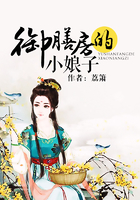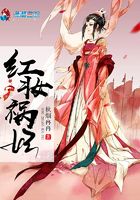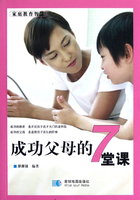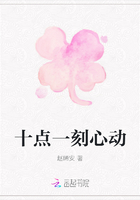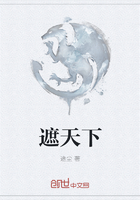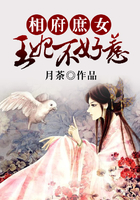一
初春,梁启超前往北京,参加庚寅年(1890)会试。会试于三月举行,因此称作“春闱”。这个十七岁的少年肩负整个家族的希望,若金榜题名、成为天子门生,将给茶坑梁家带来无限荣耀。祖父特令梁宝瑛同行,好生照应长孙。梁宝瑛大概也乐于此行,身为一名失败的读书人,一睹京城会试盛况不失为一种补偿,何况他还要拜会亲家李端棻,商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婚事。
对于梁氏父子,这是一次大开眼界之旅。在漫长的岁月里,进京赶考是一个艰苦而兴奋的旅程。帝国疆域辽阔,考生依靠骑马、骡车、帆船与步行抵达京城,倘若地处边陲,往往要花上几个月时间。这走走停停的行程也会变成一场拓展眼界之旅,考生可以暂时从枯燥的典籍中摆脱出来,游览山川、名胜古迹,拜会文友,作诗饮酒,如果足够敏感,还有机会观察民间疾苦,这都是日后跻身帝国统治阶层的重要一课。
这也是场充满自豪与憧憬的旅程,会试资格标志着他们已经成为全国精英中的一员,享有特权。每个举子都可按照路途远近获得相应的旅行补助,自几两至二十两不等。其中一些偏远考生还可以使用驿马服务,沿途以“礼部会试”的黄布旗书为标识。[82]
到了梁启超这一代,这些体验陡然发生了变化。“烈火转孤轮,浩荡随所适”,“四海真一家,万里乃咫尺”,一位举子这样形容乘坐轮船的经验。[83]近代交通令帝国的空间骤然缩小,动辄经月的路程缩短为几天,速度的刺激成为新体验。这是一场被迫的革新。仅仅四十年前,英国人的轮船想从虎门驶至广州时,还引起了当地人的惊呼,认为轮船不仅会尽杀水中鳞虫,而且破坏风水,小艇疍户也将失去营生。[84]但如今,广州的商人、官员、举子已习惯在珠江北岸的丁字码头登船,前往香港、澳门、汕头与上海,英国人的太古公司与中国人的轮船招商局,都可以提供稳定的船班。
梁启超父子先顺珠江而下到出海口,然后沿东南海岸线抵达上海,稍作休息,等待前往天津的航班。照例,他们会住在广东人聚集的虹口区,此处的鸿安客栈是南来北往的广东人最喜欢的落脚处。迅速崛起为中国最重要港口的上海,定令梁启超眼花缭乱。上海至天津已是帝国最忙碌的航运路线之一,《申报》上还会定期刊载船讯,比起昔日要一个多月才能到天津的大运河线路,蒸汽船海运只需要三天。
天津是最繁华的北方港口城市,海河旁的新古典建筑是各种洋行的落脚处。自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以来,这里还获得了显著的政治意义,以第二首都的面貌出现,各国的外交官、新闻记者、地方政治人物前往北京时,总希望能拜会李大人,有些人甚至觉得,北京的总理衙门不过是直隶总督府的一个分支。
很可惜,李鸿章铺设天津至北京铁路的建议未获通过,否则梁启超将更快、更舒适地抵达北京。他们在大沽上岸,换内河船沿潮白河西行到通州,再乘坐骡车进入北京城。这短短一段路程反而是旅途中最困苦的部分,不止一位旅客描述过这个糟糕体验。一位德国女作家形容,“这条路看起来好像刚刚经受了一场可怕地震的冲击:铺路的方石块缺损很多,缺损处尽是一个个黑窟窿,走在上面一脚深一脚浅”,他们乘坐的没有减震装置的大车更是会带来特别体验,“倒霉的旅客必须蹲在一个坚硬的大方斗里……他们从方斗的一角被甩到另一角,撞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所有人都要在旅途中肮脏的小旅店里住上一夜。[85]来自南通的举人张謇在日记中写到车夫彪悍、旅途颠簸,“下车劳倦已甚”。[86]也有旅客在其中看到诗意,德国女作家发现潮河的纤夫“身板结实俊美,如同古希腊长跑者的健美体形”。[87]新任中国公使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抵达通州时,“在河岸上看到……一群驮着茶叶的骆驼慢悠悠地前行”。
对于外来者,东便门城墙是他们最初看到的北京城。巴夏礼的女儿提到,“我必须承认,它给我的第一眼感觉并不是那种让人印象深刻的,灰色的砖砌起又高又厚的城墙,好像一座巨大的监狱”。[88]穿过城门就是糟糕的街道,“一会儿踩到一堆淤泥,一会儿又被石堆绊一下;在房屋和马路之间的空地上积满了臭烘烘的死水”,[89]这景象或许还暗示了令人不安的精神状态,“这里的人民一定是处在停滞的状态中,对任何改革都提不起兴趣”,跟他刚离开的日本比起来,“中国人十分鲁莽、易怒,经常闷闷不乐,他们的生活似乎充满了沉重的色彩”。[90]就像这个矛盾重重的帝国一样,道路的污浊只是一部分,它同样有“精雕细刻的店铺门面,飘着红色三角旗的典雅招幌,随风晃动的鲜艳灯笼,以及四处张开的流动商贩头上的大伞,这些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91]
梁启超的感受与这些外国旅行者有所不同。监狱式的城墙稀松平常,从一个普通家庭院落到新会县城、广州府,都是被这些灰色围墙包围。至于人的精神世界,整个帝国都被这种萎靡不振所裹挟,北方与南方并无太大差别。
对于梁启超这样的赶考者,“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更能体现他们的心情。千年来,帝国的首都从长安变为开封、杭州、南京与北京,这句诗一直激励着每一代赴考者,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人生机会,有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梁启超或许会惊异于北京的色调与南方的色彩斑斓不同,总是灰蒙蒙,还有广东人无法想象的寒冷、干燥与沙尘暴。北京的南方官僚会在日记中记下,“大风悽懔如三冬”,“黄沙涨天”,“昨夜半大风动地,竟日不止,甚寒冷”。[92]
与大多数举子一样,梁启超父子住在家乡的会馆中。与庙宇、茶馆、戏院、青楼一样,会馆是北京重要的公共空间。赶考举子们也借此迅速融入京城生活。北京的会馆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是旅居京师的商人与官员筹资共建,兼具旅馆与公共客厅的功能。它为同乡人提供住宿、宴请的服务。在这种氛围中,官职与地位暂时退隐,相似的语言与乡土经验将他们连接起来,共话乡情平抚孤独,缓解思乡之苦。
宣武门南拥挤着近四百座会馆,它们以省、府、县的名义而建,在大街旁或胡同内,有的规模恢宏,有的不过平房几间,折射出不同区域的财富与影响力。粉房琉璃厂街上的新会会馆,坐西向东,硬山合瓦顶,房间分前半部与后半部,有大约五十间房。相比南横街上的粤东会馆、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显得相当低调。馆内悬挂着陈白沙的对联:“紫水黄山,五百年必生名士;橙香葵绿,八千里共话乡风。”会馆建于1853年,在《新会邑馆记》中,创建者期待它可以让奔波千里的本乡人能“尽歌适馆于数千里之外,而宾至如归”。馆记由顺德人、翰林院编修李文田书写,他是声名卓著的书法家,精通边疆史地之学,日后也将与梁启超发生有趣的交集。[93]
像所有初次抵京的举子一样,暂缓旅途劳顿后,梁启超随即投身于各种拜访中。他首先要获得同乡官员的印结,这种官员联署的印结是为了防止考生舞弊,确认并非冒名者。举子还要前往拜会自己的座师,正是由于他们的慧眼,举子们才得以脱颖而出。这是一次再好不过的社交机会,可以结识京官同乡,与同年举人建立联系。对于京官来说,印结费、门生钱是光明正大的收入,弥补普遍低廉的官俸。帝国统治建立于道德之上,朝廷给官员们的俸禄极低,相信他们理应被道德责任而非物质利益驱动,这样反倒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结构:那些因道德文章而跻身官僚阶层的读书人往往会着力寻找物质回报。连接文人官僚的不仅是文章、诗酒,更是名目繁多的礼金。一种制度性腐败在四处蔓延。
在各地举人中,梁启超并不引人瞩目。他年纪小,初次入京,免不了生涩、拘谨。资深的赴考者早已熟悉北京的文人生活。浙江举人郑孝胥在广和居吃饭,到广惠寺祭奠亡友,与同期举人相聚,到东单牌楼买珠毛褂[94],张謇则不断“谒客”。[95]来自浙江的考生蔡元培兴冲冲地去见他崇拜的同乡京官李慈铭,李慈铭以诗文与性情狂狷著称,是个不知疲倦的日记作家,对蔡的评价是“年少知古学,隽才也”。[96]在广东举人中,文廷式最为知名,与张謇、郑孝胥及山东的王懿荣并称四大举人。前三人也都与户部尚书翁同龢关系密切,以他的门人自居。翁同龢生于江苏常熟,不仅是户部尚书,还是皇帝的老师,被视作南方士林领袖。
当然,比起普通举人,梁启超有自己的优势,他是一位翰林院学士的未来内弟,另一位座师王仁堪对他也颇为赏识。石星巢还着力帮他拓展交友网络,介绍他与浙江举人汪康年相识,后者曾随石星巢读书,平日居住在武汉,是张之洞的幕僚,此时也在北京参加会试。翰墨书馆有九位学生中举,石星巢尤其欣赏梁启超、谭镳、梁志文、赖际熙,称这四位得意门生是“卓荦之士,经学词章各有所长”,希望汪康年能与另外三人“一结面缘”。[97]梁启超没有描述过二人见面的情形,但他俩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对于梁启超来说,广东人的圈子尚能应付,但倘若离开了粤语,则连交流都成了问题。来自四方的举子、官员经常说一口不标准的官话,浓重的广东口音也会造成不小的交流障碍,正如一个考生在日记中写道:“造庐投谒,或终日不遇一人。既见,又不能作寒暄语,宾主恒瞠然相对。偶语一事,则方音杂糅,彼此皆不能详其颠末。”[98]
社交拜访自然重要,不过应试才是最让人焦虑的事。有了印结,新举人还要通过一场复试,才可以正式参加会试。他们要去琉璃厂挑选笔墨纸砚,梁启超熟悉考具的准备过程,但北方天寒,他要携带特别的小炭炉,既用来取暖,也可以煮饭,还能温砚台,以防笔墨冻住。
三月初六,乾清门侍卫领旨到午门交大学士拆封,御使唱名,正式宣布考官的名字。宣旨后,考官就不能回私宅了,而要直接入闱,以防作弊。这是帝国每三年一次的重要事务,必须隆重、谨慎对待。这一年的主考官是孙毓汶,副考官是满人贵恒与汉人许应騤、沈源深,同考官中则包括褚成博、杨崇伊等,梁启超的座师王仁堪也名列其中。[99]
第一场照旧是在三月初八。这一天“晨风止,阴有雨意”,尽管被称作“春闱”,冬意却未散去。举子们蜂拥至崇文门东南角的顺天贡院,贡院外墙高八尺,号门高六尺,宽三尺。比起广州的贡院,这里的场面更为壮观与慌乱。准备入闱的举子更是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式乡音,他们是全国挑选出的精英,只等着跃入龙门,成为天子门生。会试检查更为严格,而在此刻的北京脱开长衫不免痛苦万分。这一年共有6124名考生,[100]其中只有少数幸运儿将跻身帝国统治阶层。入门处是一座大牌坊,中间写着“天开文运”,东西分别为“明经取士”“为国求贤”,进大门后是“龙门”——比起广州贡院,这里才是真正的龙门。[101]
外来者很容易被贡院中的景象震惊。大多数人相信这是帝国最为公正的人才选拔机制,它不是基于血缘、神权,而是建立在个人才能之上。一位英国人受此启发,建议本国采取“一种考虑周详的地方与京城考试制度,就如中国近一千年来所实行而迄少变更的普通考试制度一样。但欲将来参加行政部门以下的各附属部门工作,则必须先经过普通考试及格然后再参加京城的专门考试”。但有些人看出了这种选拔的弊端,认为这是“鞑靼人的一个小朝廷能利用文官竞争考试的制度来网络全中国的才智之士”。[102]中国的举子当然不会知晓这些看法,毕竟他们看不到人生还有其他选择。
午正封门后,考生开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考卷长一尺、宽四寸,上有红线横直格,每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五字,先要写下姓名、籍贯、年龄、出身、三代,才能作答。第一场的题目是“子贡曰夫子之文章”。[103]与乡试一样,这一场的四书文最为重要。
对于梁启超这样的南方举子,北方考棚尤为难熬,尽管有油布为帘遮风挡雨,却依旧难抵寒气。在连续三天的应试中,第二天转晴,风却到晚上才停,第三天“浓阴,辰正雨有声,虽小而密,至未正始止”。[104]梁启超如果知道蒲松龄的描述,也一定深有同感:“其归号舍谒,孔孔伸颈,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105]
十一日,梁启超再度入场。坐在东玉号的郑孝胥在夜间答题甚速。[106]即使考场的规定严苛,甚至对上厕所的次数都有规定,但就像帝国的统治风格一样,威严外表之下到处是漏洞。三场时,郑孝胥甚至帮一旁的台湾考生写了策论。
三月十六日,考试终于结束了,举子们获得了暂时的放松。郑孝胥立刻去拜会朋友,欣赏庭院中盛开的牡丹。梁启超初来北京,可以品味这里的文化生活,去琉璃厂买书、戏院听戏。自四大徽班进京以来,京剧成了最时髦的娱乐,大栅栏就有六家戏院,其中三庆园戏院最有名,谭鑫培、尚小云都是一时名角,据说慈禧太后也常在宫中吟唱。举人们还可以去胡同吃小吃,到天桥书茶社小坐,富贵街上的五香酱羊肉也很有名。“斜日市楼评酒味,秋风门巷听车声”,其中一位这样形容这闲荡的快乐。[107]
举子们的焦灼从未消失,人人祈祷自己得中。这一年的放榜定于四月十日。性急的举人拥挤到琉璃厂的放榜处,越过拥挤的人头,寻找自己的名字,或忐忑地在会馆中等待写在绢本上的红字捷报。
梁启超的好运气没能再现,他落榜了。不过他不必沮丧,1886年考中进士的平均年龄将近三十六岁,首考就中的例证更是少得可怜,约有三分之二的进士是在成为举人十年内获得的。[108]他才十七岁,有足够的时间等待。名闻天下的郑孝胥与张謇也都同样落榜。学海堂的同学曾习经中了贡士,留下来准备殿试。
放榜也意味着一场新狂欢,戏院、酒肆挤满了举子,有的为高中而癫狂,有的借酒浇愁。除了少数幸运者留下来等待殿试,几千名举人如鸟兽散,京城从喧嚣转为平静。
对于这次北京之行,梁启超没留下任何记录。或许他急于准备会试,无心观察一切,或许被接踵而至的新经验占据着,不知如何描述它。比起北京,上海似乎意味着一个富有诱惑的新世界,对他更有吸引力。在回乡路过上海时,他在四马路的书局买到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意外地发现世界上原来还有五大洲之说,中国不过是这五大洲中的一国。他还看到上海制造局译出的西书若干种,可惜无力购买。
落第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影响,这是每个读书人再常见不过的经验,从挫败中迅速复原是必须经历的一课。梁启超该先回茶坑村,向祖父汇报一路见闻,劝慰因落榜给老人带来的失落,还要谈及即将到来的婚事。他又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轨迹,在学海堂与翰墨书馆之间穿梭,钻研时文、辞章、考据之学。
这平静的生活,很快被一次会面打破。
二
陈千秋告诉梁启超一桩异事,城里来了一位名叫康有为的学者,尽管只是个监生,却曾在北京上书皇帝呼吁变法。出于好奇,陈千秋前往康先生的住所拜访,随即被他的个人魅力与学识折服。康有为谈论了《诗》《礼》等诸经,攻击盛行多年的考据之风,还用自己的视角重新诠释了孔子。陈千秋满怀激动地告诉梁启超,康先生的学问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这才是他们期待的老师。
陈千秋的话激起了梁启超的好奇,或许还有一丝怀疑。他尽管在会试中败北,但怎么说也仍是个新科举人,自认在训诂与辞章上“颇有所知”,不免有些“沾沾自喜”,[109]一个没取得过功名的康先生,能有怎样的学问?
八月的一天,梁启超随陈千秋前往惠爱街上的云衢书屋,去拜会这位康先生。他中等身材,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唇上有两撇向下弯的胡须,肤色微黑,有股武人气,与读书人常见的文弱样子不大相同。他们可能有过短暂的寒暄,广州的学者社群联系紧密,康有为曾师从吕拔湖学习过“制艺”,另一位老师朱次琦则是肄业于学海堂的著名学者,也与石星巢相熟。正式谈话开始后,梁启超的沾沾自喜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康先生气势逼人,声线洪亮、滔滔不绝,语气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判断。
即使有了陈千秋的事先铺垫,康先生带来的震撼还是超越想象。夏末广州的炎热暂时被遗忘了,甚至时间都凝滞了,辰时开始的见面,一直到戌时才结束。“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日后写道。[110]
走出房门的梁启超感到如“冷水浇头,当头一棒”。他陷入晕眩,整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感到旧自我被摧毁后的茫然,“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111]翌日,他再次前往云衢书屋,这次康先生的态度和缓下来,又讲述了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还有对史学与西方知识的看法。对于一个生活在彼时知识气氛中的年轻人,这些观点带有显著的异端色彩,富有别样的魅力。他彻底认同了陈千秋的看法,康有为的确是他们梦想的老师。
这是梁启超人生中碰到的第一个强有力的人格,或许是最强有力的一个。不管学识、阅历还是个人风格,比梁启超年长十五岁的康有为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康有为也享有神童的名声,自称十一岁读毕四书五经,十二岁观赏龙舟竞赛,即席写下了四十句长诗。他曾入读朱次琦的礼山草堂,朱次琦想扫去汉宋之门户之见,将孔子视作最终的诠释者,推崇个人品行与实践。同样是在这里,康有为发现,比起程颐、朱熹代表的理学传统,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直捷明诚,活泼有用”,尤其符合自己的脾性。[112]
他高度地以自我为中心,早早就认定自己“能指挥人事”,十一岁时就像成年人一样处理父亲的丧事,家乡人甚至用“圣人为”来讥讽他的一本正经。他结婚时不让人闹洞房,不让女儿缠足。他立志三十岁前读完群书、成为圣贤,还曾到山中冥想世界,感到天地万物与自己成为一体,转而忧虑苍生困苦,放声大笑大哭。生活屡屡挑战他的自信,科举考试屡屡失败,让他仇恨八股文的束缚,却又更加渴望功名。
倘若按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康有为不过就是一个落魄天才而已,这在中国传统上屡见不鲜。幸好他还对外界充满好奇,游历从江南到塞外长城的景观,十七岁读到《瀛寰志略》,“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113]他还对一个新世界有直接感受,在香港看到“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114]上海租界再次印证了他在香港的印象,西方人的管理比中国人更胜一筹。对于当时的中国读书人,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或许唯有身在伦敦的郭嵩焘、严复等几人才有类似的看法。他购买了大量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书籍,从几何、数学到政治制度,无所不包,还订阅了《万国公报》。他在显微镜镜头中发现一只蚂蚁好似大象这么大,一片菊花瓣像是一片芭蕉叶,一滴水里竟有如此之多的微生物,有鳞有角,如蛟龙一样蠕动。这些都给予他观察世界的全新方法,大与小、重与轻、长久与短暂,一切都变成相对的,与佛教典籍颇有相同之处,万物真实又虚幻。
这些经历与性格赋予了他崭新的想象力。他试图在儒家学说与西方知识之间找到某种联通,解释说六艺中的“射”在孔子时代是武备的意思,在今天武备是枪炮,“御”则是驾驶火车轮船。
他更有一种罕见的行动能力,深信自己的“经营天下之志”。偶然结识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后,他了解到京城的风气,道光、咸丰、同治这三朝的掌故,开始遍读《东华录》《大清会典》等书。
1888年,康有为再次前往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他是一名与众不同的应试者,不仅对再度落榜不以为意,还认定自己“学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于人中,倜傥自喜”。[115]他马不停蹄地结交各种权贵,期望获得他们的赏识,试图让他们替自己上呈奏折。在奏折中,他公开要求皇帝下罪己诏,还描绘了一个令人惊恐的图景:俄国在北方筑造铁路,迫近盛京;英国入侵缅甸,并窥伺四川与云南;法国以越南为跳板取得广东、云南。中国正在陷入包围之中,而“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116]他大胆催促皇帝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上书并没有抵达皇帝手中,康有为的不祥警告没引发共鸣,却带来争议。大清国两百多年来,第一次有监生试图上书,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犯上。与康有为良好的自我感觉不同,人们被他的躁进、功利弄得不胜其扰。北京的一些广东人把他视作耻辱与危险,要把他驱逐出北京。连欣赏他的朋友也说他性格中“冬夏气多,春秋气少”,劝他平和一些。[117]
梁启超遇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康有为,带着失落与傲慢,混杂着古今中外的奇怪学识。他痛陈时代弊病,雄辩滔滔,既能大谈孔子之道,也能描述西洋事物,比起寻常学者的木讷、低调,他似乎显得过分生机勃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