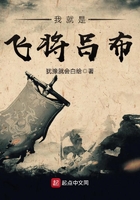南予珽和凤濯缨这几日一直逗留在粟城,每日里不是逛街买东西,就是去郊野游玩,好像有些乐不思蜀了。
“你前几日跟疯了一样,马不停蹄地赶往淮阳,好像身后有野狗撵你似的。怎么如今却是一点都不着急了?”凤濯缨问道。
南予珽嘿嘿地笑着,然后拉过凤濯缨的手轻轻吻了一下:“前几日我还是个毛头傻小子,当然只懂得快走快跑。现在我长大了,明白了这温柔乡的好处。”
凤濯缨被这个死皮赖脸的男人说得脸上一红,但是手却乖乖地被他牵着,一点儿想拿回来的意思都没有。
“不过这几天咱们把这粟城逛的也差不多了,该玩儿的该看的都享用到了,是时候离开了。”南予珽说道,“更何况我看这粟城里的姑娘长得都挺不错的,我怕再待下去,我的那些卫兵将士们非在这安居乐业不可。”
凤濯缨歪着头,眼神犀利:“看来王爷的眼睛不光是只看了粟城的美景,还不忘这看美人啊。”
“美人天下何其多,但是我只喜欢会扔石子儿,会耍鞭子的。”
凤濯缨伸手想要掐南予珽的脸,却被他反手压在身下,动弹不得。
“现在是大白天,你可别胡来!”凤濯缨脸更红了。
“白天我不乱来,那晚上是不是可以随便乱来……”南予珽笑得春意盎然。
“你先起来!”凤濯缨瞪着眼睛骂道。
南予珽怕自己媳妇真的生气了,便翻身又躺在了凤濯缨身边。
“濯缨,你知道吗?以前你说你生了病,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还挺失望的。”
凤濯缨听南予珽提起以前她撒谎失忆的事情,心里有些不好意思。她不知道要如何解释这件事。
“南予珽……”
“不过我现在很知足,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有现在,还有未来,这不就足够了吗?”
凤濯缨忽然觉得自己心里满满的,她悄悄把手伸了过去,然后握住了南予珽的手。
“只是,我还有有些事心里边过不去。”南予珽又说道。
“还有什么事情?”凤濯缨起身问道。
“嗯……”南予珽细长的凤眼微微眯了起来,“我皇兄,我二哥,我母亲,我最亲近的人都叫我的表字三阶。只有你,从来只唤我南予珽,听起来怪生分的。我可是成亲第一天就把我的字告诉你了呢。”
“哦哦……”没想到南予珽竟还在乎这些事,凤濯缨有些尴尬地应承着。
“以后,你也唤我三阶吧,好不好?”南予珽认真地问道。
“三……三阶。”
“欸,我在这呢,我的好夫人。”南予珽满足得好像一只小狐狸。
“不过你的字也够奇怪的,你大哥叫有容,二哥叫秦箫,这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叫三阶,难道是三个台阶的意思不成?”凤濯缨好奇地问。
南予珽随即给了凤濯缨的脑门一下:“唉,我家娘子竟是个只会舞刀弄枪的粗人,一点书都不念的吗?这《黄帝泰阶六符经》里说: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上阶为天子,中阶为诸侯,下阶为士庶人。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天下太平。”
凤濯缨的眼睛瞪的大大的:“原来,你的名字这么大?感觉比皇帝的名字还大呢。”
南予珽伸手又拍了一下凤濯缨的脑门:“这话也是瞎说的吗?虽然我和皇兄关系很好,但是这种大不敬的话也不能说出口,听见没有?”
凤濯缨用手护着自己被蹂躏的脑门说道:“其实我宁愿你不要这么大名字,不要这么大的抱负,我们一起在淮阳安安稳稳地生活,不是挺好的吗?”
南予珽叹了口气:“生在天家,哪有什么安安稳稳。有些事情你不去争不去抢,别人也会拱着你去争去抢。”
看凤濯缨表情忧虑起来,南予珽又笑着宽慰她:“不过你放心,所有的一切的决定权都在皇兄。我和二哥只是尽可能好好办差,好好展示自己而已。”
“那若是……若是皇上最后选择宣文王会怎么样?”凤濯缨试探着问道。
南予珽惊讶地看着自己的王妃:“你是我的妻子,为什么总想着别人赢了会这么样?”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南予珽把凤濯缨揽在自己怀里,“我知道你担心我们兄弟相争会伤害到对方。但是只要是兄弟,必定会相争,那一奶同胞的狮子老虎还会相争互抢,更何况人呢?”
凤濯缨听了这话,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原本以为南予珽没有争强之心的,所以她才愿意向自己的父亲保证看好南予珽,不让他危害南平。
可是现在开来,没有哪个男人面对极致的权力不动心不沉沦的。
“不过你也不要担心,我们再怎么说也是兄弟。兄弟会争抢,但是绝不会伤害。”南予珽说道,“更何况与大宝之位相比,我更希望皇兄能长长久久,长命百岁。那我就是在外面打一辈子仗,也心甘情愿。”
凤濯缨把头埋进南予珽的胸膛,从小到大,她只有今天是那么虔诚地问皇帝陛下祈祷,希望他能长命百岁,千秋万年。
================
行装已经整理好,马匹也喂得足足的,南予珽决定再次上路。
但就在他们快要从粟城门出来的时候,一个矮矮的小老头大呼小叫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且等一等再走,等一等再走!”
白幼清下了马,走到那老头面前问道:“你是谁?你可知道你拦的是谁的马车?”
那老头诚惶诚恐地行了一个礼,然后说道:“回大人的话,小的粟平简,是这粟城的县令。小的当然知道这马车上的是谁,所以才赶忙跑来了。”
白幼清一听便压低声音皱着眉头警告道:“知道还来?我家王爷就是不愿声张,所以才没有告知你们地方,现在这送行也就不必了,你们回去吧!”
“大人,王爷的意思小的当然明白,王爷出行从简,不愿扰民,是王爷体贴大度。只是这次小的来为的是另一件事。”
“那你到底所为何事?”
见白幼清总是挡在马车前不让自己靠近,粟平简突然跪倒在地,大声疾呼:“有人在县衙击鼓鸣冤,要状告王爷您啊!”
白幼清吓了一大跳,心下暗道这个老头好不上道,这样的事情不私下先沟通,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喊出来。
“你这个老头在乱说什么?还不快快退到一边去。”白幼清一个劲儿地给那老头使眼色。
但粟平简却耿直地跪在地上,就是不起来。
南予珽见白幼清一直在和那拦车的人拉拉扯扯,便亲自下车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粟平简见南予珽走下车,大喜过望,连忙跪着爬到南予珽脚下,大声说道:“粟城有冤屈难审,还望王爷替我们做主。”
南予珽看着突如其来的拦车之人,心里突然升起有一股莫名的感觉。像是在暴风雨的前夜,那吹动柳条的微风,平静得让人担心。
==============
南予珽最后随着粟城县令回了县衙,亲自去瞧一瞧到底是谁这么有胆子,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状告当朝王爷。
一到县衙,一股恶臭之气扑面而来,熏得南予珽差点背过气去。
“你这县衙是怎么了?”南予珽捂着鼻子问,“几天没有清扫了?”
粟平简没有回答,而是引着南予珽到大堂之上。
这大堂之上有三个人,一个人跪着,两个人躺着。
躺着的人蒙着白布,看起来已经去世多时了。
粟平简小声地和南予珽说:“就是他要状告王爷您,还拉来了两具尸首。已经摆在这好几天了。小的劝过,骂过,吓唬过,但是全然无用。现在天气虽然寒凉,但是也禁不住这尸首一直放在这大堂上啊。在这样下午,我这县衙快变坟地了,还请王爷救救我们。”
南予珽走到跪着的那人身边,然后问道:“你是谁?为何要状告成武王?”
跪着的人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还挂着泪。他看着约摸十来岁,还是个孩子,长得倒是虎头虎脑,有着一股不服输地精神气儿。
“你又是谁?我为何要告诉你?”那孩子问道。
“我就是成武王。”
那孩子有些惊讶,他以为这南征北战的成武王一定是个膀大腰圆的黑脸壮汉,但眼前的这位却是个眉清目秀,肤白如雪的漂亮公子。
见那孩子不说话,粟平简赶紧跑上来说道:“你这愣子,拿着这死人待在这许久不就是为了见到成武王?现在见了他怎么倒不说话了?”
那男孩吸了一下鼻涕,然后说道:“我叫高吉东,是粟城人。我告成武王管理下属不利,致使下属为非作歹,鱼肉百姓。”
经过一番询问,南予珽才了解到,原来这孩子是粟城高万鸿的小儿子。
这高万鸿虽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家里还是有着几十亩良田和一个大宅院,一家人过得算是衣食无忧。
但是去年夏天,一股子淮军驻扎在这里。而他们的首领就是淮军副都统杨青。
杨青本就是粟城人,这次换防他特地带人驻扎在这里,就当是回了家。
而既然回了家,那自然得把自己的功绩好好在自家里宣扬一番。毕竟自己可是在淮军里吃得开的。
而宣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翻修祠堂。
杨家的祠堂面积不大,这让杨青很不满意,他见祠堂边的田地又大又宽敞,便叫人把地里的苗拔了全盖成祠堂。
这地便是高万鸿家的。高万鸿当然不乐意,但是对方是军人,自己家只有家丁,硬拼是拼不过的。
高家便来县衙告状,但是对方是军人,根据南平法度,军人之事地方不予管理。
高家见状便想去京城高御状,可是却被杨青派人拦了下来。他们把高万鸿和他的大儿子高吉北全部打入死牢,折磨而死。又将高家的女儿奸污,逼着她发疯。
现在高家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只剩下这十几岁的孩子还支撑着为自己可怜的家人申冤。
“王爷,这孩子要上京城,我怕不妥便拦下来了。”粟平简说道,“但是这事情,却的确让人生气寒心啊!”
南予珽听后是十分震怒,他拍拍那孩子的肩膀说:“你放心,我一定查明此事,还你们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