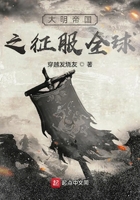张继宗也会武?俺暗自寻思。
民国十七年(1928年)“济南惨案”后,镇上的年轻人就都开始喜欢学武了,哪怕是一招半式,可人们从没见张继宗练过。
张继宗今年三十九岁,尽管比俺大十七岁,可俺跟他是同辈。他有一儿一女,平时在镇里是个很不起眼的人,有人欺负了他的子女,他从不计较,即便有人欺负了他,他也只是笑笑,自认倒霉。
仙姑拐线、里外骗马、左右缠脖、背鞭转身、十字披红……只见张继宗来到庙宇中央,身形转动,手中的麒麟鞭上下翻飞、虎虎生风,啪啪的响声在大殿里回荡。
俺摸了摸腰间的七节鞭,自叹不如。
鞭是武术中的一种软兵器。它由鞭头、鞭把及中间若干鞭节用铁制圆环串接而成。在我国北方,鞭大致分为四种:七节鞭、九节龙、十一节麒麟鞭和十三节鱼麟鞭。鞭谚说:纵打一条线,横打一大片;纵抡横打,威力无边。这种鞭软中取硬、出其不意、接招致命。不过,习练鞭术要求很高,除了它特有的方法外,还要有拳术方面的一些身形、步法及跳跃、翻滚等基本动作,需要有较好的协调性、灵活性、柔韧性、弹跳力和劲力等;在身法方面,经常运用闪、转、俯、仰、卧、滚、翻、腾、纵和回等动作;在腿法方面,经常运用正踢、侧踢、里合、外摆、弹踢、蹬腿和横踹等动作;在步型步法方面,经常运用马步、弓步、丁步、虚步和插步等。
张继宗还在舞动着麒麟鞭,看他的鞭术,没有三十年的功力达不到,镇上同来的人都惊得老半天合不拢嘴。然而,俺似乎明白他为什么深藏不露,因为他不到四十岁。
父亲曾多次提醒俺,学武之人流行着这么几句话:学三天,打遍天下;学三年,要啥无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动手不留情,留情不动手。也就是说,武术没学到家,就不能轻易跟人动手。一旦动手,就要比试个高下,哪怕是亲兄弟。爹再三叮嘱:四十岁以前,不管练多少年武术,在人家面前只能说不会。
只听“嘭嘭”两声,张继宗手中的鞭停止舞动,少顷,鞭哗啦一下掉到地上,他的两只胳膊嘀嘀嗒嗒往下滴着红色的液体。俺们知道他也中枪了。
“唉,可惜啊可惜!”小矮子边摇头叹息边命人给张继宗包扎伤口。张继宗推搡着不允,又过来两个黑衣人强行摁着,才将伤口包扎好。看到这里,俺恍惚间感觉,小矮子是个好人,可很快俺便知道,俺错了。
“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嗯,味道不糙,有这么好的肉吃着,俺就是死一辈子也乐意。”解文元吃完手中的驴肉,边说边用右手食指抠着牙缝,又打了个饱嗝,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接着清了清嗓子,唱起山东民间小调:“送情郎,送情郎,一送送到大路上,暂时的离别你可别心伤,就三年两年不见那又何妨。送情郎,送情郎,一送送到大路上……”
“八嘎,你的什么的都可,唱歌的不要,你的明白?”一黑衣人过来踢着解文元的后背,用生硬的汉语说道。
“森木君,森木君,zS?0$$°$¥%℃¤~‖~&*&……”看到这里,小矮子急了,大声喊着踢解文元黑衣人的名字,然后呜哩哇啦说了一通。
“田中君,$$°$¥%℃¤东亚病夫$¥%℃¤……”那黑衣人沉着脸对小矮子说,言语中夹带着中文。
“除了那个烟鬼和这个白面小生外。”小矮子指了指解文元和张世风,用流利的汉语说道,“其他人不是病夫,他们是好汉,令我非常钦佩……”
听着他俩的对话,俺明白了,这个小矮子应该叫田中,踢解文元的叫森木。也明白了,原来这些黑衣人是日本人。可日本鬼子为啥要置俺们于死地呢?
“日本鬼子!”高绵勋惊叫道。
“他们想隐瞒身份,没想到让森木那个冒失鬼挑开了。”解文元笑呵呵地说。
“有啥好笑的,咱们知道得越多,就越活不了。”张世风摇头叹息。
“这些日本人为啥要杀咱们,无冤无仇的?”高绵勋皱眉道。
“日本人颠羡(胶东方言:猖狂)呗。”张继宗抱着胳膊拉长声调说,“你们不是知不道(胶东方言:不知道),日本人侵占了咱东三省,建立什么‘满洲国’,去年腊月,又让溥仪当上了‘大满洲帝国’的皇帝。他们颠羡得不行了,还到处派兵,杀人放火的。”
“人家颠羡,那是人家厉害,有啥办法。”张世风说。
梁增年显得很焦急,沉着脸说:“不过,要是咱们回不去,那麻烦可就大了。”
“啥麻烦?”高绵勋问。
“啥麻烦?”梁增年压低声音,“咱这次去诸城干啥,不是找县政府说理?要是咱们回不去,镇上的人能善罢甘休,不得找县政府要人?这事恐怕要闹大……等天黑了,咱想办法逃回去,哪怕是一人半人的,也得赶紧回去报个信儿。”
众人觉得梁增年的话在理,纷纷点头同意。可俺觉得,能逃出去吗?这些日本人的武器歹毒,神秘莫测,不像镇上的那些日本人,看上去还非常友善。
古堂镇三面环山,尽管偏僻,可土地肥沃,历年风调雨顺,大多数人能丰衣足食,也是远近闻名的富裕镇。由此,日本人在镇上开了两家烟馆,东头那家叫惠馨戒烟馆,西头那家叫兴隆戒烟所。虽然名字里含有“戒烟”二字,可那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惠馨戒烟馆里有八个日本人,一男七女,男的是头头,叫荒尾精,三十多岁,身材还算魁梧,长脸,高颧骨,经常挂着把武士刀;七个女人中,有一个是他太太,另外六个是艺妓,打扮得十分妖艳,对人十分谦恭;西头的兴隆戒烟所里有五个日本人,两男三女,头头叫西尾勇造,个头矮,戴着副眼镜,看起来挺斯文。另一个男的叫才明二郎,武士打扮,其他三个女的都是艺妓……
“明白,吃吧。”解文元的声音打乱了俺的思绪。对了,这里跟众看官交代一下,俺叫张明白。扭头俺见他正递来一块驴肉。
“既来之,则安之。明白,急也没啥用,先吃饱了再说。”解文元笑着说。他见俺在犹豫,安慰着说:“没事儿,应该没毒,有毒的话,毒性也不大。俺吃了老半天,现在不还好端端的?”
“唉。”俺接过驴肉,感觉肚子真饿了,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镇上的其他人手里也都拿着块驴肉,大嘴小嘴一鼓一瘪地吃得非常带劲。
把肚子填饱后,眼皮便有点儿睁不开了。俺寻思,管他死不死的,先睡饱了再说,机会来了也有劲儿逃跑,千万甭坏了自己“飞毛腿”的名声。当然,俺练就的飞毛腿,很多人还不知道。
从记事起,每天五更,父亲就叫俺起来练功,有“行者”武松的武松拳(拳,胶东方言念锤),“浪子”燕青的棍术,“豹子头”林冲的枪术,“金眼彪”施恩的鞭术,都是梁山武功,其实,应该都是后人借梁山好汉的名自创而成。头几年练基本功,然后是套路和实战。基本功包括腿功,父亲经常让俺转树林、穿树空。日积月累,俺走得特别快,八十里的山路,十多个小时能打个回来。俺擅长鞭术,经常腰间缠着七节鞭,以此防身。能学这么好,当然是父亲教得好,自己肯吃苦,好像也有点儿遗传,因为俺家在当地是武术世家。
俺爷爷是清光绪年间的武秀才,据说一百二十斤的关公大刀可以舞动如飞。他的哥哥是清光绪年间的文秀才,有九个女儿。爷爷有三子一女。父亲张德贤是老大,育有两子两女,姐姐已出嫁,俺下面有弟弟张明礼,妹妹张明秀;二叔叫张德武,曾在北洋军当过班长,他有一个儿子叫张明友;老三张德亮,有两个女儿,都在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作,前些天,纱厂工人因劳资矛盾罢工,就回来了,顺便看望大爷爷;姑姑张德芬嫁到了胶县,儿子王恩华很有出息,不到三十岁就成了国民党胶县县党部的主管。受家族影响,父亲和两个叔叔自幼习武。不过,习武之人的脾气多数不太好,寿命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二叔是个暴脾气,不到四十岁就因病去世。现在父亲的身体也不好,不能干重活。家里的活主要落在了娘、俺和弟弟妹妹肩上。三叔在私塾上过几年学,性格温和,为人低调,较两个哥哥来说,身体最好。
此时,大殿渐渐暗了下去,同镇的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周围的黑衣人换了一批新面孔,仍旧虎视眈眈。
看着阴森可怖的庙宇,俺非常害怕,不知自己能否逃出去,若逃不出去,不知该如何死去;也不知自己这么一天没有回去,家里人是否非常着急?俺寻思,如果自己死去,家人会非常悲痛的,尤其是娘。尽管镇上经常死人,可多数是夭折的孩子,像自己这么个大小伙死的还不多见……俺就这么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睡着了,也许这是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
当俺睁开眼睛时,只见从房顶的缝隙中透射出明亮的光,一些细小的尘土在那寂静的光里飞舞。大殿里同镇的人还是那么多。后来得知,梁增年策划的夜晚逃跑行动没能如愿,他们被日本鬼子用一种特殊的铁棍打了回来。听说这种棍打在身上,会有一种剧烈的让人难以忍受的麻木酸痛感。
“他娘的,日本鬼子为啥不赶紧杀了咱,关在这个破地方做啥?”高绵勋骂骂咧咧道。死亡对于他仿佛是个期待。
“呵呵,俺觉得咱们没有事儿,应该是个误会,他们或许跟咱开玩笑哪。”解文元笑嘻嘻地说着没有底气的话。
听解文元这么说,郭松金急了,举着胳膊骂道:“他娘的,开玩笑,有这样开玩笑的吗?”
“哦,嗯,那不是又给你包上了?嗯,玩笑开得是有点儿过。”解文元徒然降低声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