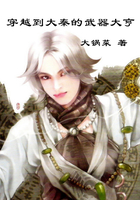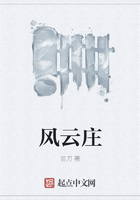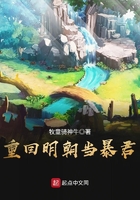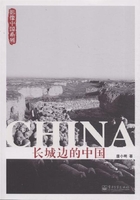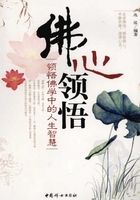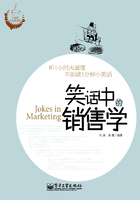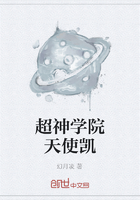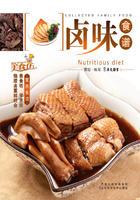夜晚的金陵城无比热闹,自打晋帝解除宵禁后,金陵城市井之间的嘈杂声比起白天更甚。
从远处看这座宛若长龙般盘伏在长江边上的城池,长街灯火与天上皓白明月交织成一副极美景象。江北的风徐徐卷进金陵,本没有多大劲的风竟刮走金陵皇城瓦砾上的灰尘,阵阵清风夹杂着微小尘埃散漫在偌大的金陵最后也不知去向。
西城外一支装备精良约百人的骑兵部队缓缓的开进了金陵。为首的年轻男人样貌俊美,身着一袭玄色长袍,袍子上纹有金丝蟒龙,端坐在一匹白马之上,英气逼人。
西市上的人见到这支队伍很自觉的避开了,原本金陵最为嘈杂的西城夜市竟在此时安静了下来。
这支骑兵部队的行进速度不慢,不一会便消失在街道尽头。
安静的西市恢复原样,只不过街上负责巡查的城卫不知何时多了两队。
茶楼上的一些富贵人家的公子们品着茶,欣赏着月色,偶尔会有诗兴大发的文人即兴赋诗,对于刚刚的那支骑兵部队他们早已见怪不怪,近日圣上召集各地藩王进京,每天都会有不同形色的藩王仪仗队进京,从刚刚男人身上的蟒龙袍看来应也是一位藩王,而大晋当下最年轻的藩王便是有“当代军神”之称的江陵王:司马玄。
坊间皆传司马玄军神之名来自于三年前那场南阳血战。
三年前鲜卑族首领拓拔圭自凉州举兵攻打北周,晋帝断定北周内部混乱,防守松懈,遂先后下令十一位藩王起兵北伐,数月间中原战火不息,最终这十一位藩王有九路大败而归,唯有江陵王司马玄和广陵王司马征还在鏖战,广陵王率军猛攻青徐二州受挫便迁回已攻占领土的人口缓缓南撤,司马玄率军六万于南阳遭遇周军主力和鲜卑族拓拔圭主力,三方即将混战,司马玄分析形势后便联合周军共同对抗拓拔圭,使诈败之计诱敌深入,最后在南阳野外全歼拓拔圭四万精锐铁骑,后率晋军攻取南阳,周军也很识趣的退去了,司马玄一战成名,而此番南阳之战注定载入史册,成为冷兵器时代,步兵反制骑兵的经典战例。
而近日晋帝诏命各地藩王进京议事,便是因为北周已被鲜卑大军所灭,拓拔圭于洛都称帝,国号凉,随后拓拔圭陈兵十万于南阳,遣使金陵,让晋国主动割让南阳。
“咳咳咳……”
烛光下,司马玄轻咳数声,眉头紧缩,跪坐在书案前,捧着木茶杯,目光凝重的看向案上的南阳军镇布防图。
“李煊,如今南阳太守是谁?”
闻声,那位叫李煊的人来到司马玄身边拱手道:“回王爷,南阳太守是胡颜路,胡欢的侄子。”
“胡欢?”
听到胡欢二字,司马玄面色更加凝重:“胡颜路为人如何?”
“属下不知,王爷,是否……”李煊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不必了,胡欢是圣上宠臣,为相十多年,在这京中势力只手遮天,本王对胡颜路为人尚不了解,若此时对胡颜路冒然动手不妥,你拿本王印玺去吏部调胡颜路的官案。”
“是。”
李煊拿起书案上的印玺跃窗而出,消失在黑夜中。
一炷香后……
相府,一位身形佝偻的老者侧身斜靠在摇椅上,老者面色红润,精神抖擞,手指不停在椅上敲打着,目光正对面的便是一群戏曲班子,伴随着戏曲音乐,老者又从身旁侍人手中接过一副苏州官窑产出的镀金银丝茶碗。
轻抿一口,便将茶碗随意放在身旁的矮桌上,微微叹了口气:“说吧,有什么事。”
“相爷,江陵王从吏部调走了胡太守的官案。”
闻言,半晌,胡欢便从椅子上撑起身子,眼神有些惊惧:“江陵王?”
随后道:“张权,你怎么看?”
那位名叫张权的侍人摆放好矮桌上的茶具对着胡欢拱手道:“回相爷,江陵王此番查探胡太守底细,料想应是与圣上明日朝会议论南阳之事有关。”
胡欢点了点头,缓慢的站了起来,对着戏班摆了摆手,相府内顿时安静了下来。
“广陵王进京了吗?”
“相爷,广陵王于前日已抵京城,现下正在府邸与各位藩王议事。”
胡欢心里清楚,广陵王年高望众又是当今圣上的伯父,虽常年镇守江北军镇,但其对朝政之事颇为用心,此番聚集众位藩王议事应也是为了南阳之事,如今朝中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局势尚不明朗,胡欢的相府每日也是门庭若市,文武群臣争相想要摸清胡欢的态度,对于这些人胡欢很聪明的避开了两派之人矛盾的焦点,既不表态又不说不管。
翌日。
朝堂上今日偏显拥挤,在京的文武百官各立左右,身后站着一些进京述职的各地军镇刺史,龙阶下立着各地藩王,藩王两侧为首的便是广陵王司马征和江陵王司马玄。
“自朕诏命各地藩王进京议事已有十多日,除了川中的藩王和云贵的藩王路途遥远朕未予传命,想必其余诸位藩王皆已到齐,今日朝会便敞开了说,对于拓拔圭在南阳的军事行动,诸位爱卿和诸位藩王有何意见?”
龙椅上的晋帝目光扫视着龙阶下的文武百官。
“启禀圣上,臣有话要说!”
闻言,晋帝和朝臣寻声看去,说话之人乃是兵部尚书杜朗。
杜朗挺直腰板走出队列,朝着晋帝微微躬身,语气硬朗道:“启禀圣上,南阳存失干系到我大晋的荆襄防线是否稳固。”
“在江陵王收复南阳之前,我晋军在荆襄一带与周军的对峙一直处于下风,军事冲突常有重大损耗,如今北周覆灭,南阳的存失反而不再那么重要。加上这几年来鲜卑骑兵纵横中原锐不可挡,北周武卒都不是其对手,更何况陆战并不是我晋军强项,我军更应避免与凉军发生正面对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从而动摇整个荆襄防线。”
晋帝微微侧目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司马玄,随后问道:“那依你的意思,我大晋应该放弃南阳?”
杜朗躬身作辑:“没错,望圣上裁断!”
晋帝沉默半晌,他继位十三年以来无时不敢忘记先帝光复大晋山河的遗愿,自他继位起,晋军的军事行动次数比之往年历代先帝时期的军事行动总和之数还要更甚,而三年前北周内部大乱,鲜卑崛起,只恨北伐失利,未能一举匡复昔日山河。
晋帝的沉默不语,朝堂上顿时犹如炸开了锅一般,群臣交头接耳议论纷纭,原先那些主战派的大臣听杜朗一言皆有倒向主和一方的趋势。
杜朗见晋帝没有动静,便再次进言:“若圣上还想明确众臣态度,那么老臣请户部尚书孙大人代表户部说话。”
杜朗当然知道晋帝的心思,举国上下没有不知道当今圣上有匡复山河之志,但是依照如今的局势来看鲜卑大军锋芒正盛,南阳若启战端,那晋军的胜算是十分微小的。
杜朗言出,朝堂再次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户部尚书孙若平。
孙若平走出队列,对着晋帝微微躬身道:“圣上,杜大人所言有理,往年我大晋与北周的战事以荆襄一带最为剧烈,自圣上继位十三载以来,我大晋每年对荆襄防线的军费支出有两百余万两白银,占我大晋一年三成的收入,若遇战事则需每年在这二百余万两白银的基础上额外多支出一百余万两白银,三年前因北伐损失惨重,长江下游地段洪涝灾害严重,国库却拿不出银子去赈济灾民,若非我大晋举国上下军民一心,怕是早已激起民变啊!圣上!”
孙若平越说越激动,吐沫星子都快飞到龙阶上。
“一派胡言!”
胡欢听到这里突然吼道:“三年前洪涝灾害朝廷已经下拨二百万两白银用来赈济灾民,那二百万两白银是被你们户部吃了吗?”
“这……”
户部官员皆面色难看,那二百万两赈灾银朝廷的确有发,但多数皆流进相府,大多户部官员也收到了胡欢的好处,得知灾区情况持续恶劣不见好转的晋帝大发雷霆要彻查赈灾银流失一案,却因户部官官相护,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而如今孙若平于南阳之事重提当年事端,难免胡欢会如此暴怒。
“那二百万两白银是不是被我户部官员侵吞,胡相应该最为清楚!”
孙若平为官清廉,为人刚直,对于当年赈灾银侵吞一案他也有所抵抗,奈何胡欢权势熏天,户部众数官员大多为胡欢门徒,案件牵扯到整个户部,孙若平也只得放弃。
“你!”
胡欢听到孙若平此话暗指之意,本就老迈的身子此时竟也站直了起来。
“孙大人此话恐为不妥啊!”
“是啊,孙大人!”
“胡相日日为国事尽心尽力,当初赈灾银流失,胡相也是自掏家底拿出五十万两白银勉强才将灾区情势稳定。”
“孙大人此言未免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你们这些人又做过多少伤天害理之事!拿过多少人家的好处?有何脸面提及君子之论?”
……
顿时,朝堂上胡欢的门人站出来为胡欢说话,那些原本就不满胡欢的臣众此时也站出来批斗胡欢门人。
孙若平被气的青筋暴起,正欲发作。
眼看着朝堂即将乱作一团,晋帝终于忍无可忍大喝道:“好了!”
“朕今日朝会所议南阳之事,尔等如此,是为何意?莫非是要朕重察当年之案,兴起大狱,让朕身陷于不仁不义之中?”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
见到晋帝发怒,原本嘈杂的朝堂在一瞬间便安静了下来,刚刚参与争吵的臣子纷纷跪伏联声:“请圣上恕罪!”
“罢了罢了!都起来吧!”晋帝心生厌恶,摆了摆手。
“谢圣上!”
见到朝堂稳定下来,此时南阳刺史王讪挤出群臣队列朝着晋帝躬身一拜,随后目光如炬般的看向晋帝:“臣南阳刺史王讪,有话要说!”
晋帝早就了解到王讪其人是死忠之士,更是主战派的中流砥柱之人。
当初在敲定南阳刺史欲派何人之时,广陵王司马征一封推荐信让晋帝下定决心调派王讪担任南阳刺史。如今朝堂上情势混乱,王讪区区一名地方刺史竟然敢在此时站出来说话,可见王讪其人的确忠勇。
晋帝大喜过望,急忙挥手道:“免礼免礼,王爱卿有何言论,尽请敞言。”
“谢圣上!”
王讪直起身子走到杜朗身边用一番打量的目光扫视杜朗随后轻蔑一笑:“昔日卑臣随广陵王北伐时,曾听闻兵部杜大人乃忠烈志士,如今看来杜大人不过乃贪生怕死,畏战如虎的一介宵小匹夫而已!”
此言一出,犹如一道惊雷劈在这朝堂之上,所有人都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