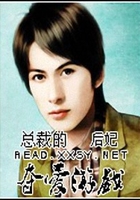“你小子从刚才就一直打瞌睡,怎么,昨晚没睡觉啊?”
“你还好意思说?你的呼噜声就没断过,我怎么睡?”
“那你现在睡会,醒了替我。”
这是汉斯叔今天第一次跟我说话,听语气似乎又变成了那个令人讨厌的唠叨鬼,可令我没想到的是,从今往后再也听不到他的牢骚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只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我来没来得及睁眼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已经被旋转的车子给甩了出去,摔在路边的荒草滩里,脑子“嗡嗡”作响,全身像是被捏碎了一样,动一动都钻心的疼。我忍着痛强睁开了眼睛,却被头顶上流下来的血给迷了眼,什么也看不见,我想喊汉斯叔来救我,嗓子却已经连疼都喊不出了。我想这就是每个旧城区人们的命运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死了,现在终于轮到我了,好在我也在这末世逍遥过一把,算是不留什么遗憾了。就在我意识逐渐模糊的时候,耳边传来了嘈杂的人声。
“老大,车里就这一盒子。其他的都是些碎玻璃瓶。”
“一盒子?把这个老头带走,回去好好问问。”
......
等我再醒来时我已经回到了学院城,看着熟悉的房间仿佛我从来没有去过什么霍普阿克,但遍及全身的痛楚似一个巴掌把我打回了现实,我...竟然还活着?
这时房门被打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只见她拿着两根棍子二话不说就往我腿上绑,似乎还没有注意到到我已经醒了。我被她这么一绑,疼得哼叫一声,她同样被我吓了一跳,“啊”的大叫一声,棍子应声落地,我心说这女人胆子也太小了,就跟学院派里那些没见过尸鼠的小子们一样。而她这一声也把隔壁的一个男人给惊了过来,进门便问: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他,这个人,他叫了一声。”
“哦?”男人有些疑惑,但看见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似乎也吃了一惊。
“你...他...你竟然醒了?真是不可思议!”
“什么?他醒了?难怪会有声音发出,那你问他能说话吗。”
男人转过来问我:
“嘿,小子,能说话吗?”
见我没反应,只好丧气地告诉女人:
“看来是不能。”
“那你给他绑吧,被他这样盯着,我不习惯。”
说罢女人把剩下的一根棍子交给男人后就出了房间,只剩下我和这个男人。从屋子一侧照过来的光线上看去,我并不记得见过这个男人,他的下巴胡子拉碴,头发却不长,像是被修理过,声音尖细,瘦削的脸上依稀可见一层细细的绒毛,一双贼眉鼠眼似乎总在盯着一个目标,看样子就是学院城旧城区里的夜枭酒吧的常客。
男人只好无奈地搬来把椅子,随手点燃了一根烟,我一闻就知道他抽的不是紫苏那种稀缺货,而是一种取而代之的赝品,那些有烟瘾但又买不起正牌货的穷鬼们,把任何能浸透的东西先浸在酒里,然后拿出来晒干,最后再制成烟卷,抽起来一样有紫苏的感觉。
“你叫乔伊是吧,我认识你,前街卖零件那小子是不?我说你也真够惨的啊,被炸成这副摸样,要不是上头执意要把你带回来,你小子早就成了尸鼠的粪便了。不过你也别把我们当什么好人,干我们这行的向来是一物换一物,就不知道你小子的命值多少了。唉,真是可惜了那辆T-300啊。”
说完男人转身便出去了,交给他的棍子也被他随手放在了床边。听他这样一说,现如今我八成是让那些城外拾荒的人给捡回来了,这人口口声声说是“上头”要求把我带回来的,难不成这个拾荒的也发展成帮派了?学院城不像霍普阿克,人口流动频繁,在我卖零件的这几年里,眼前的人来来往往就那么些个,而夜枭酒吧更是汇聚了旧城区最顶尖的帮派大佬,我虽然没接触过,但也有所耳闻,可这拾荒者里头的老大,我却从没听过。
也不知汉斯叔现在是死是活,只记得昏迷前听到有人说要带他回去,估计也是和我一样的下场,问出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再杀人灭口,这人虽然没有直接要挟我,但帮派的手段向来如此,最后连尸体也不能浪费了,卖给人肉贩子还能再赚一笔死人钱。
屋子里的光缓缓的灭了,隔壁也听不见任何动静,在宛如死一般地寂静里,我只能静静地等待未知。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简直像梦一般奇妙,陌生的人,陌生的地方,还有陌生的死亡无时无刻不在围绕着我,我才发现原来当初的生活竟如此惬意,卖着练来的零件,吃着买来的鼠干,喝着隔三岔五的美酒,去着梦寐以求的酒吧,以前的我根本不用考虑以后会怎样,更不会考虑死亡会何时降临,在别人眼里我们只是一群苟且偷生的末世“享乐人”,没有威胁,更没有价值。既然死亡已是命中注定,那么快乐的活着再痛快的死去就是最完美的结局。可是命运似乎偏偏不怎么眷顾我,算起来,我已经两次从死亡线上爬了回来,第一次神不知鬼不觉,第二次就把自己弄成了如今这副摸样,现在的我简直生不如死,还要被这些拾荒者榨干我身上仅剩的一点价值,这种恍如隔世的巨大的落差感正以血的代价告诉我生逢末世的现状。
我长叹了一口气,干脆,让他们给我个痛快得了。
......
奇怪的是从我醒来那天开始,我只要一睡着,就会陷入梦中无法自拔,梦里的场景无非都是小时候的记忆,可没过多久,眼前的一切都开始莫名的着起火来,看着房子燃起的熊熊大火,我甚至能感受到自己就在那堆火焰里被炙烤,接着身边的人也被大火逐一吞没,他们面无表情,更没有丝毫的挣扎,只是一步步地向我走来,即使被烈火覆盖,也想让我加入他们。我想躲,可是马上全城都开始燃烧起来,就在人们扑向无路可退的我时,我才猛然惊醒,全身也早已被汗水浸透。这样的梦,终于在我被逼的喊出一声“离我远些”后彻底消失了,而梦醒后的我,终于能开口说话了。
“想不到你小子还是会说话的嘛,那为什么当初不搭理我?”
得知我能说话了,那个“毛脸男”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之前的几天陪伴我的只有脑袋边上的一个碗,上面还插了根吸管,每次我醒来,都能闻到碗里稀粥的味道。至于是谁在我睡着时添的,我倒是一点也不在意,比起作贱的饿死自己,干嘛不让他们给我个痛快的呢?
这次我终于看清了这个男人的样子,除了一张长满绒毛的尖嘴脸,他还有一双细长的手手指,就在他用手拍打我脸颊的时候,一股皮包骨头的触感使我尤为在意。
“废什么话?爷我现在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干脆点就给爷个痛快的。”
没想到被我这么一骂,男人反倒笑了起来。
“哈哈哈,你小子嘴倒是挺毒,张嘴就骂,也不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想死还不容易?卖给贩肉的,怎么着也能把你这几天的饭给抵了。可我接下来说的话怕你想死也死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