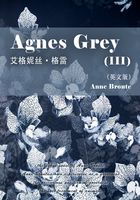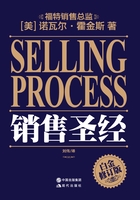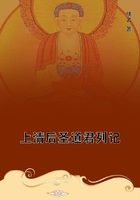又是一个风雪夜。
风冷冽,雪无情。
风雪之夜,那位于小山半山腰的新开的小门派内。
一间院子里,白雪已经完全覆盖了目及所有,不大的院子里,那总是干净利落的庭院地面上早已经似是一大张上等的宣纸,平滑,白洁。
“吱……”
一道门扉被推开,门板划过门轴的声音在寂静无声的黑夜格外刺耳。
一个肥头大脸,又矮又胖的光头走进屋子,也不见这人掌灯,却是在黑暗中抖了抖身子,雪花簌簌而落,却是有几片说巧不巧的正落在鞋面上。
光头自然是不会理会,只是悄无声息的走进内堂,步入卧室。
此时,床榻之上正躺着一个约摸十来岁的少年,紧裹着一床厚厚的棉被,面色红润,呼吸均匀的睡着。
此刻的宁静,却是那么冷寂。
黑暗中,光头走近少年,伸手出指在少年身上点了两下,倒也不见少年有任何反应。
光头退出内堂,走出房门,这次却是轻轻的带上了门。
站在门口,望着小院,光头又抬眼,看了看远处一片白皑,目光却是兀的有一丝道不明的精光闪过,之后却又是那无比坚定的眼神。
风急,雪大,好久没有这么急的风雪夜了啊,可是今夜是月圆之夜啊!皓月飞雪,这是一个注定不凡的雪夜吧!
月光明亮,雪片飘落而下,点点银光,正好是那月光借着雪花闪烁着。漫天的银光点点,确实让这风雪之夜好像多了一分梦幻奇异。
光头走进了另一间房,进门后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转身脱下外衣,退去鞋袜,吹灯,躺下睡了。
不知过了多久,宣纸般小院的地面上浅浅的印了一行足印,是很小巧的一双脚。
门开了又关。
“你得走了。”
黑暗中一道声音传来。接着便是那来人十分熟练的在黑暗中直接走向那放火折子的地方,点起了那盏油灯。之后那进入屋内的一袭红衣径直来到了那光头的卧室。
昏黄的灯光下,红衣女子的面貌自然是难以看的完全,但只是大概看去,便可推断出果然是一绝色佳人。
光头却不知何时早已坐了起来,就在那床榻之上。
“他很快就会发现你们了,得赶快换地方,就明天吧。”
红衣女子说罢,向床榻走近了一步,却也只是走近了一步,离那塌上光头还有四五步距离。或许也只是躲一下风雪透过来的凉意,亦或是,有些其他什么想法?
光头终于发声:“好。”
惜字如金。
红衣女子没有回答,却是瞟了一眼光头脱下的潮湿湿的衣衫。
“今夜又去了吗?”
“嗯,师傅他老人家交代的,我从未忘记。”光头离开床榻,却是连鞋子都没有穿,光脚走到屋中央,倒了一杯热茶,递给红衣女子。
“他总是这样,以前我就不喜欢他这样。”
红衣女子没有接过那杯冒着腾腾热气的茶,有些淡然无谓的说到。只是这话语内容却十分不符合她此时的语气。
光头缩回手,抿了一口茶,有一点烫,但也正是这烫茶才能给这处于这风雪夜的身子带来一丝暖意。
“红鸢,放下吧,那事怪不得任何人。”
随着一口热茶下肚,光头好重获新生般的舒展了一下肥胖的身子,转身对那红衣女子说到。
“可若不是他,你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还是不肯告诉我吗?”
似是经历过无数次心灰意冷,没有和女子吐出的词字相符合的气势情绪,有的只是平淡不带丝毫波澜的语气。不大不小的声音,刚好填满这间屋子,不亏一寸,不溢分毫。
一片静默,屋子里瞬间无人般寂静,死一样的寂静。
就这么凝固了片刻,光头终于再次发声了。
“你这不也随我逃亡了这么久了,既然当初选择了跟我流亡此时便也不要多问了。”
“你这算是利用我对你这份几十年的信任和习以为常的依赖吗?”
依旧是一片静默。
女子也不再多说,深情的看着一眼那赤脚坦胸,又矮又胖的光头。
“你都变成这样了,还要继续吗!那就真的这么重要吗!比…比我还重要吗!”
终于,女子似有些情绪激动,但依旧压着嗓子。
光头没有说话,走到窗户前,打开窗户,看着外面还在一刻不停歇赶着落下的雪片。
茫茫然,空荡荡。
“珍重。”
红鸢看着眼前这个人,也不再多言,转过身。原本打算就这么离去,可等到要迈出房间那一刻,她还是停下了。
“那件事,接下来我来做,就让我帮帮你吧,你太累了。”
女子出了门,又是在门外传来一句话:“这些年,我真的越发看不透你,但我不后悔,即使我们落得现在这么个惨状,至少我还在你身边。”
光头就在窗边看着那女子离开,背影如此娇小,身姿如此窈窕,如果可以,谁又不想在这寒夜里抱着那女子在屋子里火炉旁享受着温暖呢。
可是这凛冬不会因为你厌惧而褪去,那小青山,只能静坐在那里任凭这风雪吹打。
目光全无刚才那份坚定,光头目光空洞无神的盯着那倩影,直到女子的背影消失。
风雪更大了,好像要把这个季节所有积蓄的寒意在今夜彻底挥霍完全。那行足印也很快消失不见,像是从来不曾有过,庭院内又见那张宣纸。
大雪总是这样,有意无意的抹去一些痕迹,但在那看似无痕的表象之下,却鲜有人知,曾经这里有过一行足印,娇小而坚定。
那小小的火苗无风却微微抖晃摇曳了一下,也只是如此,便也回归如常了。淡淡的昏黄灯光只能照亮一块小小的地方,屋内大部分地方,竟不及圆月飞雪下的屋外明亮。
光头看着那烛火火苗,无风却左右摇摆,不能持定,低头微微蹙眉,似有深思。
一杯热茶又被斟满,就在那简陋的桌子上,热气白腾腾,袅袅上升。
安坐在桌旁,光头面无表情,一点一点的抿着热茶。
累吗?好像是很累,但却是没有退路,甚至都没有一条稍微便捷的小路。
光头终于是结束了他的沉思,看了眼那烛火,光脚走回床榻,光着上半身,下半身也只是穿了一只短裤,就这样四仰八叉的躺下睡去了。
飞雪凛冬,竟是如此睡法。桌上的蜡烛,烛泪已经顺着缓缓流下。
一个普通的风雪之夜,却在今夜显得尤其的不普通,那宣纸之上又被印上了一行足记。一袭黑色连帽长袍,似是一杆黑漆墨笔,在那张宣纸上又留下了些许痕迹。
隐藏在一袭黑衣之下,那人走过庭院,庭院当中,一脚落下,却不似之前,稍微停顿了一下,似有所察觉,但也随机不动声色的径直继续走近那间屋子。
那扇门,又开了。
此时,那一袭黑衣正站在呼呼大睡,鼾声如雷的光头床前。
光头却依旧酣睡,似是没有丝毫察觉到这袭黑衣的不请自来。
那灯光照亮了一小片地方,虽是也有些昏黄,但终归是带来了光明。
黑衣之下隐藏的人儿借着这光明坐下,看了眼那已经凉掉的半杯茶,又自己拿了个杯子倒了一杯,倒是还有些热气。
“也有快十年了,还是没搞懂你当初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黑衣人怡然抿着温茶,道。
饮完一杯,起身站立对着床上那肥胖的光头,左手一翻,手法娴熟,竟是一个精致小巧的皮革针包,一丝丝淡淡的药香从其中飘散而出。
皮革针包之上,金丝银线镂嵌着一个特别的图案,只是那人此时正背着那油灯火光,一时间倒也看不清是何图案。
包内密密麻麻的分放着两排银针,银晃晃的针身和尖锐的针尖倒是在昏暗中格外博人眼球,针尾竟不是寻常的金属制成,而是圆润光滑,微微泛光,似是由哪种不菲的玉石制作而来。
显而易见,这包银针绝非凡俗之物。
与此同时,那黑色的宽大袍袖下也伸出了一只右手。
那只手,手指白皙修长,手臂圆润纤细,手掌却似乎也有些小了,倒像是女子的手臂。相比于床上那光头,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云泥之别,也不过如此了。
针包被打开,一根排列在最中央的银针几乎同时已经在食指中指第一指节之间夹着。也不见那两根修长绝美的手指如何动作,银针却是已经准确的脱手飞刺在那胖子背上的一处穴位。
只见光头顿时双目猛睁开来,面露痛苦之色,趴在床上伸头出床外倏的是吐了一口黑血。
暗紫近乎黑的血迹摊在地上,空气中弥漫着咸腥的气味。
“你来了啊。下次先打招呼!哎呦喂,可痛死我了!”
光头一只手扶着床沿坐起来,挤眉弄眼的表达着痛苦与抗拒。同时,他还尝试着右手去拔下那根银针,却是碍于肥硕的身子,根本够不到,只得无奈的又趴在床上,似是等待着什么,而且还嘴里小声嘀咕不满咒骂着什么。
黑衣人不语,走近光头,拔下那根银针,又随手拿出一个胭脂盒大小的淡绿色细长小木盒,将银针在其上一个小孔处抽插了几下,然后便把那沾有了几不可见的些许粉末的银针放在了桌上那油灯安静的火苗上烤烧。
只见那火苗一接触银针便腾然大振,而且居然伴随着一阵淡淡的幽香,似丁香花那种味道。
不仅如此,那在银针上跳跃的火苗居然不是寻常颜色,而是黑色。
火烛的火苗的黄色接连的却是银针上的肆意燃烧黑火,甚是诡异。更诡异的是,那黑火虽然火苗漆黑,但却照亮了周围其他一切。
那银针烧了片刻,便是湮灭了,而那一直被黑火包裹的银针,此时却是银光泛泛,宛如从未用过。
黑衣人收起了那银针,又放在了那皮革针包里,之后也把针包收了起来。
“你来早了啊这次。”
光头还那样趴着,闭着眼像是在休息,毕竟现在已经深夜了。
“有事情找你,很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