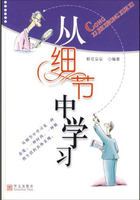仅是提及墨文卿,老嬷嬷便如临大敌,再三追问,她却又讳莫如深;倘若真是据实相告,为何无关紧要的只言片语便罢,旁的重要细节一概只字未吐;老嬷嬷有意隐瞒墨家自己的身世,老爷却又是知晓自己并非亲生……
如若自己真的并非墨父所生,那么生父究竟何人?母亲又在何处?
“母亲。。。。。?”墨文晏唇间低喃,她想起自己从小便做的那个梦,那个云髻簪花的妇人,那柔柔唤自己晏儿的妇人;一度曾以为,只不过是思念母亲过甚而发的梦,如今看来,确有其人也未可知。
墨文晏端着一心的疑虑和忧伤,借故乏了,支开众人对灯独坐良久,忽而脑中闪出一个人来,
“为何不去问问他?”暗骂自己的愚笨后觉,急忙套上披风,一瘸一拐挑着灯笼往那处去了。
墨文晏的住所本为墨府中最为偏僻的院子,平日里本就没什么人来往,又不受老爷夫人偏爱,因此配给的佣人也是极少,不过也正应了墨文晏静雅的性子,好在院子里还有个算不上精致的活水湖亭,是墨文卿怕小妹在别院住着太过乏味,而央求父亲所建,在墨文晏看来,却是小巧文雅的很。
此时正值深夜,又下着大雪,下人们早早睡去,墨文晏就着跳跃的烛火,沿着湖边深一脚浅一脚,双手冻得发僵,多时,来到别院邻着的一片荒了许久的园子,平日里瞧着都是一片颓败的模样,好在此时白雪皑皑,在黑夜的迷蒙里,一直延伸到远处。
墨文晏伫在雪里,寒意刺透鞋袜侵进骨血里,心中暗骂那人为何要将见面的地方选在这处,在手里哈了口雾气,从怀中掏出一只骨笛凑在唇边,想要挤出一丝气息来,动作因寒冷而显得有些笨拙,试了多次,才响起并不响亮的鸟叫声来。
“咕咕。。。。。。。咕。。。。。咕咕咕”墨文晏竖起耳朵搜查着四周的动静,没有回信,想是声音太小的缘故。
“咕咕。。。。。。。咕。。。。。咕咕咕。。。。”这次洪亮的多,可仍旧没有回信。
。。。。。。。。。。。。
“咕咕。。。。。。。咕。。。。。”
一次,两次,三次仍旧没有回音,她以为今夜是等不到他了,想要试最后一次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如此着急寻我,可是有什么事?”声音低沉压抑,不伦不类,似人非鬼,在这沉静的夜晚显得有些惊悚恐怖;
墨文晏如旧,背对着他。在她八岁的一个黄昏,春末夏初,大雨如注,被主母罚过的她偷偷躲在别院里冒雨哭泣,他悄悄然出现在身后,递给她一把伞,雨水震的双眼刺痛,只模糊的瞧见他身姿挺拔,一身玄色剑客扮相,脸上还同样覆着玄色的面具,那是她第一次遇到这个神秘人;
他们曾约法两章,一:墨文晏不得问他是谁。二:墨文晏不得看他真面目。从此,以骨笛为信,只要墨文晏有求于他,只要在这初见之地吹响骨笛他便会来,墨文晏则只能背对他。
“你曾说过,你一直守在我身边。”墨文晏顿了顿,显然身后之人对她的话不置可否,便继续说道:“既如此,那么你定知道,我是谁。”
话毕,她似乎感到身后的人有那么一刻的震惊,而后他向自己走近几步,悄无声息。
“我自然知道你是谁,可你却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来问我了,我曾以为你永远不会再来问我,我想那也是挺好的;”他的声音夹带着几乎不可察的震颤,不知是欣喜还是悲伤。
“你是配享无上尊崇,帝后爱之如明珠,当今昭国唯一之长帝姬,仪同藩王,贵及太子所不能比!!!”
身后之人一字一句,掷地铿锵有声,极其恳切却又小心翼翼。
忽而犹若五雷轰顶,魂游身外,确切的突然的沉重的痛感自心口涌出,五味杂陈一拥而上;无法确定的想要知道的身世像一本年久的天书,被慢慢一页页翻开。。。。。。
“那一年,宫中动乱,皇后娘娘为保护你,将不过五岁的你拖她的心腹王仲朔抚养,并为此将他升为幽州都督,可你母亲不幸罹难,他转而便将你送至墨府,丝毫不加呵护,背信弃义。我花了多番功夫才找到此处。”
“那我父亲呢?”。
“你父皇。。。。。你父皇他,你该听坊间说过的,他呆傻无知,从那后他便做了齐王的傀儡皇帝,却仍旧不自知。只有一日,他给了我一盒金饼,托我找到你。”身后之人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怅惘,“他说王仲朔是个奸险小人,得利忘义,不择手段之辈,必不会善待于你,实则那时,他已然久卧病榻,沉珂在身,可他。。。。。竟还记得你”
听到此,这页遥不可及的天书,似乎和自己产生了不可抹去的联系,这个世界还有自己的亲人。
“他还活着吗?”
“活着。。。。。。。”
“他好吗?”
“却又像死了,他做了十余年傀儡皇帝,世人只知齐相,而已忘却那疯癫人皇。”
“他在哪里?”
“京都,你去不了,即便去了也无用;你不过是个柔弱的女子,独身一人,甚或许没到都城,便已被流匪了了性命。”
“你带我去可好?”一切了无头绪,墨府如同一张细致的网,让人挣扎着想要逃开,可是背后的人一阵沉默,安静的只剩雪花落地的‘潄潄’声,她以为他已经走了,转身间,一阵狂风吹过,刮走手中那唯一的烛火,他那玄色的身影在夜色间和黑暗融为一体,显得异常高大伟岸如一颗青松。
“马踏积雪跃墙头,乘风十万到京畿,除却此,你我凡人并无他法。”很久,他黯然说道。
“也罢。”墨文晏见央求不住,只得无奈又道:“左右不过是个落魄的公主,并非男儿身,为何那王仲朔那般急迫的要将我接回幽州?”
“只因那‘护身符’!此物可保你十六年平安,但到底是何物,待你及笄之后,自会现世,鄙人也是不知。”
能想出这样办法的,除了她之外,世间便再没有了。
她是当世的绝代芳华,哪怕过了这十年,香消玉殒的她也仍旧为当日钦慕者所回忆,哪怕只是远远的看一眼,佳人在侧,如沐春风之感犹存;
她也是世人乃至千秋万代后为世人所唾骂的妖后,容貌矮丑,为人善妒,玩弄权柄,致使国家动乱民不聊生,早在高祖立国时,便有预言,盛世将毁于胭脂女子手中。
但看着眼前这个年尚不足16的女子,她战战兢兢,一如当年的她,盛世时她无奈封后,乱世时,亦无奈成了人们口中的妖后。临死之际,又只得以最危险的方法保护爱女。
“你可知,你眉眼间像极了你母后,真不知那嬷嬷看了作何感想。”黑影中的男人说道,语气极为平淡,细细品读,又有他意。
“世人都说她是妖后。”
“你信吗?这样的乱世,最是人心不可信,何况人言,哪怕是,她也是你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