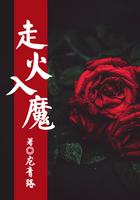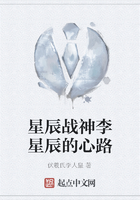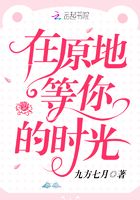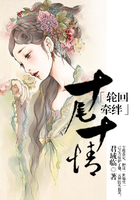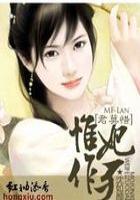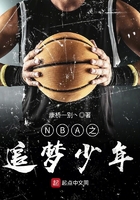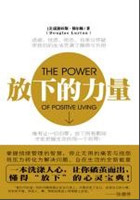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我回自己的病区己的东西,被付老师看到,这使我有幸第一次以专业人员的身份进了社区。
付老师是我们科的副主任,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临床经验丰富。我们年轻的医护人员都称他为付老师。付老师是科室里为我指定指导老师,负责我在轮岗试用期间的各方面指导。无论是转岗学习目标、转岗进程安排,还是学习结果考核都由付老师直接安排。不仅如此,据说按医院惯例在我取得独立坐诊资格前,付老师都将是我的责任指导老师,也就是说在将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要向付老师学习诊疗的实践知识和经验。这些日子里我经常找付老师讨论一些医院转岗期间遇到的其他科室里疑似有精神症状病人的情况,付老师会给我一些建议,比如,如何与这些病人沟通,用何种非药方式缓解病人的精神症状。和付老师相处的几个月里,我感觉之前课本里学的很多知识已经可以和疹疗实践联系到一起。
今天被付老师叫住的原因是医院所在的社区向我们科求助了。社区的王医生前些天来我们科室,想要咨询精神疾病初步判断、日常社区干预和辅助治疗的问题,这样他们可对社区里的几个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有的放矢。付老师接待了王医生,由于付老师日常工作很忙很难抽出大块时间一次性解答王医生的问题,所以付老师和王医生约定明天休息时去社区专门解答王医生的问题。当付老师知道我明天休息,要求我也参与这次“义诊”。
第二天下午在约定的时间我去社区办公室,路上恰好遇上师兄刘医生。刘医生也是付老师指导的学生,也被付老师要求来参加社区的“义诊”。当我们被让到社区的会议室时,付老师和王医生已经在闲聊了。王医生见我们到了,把社区的袁主任、负责治安的吴警官、负责居民事务的方干事请来,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对社区里几个有显著精神问题的人开始了隔空“义诊”。当然这种“义诊”并不能对“病人”进行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我们只能根据社区医生描述的症状对“病人”的病症进行初步判断,给社区开展工作的方法提供一些针对性建议。
王医生把社区里的几个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的情况依次作了介绍。他们中有孤寡老人拒绝接受帮助的;有喜欢捡拾可回收物堆在家里直至对邻居产生不良影响的;有经常幻想引起家庭不睦的。他们都是没有什么亲朋好友的中老年人,除了一个是夫妻同住外,其他都是独自一人居住。按照一般发病率推算,在这样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社区里精神疾病患者肯定不止这么多,王医生介绍的这几个人是需要社区提供帮助或是对他人有攻击行为被投诉到社区的。付老师根据介绍的情况对他们的成病原因、表现出的行业特征一一分析。付老师和刘师兄一起把和日常交流沟通注意点做了说明。虽然知道他们几乎没有可能去专业精神疾病医院或科室就诊,但我们还是提出这样的建议,因为只有到专业医疗机构的就诊才能得到针对治疗,缓解症状。
王医生介绍的其中一个疑似患者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个人很在像那天我看到的那个吵架的老太太。她的情况大致这样的:
吴某,女,80岁,身体基本健康,可生活自理,文盲。有退休工资,但偏少。
吴某丈夫早故,育有三子,但与子女极少交往,基本为独居状态。近来其长子有时会住在吴某处。吴某日常无特殊社交活动,仅每月定期与社区里的几个老伙伴人去寺庙烧香拜佛。
吴某搬进社区后,长时间与几户特定人家发生争执,称这些人家偷盗了她的钱物。已有3-4户人家由于这一原因搬离社区。这些人家有她曾经的同事、有她的邻居,经了解这些人家都和她有过密切接触史。
袁主任还专门对吴某与一些与邻居发生争执的过程作了介绍。
付老师根据这些介绍,给出了初步分析结果。考虑到吴某搬到这个社区时已经60多岁,早期的情况社区并没有确切知晓,所以只能按老年痴呆症的方向推测。吴某可能早年有过盗窃类不良事件的刺激,比如,因为盗窃或被盗窍受到严重身心伤害,年老后由于脑功能衰退,有了现在的表现。从行为表现看,有些像认知障碍,与年龄相关的可能性极大。由于吴某与他人的争执理由基本是自己的钱物被偷窃,所以日常工作人员与她接触时可以经常性帮助她强化记忆自己拥有的财物与日常花费,必要时可以由社区协助她管理财物。
后来的事情表明,作为精神疾病医生,在没有全面了解病人情况下,最好不要轻易下诊断结论。这回就算是经验丰富的付老师给出的建议也把袁主任坑害的不浅,不过这是后话。
“义诊”结束后,我被指定为医院精神疾病科和社区的联系人,后来我又去过社区几次,也见过这几个老人,和他们也简单交流过,当然包括吴老太。不知是注定还是巧合,吴老太成为我工作早期接触最多的“病人”。由于最终也没能对她开展正式治疗,所以她经常成为我的对照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