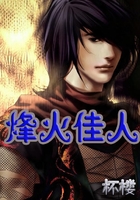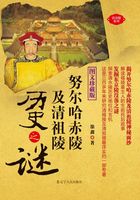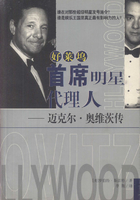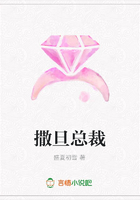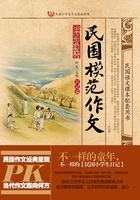冷风呼啸,廉颇站立城头,望着城外飘扬的黑旗,默默地呼出一团雾气。
震天的鼓声自秦军而起,沉闷的马蹄声和步伐声随那黑线逐渐响亮。
廉颇身旁的小卒紧握着弓,也不知是不是冬日的缘故,冷得这小卒的手有点抖。
廉颇拍了拍小卒的肩头,慢慢地看着秦军。
城外,密密麻麻的秦军拥着巨大的云梯缓缓推进,百步之隔,披着牛皮的轒轀被十数步卒推着碾过雪层,留下长长的车痕。
“好大的手笔!”
廉颇身旁,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幽幽叹道。
廉颇笑道:“相国可是惧了?”
“我倒是不惧,只是这大赵,有劳将军了。”
廉颇看了看那老人,那赵相平原君赵胜。
虽本是赵国公子,早几年却是连友人都保不住,就连如今,却是以半百之身出使楚国,虽胜而归,可其中艰辛,无人可知。
“相国安心,颇定死守邯郸。”
“如此,有劳将军了。”
······
楚军。
“邯郸如何?”
营帐中,刚接过兵印不久的项承,轻声询问道。
“将军,秦军已攻城。”
顿时,帐中气氛凝结,毕竟他们要面对的可是秦军数十万,而他们却只有十数万援军罢。
“大王可有回信?”
虽说项承早已知道结果,越人连年进犯,大楚能调出这十数万援兵,已是强弩之末了,但毕竟世上还是有奇事发生的,虽说几率很小。
“无回信。”
果然如此。
“传我命,休整军阵,加以操练。”
“加以操练?”营中一少年小将问道。
项承没有理会少年小将,只是环绕看了四周的将领,道:“知晓了吗?”
“领命!”众人齐齐应和道。
而后,众人纷纷退出营帐,唯剩那少年小将。
“父亲,我们不是应该······”
项承看了少年小将一眼,沉声道:“军营内无父子,你当称我什么?”
望着项承严肃的表情,少年小将赶紧改变称谓,不情不愿地喊了句“将军。”
“记住,军中之纪,一事不可疏忽大意。”
“是是是。”少年小将垂头应和道,似乎这顿臭骂早是家常便饭。
项承无奈地看了下少年小将,心中坚定了带他来军营的初衷,随后便看着手中的毛皮地图,不再理会少年小将。
少年小将也不泄气,跑到项承身旁,咳嗽了两三声,摆出一副认真的模样。
“将军此处出楚,是为援赵御秦也,何为驻军郊外,加以操练?”
项承没有搭理少年小将,只是把脸转过一旁。
少年小将继续跑过另一侧,开口道:“秦军数十万,赵军十余万,若我军不出击,邯郸可守几日?若邯郸不守,我等出兵又是为何?”
“且秦军不知我军,我军可突袭秦军后方,加以赵军前后夹击,秦军可破矣。”
项承放下地图,饶有兴致地问到:“你可知,秦军攻城之将何人?”
“王龁。”
“长平之初,王龁领秦军对峙三年,赵接连大败,赵军裨将领赵骑三千袭秦军,秦军斥候歼之,斩裨将。”
“今日我军十余万人,秦军能不觉乎?如此做法,我军必败之。”
少年小将愣了下,还没缓过神来,项承继续说道:“邯郸守将是为廉颇,廉颇守城,为当世之冠,以十万兵卒御秦军数十万,且赵人视秦人为狼虎,当为国丧之军,数日可不败,而数日,足以成事。”
其实,可能不需多久,十天便成。
当然,少年小将听的迷迷糊糊。
项承也不点明,毕竟这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燕儿,你要知道,我们是楚将,我们当要为楚军着想,为之将者,当为其国,以后要记住了。”
少年小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前面说的什么没记住,倒是后面一句“为之将者,当为其国”牢记在心中了。
———————————————
邺地
“报,信陵君求见将军。”
晋鄙也不在意,摆手说了句:“见”。
不一会儿,有人从营帐而入。
晋鄙向带头者拱礼道:“不知公子为何事而来?”
“兵事。”
魏无忌取出兵符,交给晋鄙。
晋鄙接过兵符,恭敬道:“公子先在营帐中歇会,我去取兵符相合。”
“无事。”魏无忌笑道,“军中纪律,当不可违。”
“哈哈,谢公子体谅。”晋鄙说着,招呼了些近卫服侍魏无忌两人。
等晋鄙走后,魏无忌遣散了身边近卫,笑道:“尔等皆吾大魏之勇士,应当我服侍你们,怎么能让你们服侍我等呢?”
“不敢,公子乃君子矣,吾等乐为公子效劳。”
虽说驻军边境多年,可信陵君贤明的名声早已遍布天下,以致边境之军,无一不识魏信陵。
不久,晋鄙拿着另一兵符匆忙赶来。
“兵符无误,可发兵矣,只是······”
魏无忌站起,问道:“只是什么?”
“出兵之事,当有礼使,为何只是公子与食客而来?不如待我与魏王相报,待礼使前来,再出兵可否?”
说罢,晋鄙举着手望着魏无忌以及魏无忌身旁的大汉。
“晋将军乃我魏之良将,为我魏操劳至此,无忌拜谢将军。”
“公子严重了。”
晋鄙连忙低头弯腰拜谢。
这时,魏无忌身旁的大汉取出袖中藏着的四十斤重的铁锥,一椎砸死了晋鄙。
“只是无忌对不起将军了。”
而后,魏无忌取过兵符,走出营帐中,集结士卒。
“今夫暴秦无道,举兵攻赵邯郸,是为大罪矣,若我等袖手旁观,明日我等皆为秦囚也。”
说罢,魏无忌取过兵符环绕四周。
“若军中有父子者,父回家中;有兄弟者,兄回家中;无兄弟者,回家奉养双亲。”
而后,得精兵八万,越过边境援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