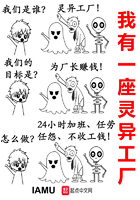今晚的灯光似乎特别亮,零零散散掉到特蕾西的脸上,映得如浴水葡萄般的瞳仁也透亮。
不远处,阿东被吓了一跳,但看清楚来人后,又笑得贼眉鼠眼了:“这不是忍忍西吗?怎么,土拨鼠也敢出洞了?”
夏夜风猎猎,吹得少女垂在额角的茶色发丝纷飞,眼前视野被干扰,却不影响其目光万分坚定地射向远方,好像可以斩破黑夜的利剑;她含笑着回敬道:“你见过如此比你人还大的土拨鼠?”
虽这么笑说着,当面听着,她心里终归有些懊恼,面上却是不显;就好像一本书,书封看上去很是高大上,可实际上它的内容幼稚得好比童话。
她骂他又矮又小又眼瞎,那小家伙脸色自然不好,笑容凝固了,见那面部的肌肉以一种僵硬的姿态呈现着,而怒道:“你他……”
她打断他,面带微笑地堵上他那张脏话连珠的嘴道:“还有,你和你妈一样软弱无用、讨厌嫌恶、令人反胃!你们全家个个都是无赖,叫人作呕憎恶、恶心抵触!”顿了一下,她杏眼迸射出轻蔑而不屑的光芒,冷声,“所以,以你的分量,没有资格对我们家说三道四!”
明眼人都看得出她此刻皮笑肉不笑;阿东没她好沉得住气,却显然是不承认的,但盖对不上话来,故一边气得直跺脚,一边扯着公鸭嗓大声嘟囔道:“沈诺西,你瞎说!你放狗屁!你全家……”
特蕾西冷声道:“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阿东的声音戛然而止,他脸涨得通红,还一心想要反击;观他东张西望一番,约莫看到几步之遥外有一块粗糙的大石头,便眼眸一亮,一边屁颠屁颠地跑过去,一边扭头喝道:“你别跑,吃我一招!”
特蕾西眨巴眨巴眼,无语地看着他,内心猜测:一方面,到底是低了一个脑袋,阿东这么喊是为了给自己壮壮气势吧;另一方面,她莫名感觉他生怕她跑了似的……而等他跑到那石头跟前,只见他奋力一踢,那块石头倒是有脾气,非但没有飞向了特蕾西——下一秒,阿东就痛得抱起自己的脚来了个金鸡独立,失声大叫:“哎呦!”
一伙人看得目瞪口呆。
顷刻,特蕾西嘴角微扬,似笑非笑。若不是阿东长了一张欠揍的嘴,她毫不怀疑她会被这个邻家小弟弟可爱到。
又见,阿东懊恼地瞪了一眼那顽石,然而他脚下石竟然纹丝不动,似乎在无声地嘲讽他自不量力;特蕾西脑中灵光一现,佯装好人心肠,学着他的语气笑眯眯地替他接了话:“哎呦,好丢人现眼!”
这一激,阿东委屈得眼泪差点掉下来,可就是不肯服输,不然太没面子了——他可是“男子汉大丈夫”啊!一咬牙,他硬着头皮搬起那块石头,跌跌撞撞地往前冲了几步,对她喊道:“我和你拼了!”话音刚落,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把石头举到胸前,奋力朝特蕾西抛去。
特蕾西睁大了眼,勾唇判断着:这石头,目测斤量不小,要是真砸中人,杀伤力应该还蛮大的……不过她一点也没有躲的意思,甚至一丁点也不想给他面子,眸里依然挂着笑意,目光不闪。
天地之间,她的神态自信而夺目,黑葡萄一般晶莹剔透的紫罗兰色眼睛这刻美得动人,寒得骇人。
电光火石间,那石头已经落到距离特蕾西几步远的地方,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似乎有什么刚好滚到了她脚边,她低头看了眼,忍俊不禁地“嗤嗤”笑了两声。
原来那可怜的石头不仅没有砸中人“立功”,还自碎了一块小石子;她都替这石头疼了三秒,心中只觉得好笑:嘿,就料他有胆也没这个力,滑稽得像跳梁小丑!
再看对面,暗夜下的阿东好像面红耳赤然,闻他朝自己喊道:“我认真的!”依着轮廓,想来他已经没脸去瞄同伴看他的眼神了。
特蕾西轻笑了一声,笑里意味不明,玩味道:“啊,这样,值得敬佩。”
只见她扶杆直起身,亮出藏在掌心中的水果刀——看得阿东寒毛倒竖。他身边的小朋友也害怕极了,眼睛一眨一眨地盯着她左手中明晃晃的刀片,生怕她下一秒会一言不合、杀人灭口。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一时间,只有夜风在呼啸,摇得路灯灯光影影绰绰。
只闻,特蕾西像笑又不笑道:“阿东,别来无恙。”
阿东吞了口唾液,外强中干道:“你要干嘛!”
“我不干嘛。”特蕾西笑里藏刺,扬声悠悠道,“喂,你们信不信,十息之间,我能让阿东头皮开花。”
那群小家伙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不该回答她的话;而她也不是真的要问他们。
阿东挺了挺胸,气势汹汹说:“你敢?你以为你谁啊……”
特蕾西已经瞄准他头顶的路灯——准确地说,瞄准的是悬着他头顶路灯的路灯丝,分明极细的一根,她掷出刀子。
这路灯几十年前就在,灯丝是比较老式的太阳能装置,平时也没有人注意,这会儿却成了众人的焦点;阿东盖只看到了她朝他抛刀子,心里害怕极了,吓得一霎闭了眼、抱住了头,色厉内荏然。却半天没动静,他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确认一番,以为无事后,又嬉皮笑脸得意道:“你丢哪儿去——了,呃……”就在这时,头顶灯光不给面子地一闪,暗了下来,突生异样。
不安从心底油然而生,阿东怔怔抬头仰面;恰恰这时,黑黑的一坨灯泡,罩了下来,刚好盖到他脸上;顿时,他头破血流,滚烫粘稠的血液流过脸颊。
特蕾西看完这一出好戏,心里毫无意外,也没泛滥什么怜悯之心,只是佯装无辜地摊了摊手,怪可爱地歪了一下脑袋。没有任何犹豫,她不假思索地钻进了漆黑的夜色中,潜入黑夜。
在约莫两三秒后,阿东号啕大哭。小人儿肉乎乎的一坨,很胖,跌坐于那冰凉的地上就像个树墩一样,就死活不起来了,哭得惊天动地的。
他相好的几名小弟皆不知所措,又呆愣几秒,下意识地用目光去寻特蕾西的身影——她到底比他们大,关键时刻还得靠着她;可人家哪里愿意留下和他们“谈心”,早就跑得没影了。
哭声是会被感染的,于是乎,小的们便一个个低垂着脑袋,一句句地呜咽,越哭越委屈。
特蕾西溜地飞快。她回到家,把门锁上,暗吁一口气。她可不想摊上这锅热气腾腾的麻烦,阿东顶多不过破个相,可这小孩闹起来却是无法无天的;却也知道,这事与她脱不了关系,迟早是要刚一场正面。
每当在这种时候,特蕾西总是想着:她还有一个叔叔――沈德。
德叔明面上是她世界末日中仅存的一缕温柔。来自昔日的温暖总能给予她安慰,托予她活下去的勇气。
她不能再没有这个叔叔――对特蕾西来说,他就是第二个父亲!
确实,德叔对特蕾西的关照是绝不亚于一个义父的。比如,前一阵子,他就三顾茅庐来接特蕾西去他那同居,却都被特蕾西婉拒了。盖因为害怕被渔村里的人议论此事,德叔便没再坚持。
特蕾西是很有主见的,她也相信德叔的品格,之所以拒绝,是因为舍不得朝夕相伴生活了九年的小屋子。虽然这个想法天真了点,但毕竟她现在是屋子里唯一的主人,且对小屋子——包括小屋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有感情的。这一朝之别,说得好听只是去寄人篱下一段时间,却是心知这一走以后怕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吧。
和爷爷一起生活的日子,她很快乐,也很怀念,那是她的人间;她感谢小屋子给予了这段过往九年的庇护。倘若她离开了,过往的所有都会清零,淡去。
当然,这是她对外的说辞。
她自然不会说:实不相瞒,这是一个有“秘密”的小屋……
再说了,德叔的生活怕也不容易;特蕾西打从心底害怕再被这个与她有点亲情的叔叔“嫌弃”,故她一点不想给叔叔添麻烦,也不想靠着他苟活。
而且,她也不是一无是处啊,她两岁就会打扫卫生,三岁就会做饭,四岁就会洗衣……粗略还是能够自理的。只要德叔能给予她一些所谓“亲人”的关爱,她是绝对能够在宜春里铁着头皮生过下去。特蕾西想要向大家证明:她还有“亲人”,她可不是无所依赖的孤女!
有时她会告诉自己:她也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生活!她时常会想着,或许对于德叔来说,自己也是他生活的希望啊!安吉尔虽说只是失踪,但这种下落不明极有可能就代表着死亡――德叔不可能不心知肚明!哪怕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安吉尔被找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也不大可能会白玉无瑕的再次出现在德叔面前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特蕾西想要体体面面生活的斗志更加强烈了。因为她不仅是在为自己而活,还是在为另一个不幸的人在活!哪怕眼角含着泪,昂起头来,她却还是那一副自豪的笑脸,绝不屈服!
可是,就这样坚持快活了几日之后,特蕾西又敏感的想到:德叔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累赘?随着时间推移,特蕾西更加焦虑了:德叔会不会因为安吉尔的事怨上自己呢?
毕竟……安吉尔的事和她好像也有一丝关联――安吉尔也许就是在给她送那些“不寻常”的信件的途中失踪的……如果没有那些不寻常的信,安吉尔会不会就平安无事呢?
特蕾西有些自责……突然感觉好像自己的责任还挺大的……唉,现在的她多么希望安吉尔还能和爷爷去世不久的那会儿一样,为自己送来一封又一封神秘的邮件……
坐回床沿,特蕾西又想到了那个叫“罗希”的女人。
她是谁?
特蕾西的心又开始乱了,她的杂念太多了……
残破的窗子,昏暗的内室,整洁的茶几,以及茶几上削了半边皮的苹果。
窗外渐渐嘈杂了起来。
她盯着那个上身黄澄下身红彤的大苹果发了好一会呆,突然头痛地想到一件重要的事——她现在务必去找回那把水果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