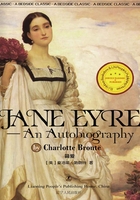那年正月初九,才立春。
季节虽到了,气候却没有到。往年黄荆山的人们,三月便都甩掉了破棉袄,任暖得发痒的日头在臂膀、胸脯上蹭来蹭去。可那年三月,破棉袄谁也脱不下,手伸进水里,冷得生疼。往年三月,只要下一夜雨,第二天就有满山的竹笋破土而出。正闹春荒的人们,上山去把竹笋抽了回来,或放到锅里煮,或拿到城里卖,换回粮和油,也就再饿不着了。可那年三月,雨也多,但那竹笋总也不肯冒出土来。
那雨落得乱糟糟的,路上全是泥泞。雾罩在山头上,越压越低。山峰和岩石藏在雾中,瘫软了一样,如饿汉,再站不起。挨饿得太久的麻雀,立在枝头上有气无力地叫,食物仍找不见。漫长的白天,山上山下到处都是挖野菜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挎着模样相差无几的竹篮,面色都很憔悴。那竹篮只装了少许野菜,声声叹息早已把它装满。他们一边咒骂着那迟来的气候,一边望着烂泥地发愁。
春枝抬头看了看天,天黑得吓人,毛毛细雨又飘了起来。她叫了一声,“腊梅——”那声音原来很壮,现在却虚了,还有些颤。
腊梅是她的老二,在远处应了一声。
“天要黑了,回吧!”
“我篮里还不多哩!”
“算了算了,回吧。”
腊梅挽着半篮野菜,走了过来。她十五岁了,个头和春枝一般齐,只是很瘦,很弱,仿佛一阵风也能把她吹倒。她看了春枝的篮子,不好意思地说:
“妈,又没有你多。”
“行了,够吃两餐了。”
“妈,你头晕不晕?”
“你又头晕了?”
腊梅脸有些红,像是自己说漏了嘴,连忙掩饰自己:
“我才不晕呢!每天我吃得最多。”
春枝心头针扎似的疼。
“碰上这年头,除了喝糊子粥,还能吃什么!”
母女俩走到溪边,把那野菜一棵一棵地洗净,回了家。
八岁的浑子放了学,带着六岁的妹妹玉玉在门口玩。浑子见妈妈和姐姐提着菜篮回来了,扒着篮子看,玉玉也扒着篮子看,还伸出那只小手,在菜里翻。春枝把玉玉的手推开:
“菜洗净了,你手不脏么?”
“我饿,妈!”玉玉把手收了回来,没有从篮子里找到吃的,很失望的样子,两只眼睛哀哀的。
“妈这就做。”
浑子凑了过来:“做么子好吃的,妈?”
“煮粥。”
“又吃粥,一泡尿就屙了!”
春枝心里也烦,举起火钳,浑子也不动。春枝看到儿子瘦精精的,一张孩子脸,黄黄的,那火钳便打了折扣,没有落到浑子的屁股上去。
“你作业做了么?”
“没做。”
“没做作业,你还想吃么子?先做作业,做好了,粥就熟了。”
“我上了一堂课,肚子就饿了。妈,明天中午煮一餐饭吃,好不好?”
春枝横了浑子一眼,“做作业去!”
“妈,你答应我嘛!”
“过几天,粥都没有吃的了,你还要吃饭!要吃饭,就要好好读书,像你哥一样。”
树黑哥读书,考上了师范学校。连户口也转走了,吃了商品粮,一个月二十七斤呢。在汪仁公社,提起树黑,没有几个不晓得的。
“那孩子聪明过人,不读高中亏了。”
“读了高中,读大学一定没问题,去不了北大,去武大那是肯定的。”
“他家里负担不起。”
“所以他考了师范,饭解决了。”
“饿不死,又读了书,这才叫聪明呢!”
浑子做作业去了,要是读书能把肚子读饱,读得每天有饭吃,像哥哥一样,那真好!
春枝舀来半升米,简单洗了洗,倒进鼎罐里。
腊梅用水瓢往鼎罐舀水。鼎罐快满了,这才住了手。
“再舀一瓢,姐姐!”玉玉说。
“够了。”
“我要吃好几碗呢。”
“好几碗也够了。”
这时候,廷秋回来了。他在门口用力跺着一双泥脚,叫着:
“浑子,浑子!”
浑子听到爸爸的声音,连忙放下笔,几步跑出来,“爸带好吃的回来了?”
“当然!”
廷秋进了屋,叫浑子往箩筐里看。浑子见箩筐里有四个红苕,连忙拿起一个。
春枝见了,面带喜色,“哪里弄来的?”
“你管哪弄来的,吃就是了!”
春枝把浑子手中的苕接过,脸吊起,说:“你三十多岁的人了,没犯糊涂?你是生产队的粮食保管,偷吃大伙的粮,你良心狗吃了!”
“莫放你娘的臭屁!队委会的决定,苕种留得多,多余的一家两斤,分了,我什么时候偷吃了大伙的粮?你嘴要生蛆呢!”
春枝用手擂了一下廷秋的胸脯,露出笑脸,“人要行得正呢,这样,吃才吃得舒坦。”
“妈,放到鼎罐里煮?”
“煮吧煮吧!”
腊梅把苕洗净,春枝用菜刀把苕切成块,放进鼎罐。玉玉和廷秋围着火炉,等粥吃。腊梅往灶孔里添柴,春枝在炒菜。那菜泡起一大锅,一会儿,便塌了下去。能盖盖了,春枝把锅盖盖上。腊梅加了两把火,便不再烧。春枝揭开锅盖,放了盐,滴了几滴油,又把盖盖上。
粥也熬熟了。
浑子的作业早就做完,他把煤油灯放在碗柜顶上,门没关严,风吹进来,灯苗忽闪忽闪的。浑子去把门关严,并闩了门。
“这么早,闩么子门?”春枝说。
“风打灯哩!”
“把门打开!”
“天不是黑了么?”
“黑了也要打开!又不是吃海参燕窝,要躲着。”
浑子不明白,也就不动。玉玉更不明白,更就不动。腊梅大些,知些事,晓些理,她去把门闩拔开了。
廷秋说:“熟了?”
春枝说:“熟了。”
“提起来吃吧?”
“吃吧,细伢早饿了。”
廷秋站起,把鼎罐从挂钩上取下,在三角架上放平。春枝叫三个孩子围着桌子坐好,廷秋见伢们鸟儿一样,叽叽喳喳,独自闷在一边,抽那袋水烟,咕咕嘟嘟响。
浑子和玉玉眼睛盯着鼎罐。春枝一手拿碗,一手拿汤瓢,在盛粥。那粥很稀,见得到人影。春枝先跟廷秋盛,在鼎罐底捞起几块苕,那碗便有了些分量。她端到廷秋面前,廷秋接过,放在桌上,“先冷冷,我把这袋烟抽完。”
那碗冒着热气。浑子的喉头蠕动着,咽了口口水。玉玉也耐不住,也吞了口口水。腊梅不动,肚子咕咕叫了好久,她没说。她晓得,说了也没有用,话也不能当饭吃,填肚子。
春枝在鼎罐里满世界地捞,那三个碗上好歹都盛了几块苕。苕吃了,经饿些。她最后给自己盛时,一块苕也没有了。她夹了些菜,坐在一边,不声不响地吃。
浑子和玉玉把粥喝得一片山响。
“吃慢些,别烫着。”春枝说。
那声音便小了些。
腊梅数了数,自己碗里有四块苕。她吃了一块,那苕好甜好甜。她喝了一口粥,正要吃第二块,见妈妈一个人坐在一边,料定她一块苕也没有。她端着碗走了过去:
“妈!我不吃苕,吃了苕我光裂心哩。给你吃了吧!”说完,就往妈妈碗里拣。
春枝挡开,“你这个丫头,么搞的,我吃了更裂心呢,吃了苕我就不舒服,你又不是不晓得!”
“我真的不晓得!”
“这不晓得了。”
“不!妈,你吃几块!”
“我不吃。”
浑子连忙插嘴,“姐不吃,给我吧!”
腊梅正要往浑子碗里拣,春枝将她推开,一巴掌朝浑子胳膊打去,“你那么猴相,又不是没给你盛!”
浑子胳膊一晃,拿着筷子的手一松,夹着的一块苕掉在了地上。他“哇”的一声哭起来。
廷秋坐在一旁,脸色很暗,“你看你,犯得着打孩子么?”
春枝白了他一眼,“你别护他!这伢太猴相。”
“不就是个孩子么!”
“从小看大呢。”
“从几块苕看起?”
“……”
“别嚎了!”廷秋一声吼,浑子也止住了哭。
玉玉趁浑子哭的时候,已经把第二碗粥喝到了肚里,盛了第三碗。
浑子喝了四碗粥,肚子有些胀,便把碗放下了。又觉得并不饱。但鼎罐已经空了,这时他见到掉在地上的那块苕,便迅速伸出手去把它捡了起来。苕上沾满了灰,他放到嘴边吹了吹,就要咬。
腊梅说:“脏呢!”
浑子说:“不脏。”
玉玉说:“你要怕脏,就给我,我不怕脏。”
腊梅舀了半瓢水,浑子将那块苕洗了,捏在手里,一时并不吃。
玉玉说:“哥,吃了吧!你不吃,放到明天上学再吃么?”
“明天礼拜天,我不上学。”
“那现在吃了算了。”
浑子看着玉玉,玉玉歪着脑袋,盯着他手里那块苕。那块苕又薄又小,却充满了诱惑。玉玉很巴结地看着浑子,浑子刚读过课本上《孔融让梨》的故事,犹豫了一会儿,狠了狠心,将那块苕掰成两半。
玉玉说:“哥哥真好!”
“你有了,可别不给我。”
“还会有苕么?”
“今年怕是吃不上了。”
洗了脚,孩子都上了床。早早地睡,这是山村最大的自由。既省了油,又养了身子骨。没有一家不是这样。
廷秋提了一只空粪桶,放在屋角,那是准备夜里大家屙尿用的。睡到半夜,春枝总要把玉玉和浑子叫醒,拉长长一泡尿,要是春枝白天乏了,没有醒来,那就莫怪玉玉和浑子在床上开湖塘。第二天,非得晒褥子被子不可。没有日头,就用火烘,满屋尿臊气,若是晚饭吃得干,玉玉和浑子一觉睡到大天光,也不尿床。可总吃干的,哪里有?
孩子们呼吸渐渐均匀了。廷秋晓得他们已经睡着,他翻了个身,轻轻叹了一口气。
春枝也没有睡着,她轻声问道:
“还没睡着么?”
“没!”
“想么事呢?”
“村子里又有好几家没一粒粮了。”
“我们也不多了。”
“还有几多?”
“四五十斤谷吧。”
“麦子呢?”
“一粒也没了。”
“这个上春熬得过去么?”
“不怕!那谷也能辗出三四十斤米呢。那糠也能吃。去年,用糠拌菜做粑吃,不是也吃过么?我们一天吃两斤米,可以吃二十天呢,二十天,山上有了笋子,地上有了青蚕豆,香椿树上有了叶,饿不死。困吧困吧!”
于是就再没有言声。
外面突然一阵狗叫,叫得急火火的。过了一会儿,又不叫了。
廷秋坐起,“不会是贼吧?”
春枝正要睡着,又被弄醒,“什么贼?都快半夜了,贼个鬼,现在还有什么可偷?你就把门打开,看贼偷什么!”
廷秋又叹了一口气,再也没有说什么。雨滴在屋檐下,嘀嗒响成一片。那夜很黑,黑得让人害怕,他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黑暗中,有很多很多张开的嘴巴,冲着他无声地叫着,嚷着。他闭上了眼睛,那些嘴巴依然张开着,离他更近了,在他的周围,把他淹没了。
一抹清光洒在窗棂上。远处山峦树木显出明朗的轮廓,窗外雨声已歇,大气中杂糅着野草与泥土气味。
春枝抽掉鼎罐底的两根木柴。那粥又已煮好。她盛了一碗,凉在桌子上。她有意捞了一些稠的,却也稠不到哪里去,碗里仍有人影在晃。这一碗是给廷秋盛的,今天他要下水田,下早谷种,他不吃饱,扶犁打耙的干重活,能受得住?把脸抹了两把,廷秋就把那碗端了起来,发现那粥比平日稠些,觉得有些怪,堂客莫非疯了?这么吃,一天要吃好几斤米呢!一个上春如何熬得过?
他揭开鼎罐盖,才看见一鼎罐的清清米汤,没有几粒米。他趁春枝不在,连忙把那碗粥倒进鼎罐。
他喝了几碗清粥。肚子撑得很大,可仍觉得空荡,不饱。这时队长喊:“上工啰!”大家纷纷出了门,有的拿着锄,有的捏着鞭,有的扛着犁,有的挑着筐。也不说笑,人人脸上都是菜色,怏怏的,像霜打的草,没有精神。
队长说:“廷秋呢?把仓库打开。”
廷秋手里捏着一串钥匙,他晓得要开仓门,挑谷种。大家在仓库门前立住,看廷秋开门。廷秋正要开门,发现锁被撬了,“噢!锁被撬了!”
这一叫,使大家立即傻了,呆立在原地,没一个人动弹,木头似的。谁都晓得,仓库里没有别的,只有谷种。若是谷种被盗,那一村人别说上春挨饿,秋天也只有喝西北风了。
只那么一瞬间,大家缓过劲来,一起朝仓库里拥。
“是不是偷了谷种?”
“偷了多少?”
仓库很小。先进去的人又被后进去的人挤了出来,众人骂骂咧咧,那眼中都含了火,红红的、炽炽的。
用一种质问口气:
“廷秋,你保管是怎么当的?”
“到底偷了多少?”
廷秋最后走出来,只那么一会儿,他就完全变了另一副模样。他脸色煞白,牙关咬得很死。他的眼睛满是恐惧的神色,一忽儿,变成愤怒,眼睛燃烧着两炷怒火。他的脸又红了,通红通红,弥漫着每一条深深的皱纹。他的额头沁出点点细细的汗珠。他的嘴唇嚅动着,像要说什么,又气得说不出来。
“你魂丢了么?问你呢,偷走了多少?”
廷秋定了定神,“一担。”
“一百斤哩!”
“这不要了我们一百多人的命么!”
“抓着了,揍死那狗日的!”
“我看是家贼!”
“本湾人干的?”
“你想想,别个湾子离这有几远,半夜三更来偷,不怕鬼么?”
“也是!”
队长急得双脚直跳,“妈的个,这么爱偷,怎么不把老子的鸡巴偷去吃了!”
“队长,我看一担一餐也吃不完。我们挨家挨户搜!”
“对,搜!”
“要是藏了呢?”
“能藏到哪里去?就是藏到×窟窿去,也能搜出来!”
队长问:“不犯法吧?”
“犯什么法?偷东西才犯法呢!”
队长又问:“大家都愿意搜?”
众人都点点头。
廷秋说:“要是人家还有谷子呢?”
有两三个人应和,“是啊,还有谷子怎么办?有谷子就算偷么?”
队长问:“还有谷子?哪家还有谷子?他妈的,我几天没见一粒米了。”
众人应和,“是啊是啊,谁家现在还有谷子,猫窝里还能搁住鱼么?”
那两三个应和的人再不吭声。
廷秋说:“我家就有谷子。能说那是偷的么?”
众人眼睛直了!一齐盯着廷秋,好像原来都不认识他。
“我们大家都吃完了,怎你家还有?”
“当保管还真有当保管的好处。”
“我看八成是你偷的。”
“莫放狗屁!”廷秋狠狠骂了一句。那人是他的叔伯大哥廷洪。廷洪伸手给廷秋一拳,廷秋没来得及躲,那拳打在鼻梁上,鼻孔打破了,血流到嘴唇。
众人看在眼里,没有哪个喊不打了,却在一旁加油,“打死他,打死他!”吼得地皮发抖。
廷秋见打他的是自家兄弟,气得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绿了狗眼!你看我是偷东西的人么?”
廷洪说:“怎么独独你家有谷子!”
廷秋无言以对。他转而一想,现在粮食就是命。自己是保管,当着大家的家,却把粮当丢了,不怪自己怪谁?他把嘴唇的血舔了,又吐在地上,“你们搜吧!从我家搜起。要是搜出了一担,你们杀我剁我都行!”
队长怕闹出人命,派了人去叫大队长。
大队长说:“只有搜!一家一家挨着搜!”
搜了一上午,从四家搜出了谷子,廷秋那四十五斤搜出来了。另外三家也搜了八十多斤。一共有一百三十二斤零二两。
那谷子金黄金黄,颗粒饱满,在云缝漏下的阳光下闪着炫目的光芒。谷子摆在禾场上,全村男女老少围着它。被搜出谷子的人家哭哭啼啼,不停地呼着冤枉。
春枝也哭了,不过那是在家里,现在她没有哭。她相信人总要讲点道理,不是偷了一百斤谷么?现在出来了一百三十二斤零二两,看你怎样办?
众人也在议论:“他们打伙偷的么?”
大队长说:“多出三十二斤零二两,这说明不是偷的。那到底是哪一家没有偷呢?你们四家谁也不承认自己偷了,也就说不清楚了。我看这样吧,那一百斤就交出来,撒到田里去,做种。另外三十二斤零二两,你们四家平分,一家八斤,多余的二两就算了。
那四家谁也不干,都说自己没有偷。
队长说:“照大队长说的办吧!”
春枝含着泪,力图不让那眼泪流出来。她想骂人,却又骂不出来。她想打人,又不晓得去打哪一个。她把那八斤谷子提了回来,一进屋,便关了门,掩面大哭。
各家各户都断了粮。那四家却在众人面前露了底,八斤呢!该吃饭的时候,便有流着鼻涕的细伢,拿着一只盛饭的小竹筒,出现在那四家门前,眼睛干巴巴地盯着别人的碗。有的干脆说:“把一点给我吃吧?”“去去去!”那细伢便失望地走了。有的细伢忍不住,一路哭着回去。于是有些大人除了骂伢没出息外,还走到门口指桑骂槐,骂得一村子疙疙瘩瘩。
大约是省得惹那是非,吃饭的时候,各家各户便都闩了门,天皇老子也叫不开。天塌下来的事,也要等碗放下来再说。邻里之间,从前说不出的和睦和亲密,现在生分得不行,打了照面,也不说话,似乎彼此不曾认识。
廷秋喝完清粥,蹲在门坎上,取一根钡针似的竹片,剔着牙齿。几根嚼不烂的野菜根塞在牙缝里,不肯出来。剔完牙齿,廷秋拿起那根水烟袋,叭嗒叭嗒地吸。那烟叶很粗,烟很呛人,呛得他自己咳个不停。
“不能少抽一点?”春枝把嘴从碗边拿开,“烟能当饭吃么?”
“少嗦。”廷秋有些不高兴。
“跟你说来,”春枝把碗一放,“我们晚上也没有一粒米了。”
“没有米了,跟我说有么子用?”
“你是当家的,不跟你说跟哪个说?”
“我也变不出米来。”
“不能想点法子么?”
“饿不死你!”
门口是一块麻地。
有人提着篮,扛着锄,去挖麻苕。麻苕就是麻根。
“麻苕能吃么?”春枝悄悄地问。
廷秋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