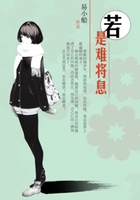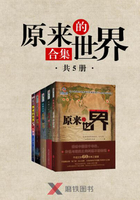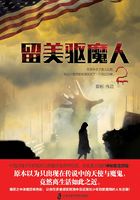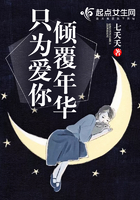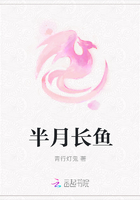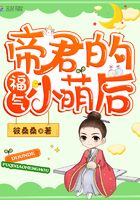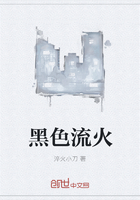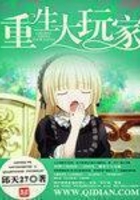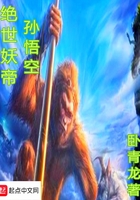小年儿的第二天,腊月二十四头半晌儿,刘老爷家的大马车又停在了王家大草房前。车上坐的是五少爷刘成信,赶车的还是刘三儿。
五少爷进屋一看心里边儿别提多高兴了,这个家整得太像样了。墙用白纸刚刚糊过,整个屋子那叫一个亮堂。炕头上边儿的墙上粘着一张杨柳青年画——娃娃抱鲤鱼,把个屋子点缀得喜庆十足。炕上的被垛摞得溜齐,炕席是新编的,屋子特别的干净。靠东墙摆着的大卧柜擦得锃亮。炕头下的攮灶子里还燃着柴火,屋里很暖和。外屋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锅碗瓢盆拾掇得规规矩矩,柴火堆儿码得也很板正儿,锅盖也是木头的本色儿。
今天,刘成信来没跟刘老爷打招呼。老爷子这几天总叨咕这几个孩子,他心里知道想接这几个孩子来家过年是不可能的,淑清那孩子太有主意,谁也说服不了她。五少爷刘成信更掂心这几个孩子,装了两面袋子冻饺子,还有两条二哥从泰安捎回来的大胖头鱼,招呼上刘三儿赶着车就来了。
淑清正在炕上纳鞋底儿,看见五舅进院儿,放下手里的活儿迎了出去。
“五舅,这大冷天儿,你咋又折腾来了?”淑清一脸笑意。
“在家待着也没啥事儿,全家人都掂心你们,我就来看看。这屋子收拾得这个利索,你们几个可真能耐呀,回家跟你姥爷一说,他不得咋乐呢!”
珍珠赶紧拿来笤帚,打扫干净刘老五鞋上的雪,然后跟着刘三往屋里边儿倒腾东西。
淑清说:“五舅,你咋又往这儿拿这么多东西?上回我姥爷给拿的东西还没咋动呢。”听着是埋怨实则是感激。
“也没拿啥,你几个舅妈包的冻饺子,过年这几天都得吃饺子,拿过来就煮,方便。还有你二舅从泰安捎回来的大鱼,一条都十来斤,是双阳河那边儿,撺冰眼得来的,咱这边买都买不着。”
淑清突然想起了个事儿,问道:“五舅,我三舅那边儿有信儿没?我咋听说张少帅的队伍早都撤到了关内去了呢?”
听见淑清的话,刘老五心里边儿这个高兴,这孩子咋这么懂事儿呢?这是过年了,想亲人了。
“你姥爷也为这事儿闹心呢,就夏天来封信,到现在连个信儿都没有。不过听说他们在南边跟小鬼子打仗呢,也不知道个准信儿。你姥爷最担心的就是你三舅那个脾气,打起仗来不要命,怕伤着啥的。”
“事儿肯定是没事儿,我三舅那么大的官儿,又不用亲自上去打,我看我姥爷的担心是多余的。”
“啥样咱们也没招儿,就得凭天由命啦!”五少爷叹了口气说道。
“我二舅和我四舅回来过年不?我姥姥这段咳嗽病犯了没有?”淑清又问道。
珍珠从外屋进来,端了两大碗开水放在炕沿上。
“三舅,五舅,喝点热水暖和暖和。”
刘老五心里又是一阵热乎,我姐把这些孩子咋调教得这么好呢?他喝了一口水,接过淑清的话儿。
“你二舅和你四舅都能回来,要不你姥爷也不让啊。你姥姥的咳嗽病这段时间也还行,前一段儿犯一阵子,吃了蔺先生几副汤药,这段儿时间见轻了,你不用掂心。”
王老三帮着烧火,珍珠开始做饭了。刘老五听见刷锅声急忙走进厨房喊:“二外甥女儿,想让五舅多待一会儿就别忙活了,再忙活,我马上就走。咱们爷儿几个坐这儿消停地唠会儿嗑儿。”
淑清追出来拉着刘成信说:“五舅,家里啥都现成的,你就吃一口再回去吧,外边这么冷,饿着肚子往回赶,我们心里也不得劲儿呀!珍珠,你和三叔忙活,我跟五舅唠会儿嗑儿。”
淑清连扯带拽地把刘成信拉进屋。她悄悄地把福临拉到身边,告诉他去东院儿把范婶儿叫来。又跟刘成信说道:“五舅,我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啥事儿呀?弄得这么神秘。”刘成信不知道这孩子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淑清怕让在外屋的王老三听见,关上里屋门悄悄地跟刘成信说:“我帮我三叔相中了一个人,就住在东院儿,就是原来我们家住在李大善人家时北屋的邻居。前一段儿胡子打响窑时,她家范叔被打死了,剩下的孤儿寡母也没法儿过。我就撺掇我三叔,俩人也都愿意。”
“傻孩子,这是你们家的事儿跟我商量啥呀?”刘成信笑着说。
淑清拉了五舅一把说道:“你忙啥呀?听我把话说完。我是想等我范叔烧完百天,就把他俩的事儿办喽。范婶儿家没房子,住的是杜老爷家四面透风的瓜窝棚。我想就我们几个孩子,这大房子也挺不起来,西屋还闲着,不行就让他们搬过来住,这样大家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不知道你同意不?”
“这也是你们家的事儿,我同不同意能咋的?”刘成信还是笑着说。
淑清干脆直截了当地说:“那能行吗?这房子是我姥爷家给我们几个盖的,我三叔姓王,老刘家盖的房子让老王家人住,你不同意哪行啊?”
刘成信嘴上没说,心里边儿却在想,淑清这孩子虽然年纪小,办事儿却滴水不漏。明知道这事儿说出来,我没法儿反对,却提前跟我商量,把我们家的嘴堵得溜严。
“淑清啊,这房子是你姥爷拿钱张罗盖的不假,就是给你们盖的。盖完了这房子就是你们家的了,怎么住你们自己说了算。再说这事儿本来就不算什么大事儿,用不着想这么多。你三叔也一直在照顾你们,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家的事儿,你们自己定,我们不参与。”
“五舅,那你这是同意了?我还没和我三叔说,他要是听说你同意这么办,还不把他乐坏喽!”淑清听五舅这么说非常高兴。
福临和桂珍手拉手走了进来。
淑清马上介绍说:“范婶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五舅,这是我姥爷家的老刘三舅。”淑清没落空,也把刘三子介绍给了桂珍。
“这就是那院儿的我范婶儿。”
桂珍明白了淑清让福临叫自己来的目的。她一点儿准备没有,有些不知所措。她两只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脸红到了脖子根儿。
“五老爷,三哥,你们刚到啊?外边挺冷的,冻够呛吧?”
刘成信对桂珍有印象。姐姐去世的时候,她屋里屋外的跟着忙活了好几天,能干活儿还挺能张罗。桂珍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但年龄并不大,看起来也很顺眼。
刘老五觉得这个女人要是进了这个家,应该能不错。
“啊,老妹子,刚才,我大外甥女儿已经把你和老三的事儿跟我说了,挺好的!听淑清说过,以前你就没少照顾这些孩子。今后这几个孩子还得让你多操心呢。”
“哎呀,五老爷,这可不是,我没照顾过孩子们什么,说实话,倒是这些孩子净照顾我了。要不是淑清,我没准儿都活不到现在。”看见刘老五很随和,桂珍的紧张减去了不少。说到伤心处她的眼圈儿红了。
淑清一看桂珍要动情,马上插话说:“啥照顾不照顾的,都是穷人帮穷人。范婶儿,我陪我五舅,你去帮着珍珠做饭吧!”
一会儿工夫,四个菜就端上了桌。还没到饭时,只有王老三上桌子,陪刘成信和刘三子吃了口饭。
刘成信走后,桂珍帮着淑清和珍珠收拾碗筷儿。淑清把和五舅说的让桂珍一家搬到西屋住的事儿,告诉了桂珍和王老三。
“这可不行,坚决不行!这房子是老刘家盖的,你们是老刘家外甥,你们咋住都行。我在这儿住是因为你爸爸出工没在家,我领着你们几个孩子。我用这屋娶媳妇,那不让人家笑掉大牙?肯定不行!”没等桂珍说什么,王老三首先反对。
“咋的啦?这房子是我姥姥家盖的不假,既然是给老王家盖的,就得由老王家自己说了算,怎么住也由老王家自己安排。你在这闲着的屋子里娶媳妇怕人家笑话,把一帮没妈的孩子扔下不管,出去自己娶媳妇,就不怕人家笑话?本来就是两家苦命人凑合在一起过日子,你非得要整这个脸那个皮儿的,就有脸面了?”桂珍听王老三说的有道理,就没插嘴。淑清那张不让人的嘴开始抢话儿,调门儿也很高,像是要吵架。
淑清这一通儿连吵吵带喊,把王老三给镇住了,王老三寻思半天没张开嘴。淑清一看王老三没嗑儿了,又把语调压下来。
“三叔,说真心话,咱们这两家谁过得不难?本来咱就是互相搀扶着过日子,再整那些个穷讲究有意思吗?咱们现在一起将就着,花钱手紧点儿,等明年要是能再攒点钱,这东边还有房场,咱就再盖两间。到时候你不想在一起过再搬出去不行吗?都是自己家人,啥你的我的。”淑清说着眼圈红了。
“大闺女,那是过了年儿,出了正月以后的事儿呢,到时候咱再商量,先别着急定这事儿,啊!”桂珍马上打圆场,说着拉住淑清的手。
“范婶儿,反正你和我三叔的事儿,咱们都定下来了。我看从明天开始,你们那院儿就别开伙了,都上这院儿吃来,你也过来张罗做年饭。”淑清好像是家长,跟这俩人说话像是命令。
桂珍马上反对说:“那怎么行?我们那边也挺好的。再说,我跟你三叔的事儿还没挑明,除了咱们自己家,别人都不知道。这就在一起过上年啦,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没人性,来啃你们这些没妈的孩子。不行,真不行!”桂珍直摇头。
“啥不行啊?我们这边又是鱼又是肉的,你们那边啃冻白菜、吃大饼子,你心里能得劲儿,还是我心里能得劲儿?你不吃拉倒,可那老的老、小的小,你能忍心我不能!你要怕面子上过不去,我这就去找李满堂让他做媒,这事儿不就挑明了吗?”淑清一顿“突突突”,让桂珍根本没法儿插嘴。
看见桂珍为难的样子,淑清拉过桂珍的手说:“范婶儿,啊不,是三婶儿!你就听我的吧,你们收拾,我这就去找李满堂。”说着拿起外衣就往外走。
“我的那个活祖宗哎,这性子咋这么急呢?”桂珍马上往回喊,淑清已经走出老远。
淑清找到李满堂,把她的意思跟李满堂说清楚后,李满堂非常支持,还一个劲儿地夸淑清。
淑清和李满堂来到范家时,桂珍在王家还没回来。范奶奶早就对这件事儿十分赞成。李满堂把话一说,老太太响快地就答应了,还约定二月初六让桂珍过门儿。
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五,淑清逼着三叔跟她一起上了一趟李黑塔屯儿,在那儿的商铺里买回了足够做两套行李的棉花和布,还为三叔和桂珍每人买了一身做新衣服的布料。回来后,淑清找到村里的冯成衣匠子帮着裁好,让桂珍拿回去抓紧做。又找了村里活计好、命全科儿的女人,整整忙活了一天,做好了两套行李。淑清这么着忙,是她知道有正月里女人不能动针线的说道,她决定年前把这些活儿做完,省着到时候抓瞎。要是依着桂珍就啥也不置办了,可淑清不干,她觉得不管咋说,三叔和桂珍也是翻一次身,不能随随便便。
腊月二十八晚上,所有的活计都忙完了。淑清把桂珍叫到家,让她帮着发面,准备蒸馒头和捞连年饭。东北的农村有个老理儿,正月里不能让生米下锅。苞米子煮好了用水投过后冻成团,放在外面的大缸里。吃的时候,拿回来缓好,在锅里用热水一烫就可以吃。小米饭也是一样,捞好后冻成坨子,吃的时候在热锅上一熥就可以吃了。馒头也是蒸完后冻上。准备东西两院儿九口人一个月的吃食,不是一件小事儿。王老三、桂珍、淑清加上珍珠四个人,在两家的四口大铁锅前整整忙活了两天。
大年三十的上午,头一天已经缓好的猪肉和下水,被放在了一口十四印的大铁锅里,一个开儿就把香味儿从锅里逼了出来。福临、玛瑙和盘脐子、丫蛋儿,闻着香味直咽哈喇子。
“二姐,啥时候开饭呢?”玛瑙跟在珍珠的屁股后一会儿问一句,把珍珠烦得没招儿没捞的。
过了年儿,西屋就要作三叔的新房了。这几天人多一个屋子也挤不下,淑清就把西屋的炕也烧了。开始的时候有点凉,烧了两天屋子就暖和了。老齁巴美滋滋地坐在西屋的火炕上。
灶坑的火燃着,孩子们里外屋跑着,厨房里香味儿飘着,把两个晦气了一年的、冰冷的家温暖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