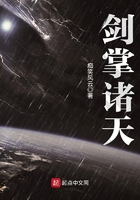“快?”我像兔子一样一溜烟狂奔到新开路小学门口,但见正午之下门可罗雀,我惊喜万分却无处炫耀,直至午时三刻,同学们进校,我才站在校门向大家郑重声明:“我今天是第一个到校的。”
当然事情远没有结束。当同学们排好队走进教室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把书包落在家里了。我拼命朝家里跑去,身后传来那催命般的上课铃声。
混沌得令人哭笑不得,是我启蒙时代的唯一记忆。
在我一直珍藏的家庭档案里,有两份我最早接受启蒙教育时期的原始文件。一份是四岁时,私立北平汇文第一小学附设幼稚园小班的《评语及各科成绩纪录表》。另一份是六岁时,北京东城区新开路小学一年级的《鉴定评语及学业成绩表》。两份文件相距整两年,但可以看得出,就操行而言,我的进步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两年来我已经从一个“欠活泼,记忆力弱”的傻小子,蜕变成一个“学习有进步,不守纪律,对同学和气及爱劳动”的一年级小学生了。而就学业而言,算术已从当初的65分,进步到学期成绩95分。国语从当初的75分,进歩到学期成绩82分。唱歌和图画也都有较大的长进。在全班47名同学当中名列甲等第27名。当然,这样的名次,对于今天许多学生家长来说,已经无颜见江东父老了。但当时我的父母,却从未因此感到事态有多么严重。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是一个思想改造的地方。学员大都是旧政府的官员及解放前的公教人员。北平市的原市长何思源就与父亲同在一个学员班。在这里,学员们不仅要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别了,司徒雷登》等著作,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及某些政策法规,最主要的一条,是要交代自己(包括检举别人)在解放前所有与共产党的主张相悖的思想及行为。学员们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期间,平日是住校的,只周六回来。一个阶段下来,父亲的心情明显好起来,每次回来,他都会认真地查看我和姐姐的作业,听我和姐姐给他唱那些新学会的歌曲,要是有好的故事片,他还会与全家人一起去看电影,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栖凤楼西口附近有三家电影院,其中有长安街上的美其电影院和平安电影院(后来改作青艺和儿艺),还有崇文门大街上的大华电影院。当时正是新旧时代交替的时候,所以一些解放前出品的故事片仍在放映,像《万家灯火》、《春风秋雨》、《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我们还看过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工作者创作的《中华儿女》、《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和《钢铁战士》。
五十年代初,苏联电影开始进入中国。记得我们曾经看过一部反映年轻一代走上革命道路的苏联电影《马克辛的青年时代》。从电影院出来后,在华灯初上的大街上,我一路高声朗诵着电影中的那句台词:“前进吧,马克辛!前进!你要知道,你是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惹来路人许多诧异的目光。
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个周日,父亲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买书,从书店出来后,意外地与李文光迎头相遇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李文光看见父亲后,竟瞬间侧过头去,转身消失在大街上的人流里。父亲陷入了极其复杂的困惑之中。
消失的李文光是通过钱禹年认识父亲的,据说也是燕大的同学,他曾去过几次江擦胡同二十九号,而且不管父亲当时有多忙,他每次去,都会无所事事地坐上许久。
“沉屁股。”连母亲都有点烦他了。
最后一次来是一九五〇年开春的一天。那一次他是来求父亲的。他说自己租的房子到期了,一些家具器皿一时无处搁置,打算托父亲找间空房暂时寄存一下。父亲怕他死磨,便答应将那些东西存放在东堂子胡同五十二号,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北平区分会的一间闲房里。之后,李文光便不再登门做客了。
一九五〇年夏天,父亲因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财产移交事宜,到东堂子胡同五十二号去核实情况。在那里,父亲见到李文光存放的家具器皿仍堆放在房间的角落里。他无意中拉开一个五斗橱的抽屉,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支手枪竟赫然出现在抽屉里。
父亲立刻紧张起来,他派张木匠找来李文光,指着那支手枪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嗨,我以为是什么事呢,您真有点大惊小怪了。”李文光毫不在乎地把枪在手里掂了掂:“我常玩这个,真的,起码可以防身。”
解放前,一些富家子弟拥有枪支自然无可厚非。但时逢新中国成立之初,军管会关于上交武器的通告早已发布了,更何况父亲对李文光的背景毫不知情。于是,他断然让李文光尽快将存放在这里的所有物品统统搬走,借口是人民政府近日即将收回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全部房产。李文光没做任何解释,他痛快地答应了。
从此,李文光就再没登过江擦胡同二十九号的门。
“可走了。”母亲喘了口气说:“一坐就是大半天儿,真让人冷不得热不得。”
几个月来,华北革命人民大学的思想改造,已经使父亲开始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嗅觉。王府井大街上奇怪的邂逅,让父亲深感不安。从李文光街头的有意回避,联想到五斗橱里的那支手枪,父亲当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回到华北革大后,父亲便以书面形式,向组织检举了他对李文光的怀疑。娄钊昆、钱禹年、李文光的军统特务案,就此浮出水面。
但一九六五年,在父亲被定性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决定中,“……为特务钱禹年、李文光匿藏匪用物资。”却成了又一条有口难辩的罪证。
新开路小学的校门外,每天都有几个摆地摊的,卖些笔墨纸砚、描红、橡皮等文具。这些地摊还捎带着卖些吃的东西,像春天的青杏儿、夏天的桑葚儿、秋天的大赤包儿、冬天的酸枣面儿等,对女孩子来说十分诱人。
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卖画的。
那是一种和田字格本一般大的单页淡彩印刷品,内容大多是姑苏夜泊、寒江独钓、华山松岩、三潭印月等山水小品,不知什么时候,我开始被这些图画所吸引。
不久,在我的书包里,已积攒了几十张这样的画页。我将其视为珍宝,每天从早到晚爱不释手。
渐渐地,我变得安静下来了。我想起了徐悲鸿先生说过的话,每天放学回家后,我都要花上大量的时间临摹这些优美的画页,一张一张的很有成就感。
终于,姥姥也被我感染了。她用笔刀削好了所有的彩色铅笔,然后伏在桌前,在画纸上十分娴熟地勾勒出一朵朵盛开的牡丹,飞舞的蝴蝶,活泼的金鱼,还有奇异的佛手和丰硕的石榴。这些都是姥姥做姑娘时和画师学的。那时她梳着光亮的两把头,发髻里掖着一个盛着清水的琉璃瓶,里面插着一枝香气袭人的茉莉花。
十二月初,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三期学员即将结业。此时,大连港务局毛达恂局长不失时机地通过交通部有关部门,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申请调派职工教育方面的专业人才。经过筛选,从结业学员中选出八人远赴大连,父亲即为其中一名。
听到这一消息后,新婚不久的叔叔和婶母立刻从天津赶来了。叔叔自山东齐鲁医学院毕业后,刚刚分配到天津铁路医院检验科。婶母张淑云天津护士学校毕业后,去了水阁医院。叔叔和婶母是一九四八年在仰山伯伯的新星报社认识的,一九五〇年于山东济南完婚。
叔叔婶母来北京的第二天晚上,由父亲做东,在王府井东来顺饭庄请仰山伯伯、珍一阿姨及祁伯伯一起吃了顿饭。
仰山伯伯那天喝醉了。他满脸通红地举起酒杯,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我与素心兄自昌黎汇文起至今二十余年,可谓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欲相进,同利相死。其间,平津云烟,巴蜀烽燧,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虽不曾煌煌大业,却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了。”说着他打了个踉跄,跌坐在椅子上。
“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矣……”仰山伯伯嘤嘤地哭了。
不久前,十月出版社宣告破产了。当初计划翻译出版的外文书籍,成书后,均得不到新闻出版机关的出版书号。在贷款逾期债主盈门的情况下,倒闭是在所难免的。为了支撑生计,珍一阿姨走出家门,在一家供销社做了售货员。仰山伯伯经杨扶青推荐,为北京市东城区工商联收用。这一年父亲四十一岁,仰山伯伯三十九岁。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父亲一行八人从前门火车站,乘火车远赴东北了。按大连港事前的安排,家属需暂缓离京。因为这期间大连方面还需做大量的后续工作,为家属联系接收单位,为这些来自首都北京的专业人才,安排住房等必要的生活准备,等等。
当父亲乘坐的列车伴着志愿军战歌的旋律,缓缓驶离前门火车站站台的时候,母亲的心中油然生出一丝悲壮。这不是为父亲的远行,也不是为那迎面扑来的陌生,多少年之后,母亲才意识到,这悲壮源于人们义无反顾地奔赴,源于那时代洪流中的孤独。
父亲去大连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只能通过书信往来了。父亲逢周日必给我们发一封信,九个月下来,从未耽搁。
父亲是一个做起事来一丝不苟的人,包括对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他做起来都十分认真,譬如写信封。
父亲写信封是很讲究的。邮票贴的位置也十分标准。平常写给母亲的信封上,台头自然是“李玉玺女士收”,而写给我的信封上,台头必写“唐浩小朋友收”。开始回信时,我总愿意在信封上写“唐子清父亲大人亲启”,以表尊敬。父亲却及时纠正了我,他来信说:“信封是写给邮递员看的,你这样写,我便成邮递员的父亲大人了。”这些细小的生活习惯,父亲从很早就注意培养我们,现在想来终生受用。
父亲给我和姐姐写信,字总是写得很大且十分工整,从不连笔。字里行间像是与我们面对面的谈话,十分亲切。至今我还保存一封一九五二年早春,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
唐浩:从前你给我来的信,写的很好。为什么很久不给我再写信了?爸爸希望你两个星期给爸爸来一回信,因为爸爸实在喜欢看你的信。姐姐上次来信说:“老师说小弟弟很用功学习。”爸爸非常高兴!爸爸给你寄去的相片和《好孩子》半月刊,你都收到了吗?你觉得《好孩子》中那(哪)个孩子最好?你会写出来告诉爸爸吗?从前你的算术学得很好,现在是不是更好了?我从前在书中看过一句话:“友爱、大方、慷慨、诚挚。”我以为很好。请妈妈给你讲讲什么意思。你们能不能作(做)到?爸爸很好。祝唐浩进步!爸爸三月二十八日清早在大连写一九五二年,栖凤楼小三条七号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是在平静的企盼中度过的。
这一年夏天,仰山伯伯带来了一个让人心痛的消息,“三反”运动中,在昌黎汇文中学全体师生对“大贪污犯徐维廉”的批判会上,徐爷爷的二儿子徐志方激动之下跳上讲台,当众打了徐爷爷一记耳光!对于将尊严视为生命的徐爷爷来说,这一掌几乎是致命的。
年底,私立昌黎汇文中学正式由人民政府接收,徐爷爷黯然离开了昌黎。
直到第二年十月,徐爷爷的贪污问题方才得以澄清。之后,通过杨扶青的举荐,周恩来办公室出面将徐爷爷安排在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医学杂志社,做了一名普通的外文编辑。至此,冀东地区一代赫赫有名的开明绅士,终于在云卷云舒近三十年之后怅然沉寂下来了。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母亲、姥姥携我们姐弟三人,从天津赤峰道码头登上了海盛号客轮。叔叔和婶母一直把我们送到栈桥的入口处。
“一路平安!”叔叔站在码头上一直挥着手,直到轮船烟囱里的黑烟将天津码头远远地遮去……
站在船头的甲板上,我奇怪地问母亲:“妈,大海不是蔚蓝色的吗?”母亲裹着风衣耐心地说:“现在还没有到大海,这里只是海河,所以是黄色的。”
“什么时候咱们能看到大海呀?”
母亲望着轮船行驶的前方:“大概不远了。”
下午,河面渐渐开阔了,但水的颜色还是黄色。天空中传来了阵阵鸥鸣,人们闻到了海的气息。
黄昏到来之前,风浪开始大了。母亲将我和姐姐叫进船舱,我很早就睡了。睡梦中,我又见到了小三条的王致和,他对我说:“我抽空带你上香山去,我妈说,山里的秋叶又红了……”
第二天一大早,当我推开舱门走上前甲板时,立刻被眼前浩瀚的海洋震撼了。阳光下,湛蓝的海水卷着雪白的浪花,撞击着海盛号客轮的船首。呼啸的海风将飞扬的泡沫吹成水雾,在船舷一侧化作道道稍纵即逝的彩虹。天空和海洋向四周无限伸展,秋云投下巨大的云影,在海面上飞快地掠过,让甲板上的人们感到阵阵温暖,阵阵寒凉。
中午过后,遥远的海平线上,出现一道黛紫色的山峦。我一头钻进船舱,在漫长狭窄的走廊里奔跑呼喊着:“我看见陆地了!”
“于是,上帝对诺亚说:你和妻子儿女都可以走出方舟了。你要把和你同在方舟里的所有的飞禽、走兽及一切爬行的生物都带出来,让它们在大地上繁衍生息吧。”(圣经·创世记·第八章)
轮船绕过一片峭壁形成的海岬,我们见到了一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