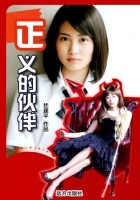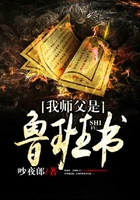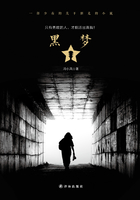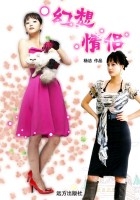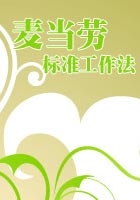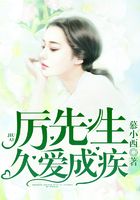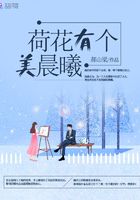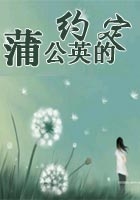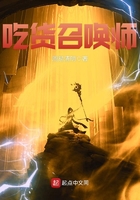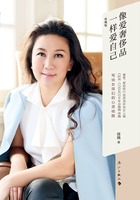随意间,一位同学发现在船台下的一个角落里,几个造船工人正在用木方和三合板,钉制一个巨大的椭圆形的轮船烟囱。我们好奇地凑上前去。
“别过来!”工人们发现了我们:“离开这儿!”他们挥手示意,表情都很严肃。我和同学们灰溜溜地跑回了车间。
一周之后,在六亿人民地动山摇的欢呼声中,“跃进号”万吨巨轮顺利下水了。在三合板做成的高大的烟囱周围,飞过许多彩色气球和绸带,以假乱真得天衣无缝。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为了培养年轻人的劳动热情,许多中学都办起了自己的校办工厂。大连九中自然不会例外。
一九五八年冬天,学校与西岗区北京街一家生产电器开关的胶木工厂联合办学。同学们与一线工人一起实行三班倒,即早班七点至午后三点,中班午后三点至深夜十一点,晚班深夜十一点至第二天早上七点。
我们参与勤工俭学的是压力车间,那是一个会让人立刻联想到画家门采尔笔下欧洲工业革命初期常见的半手工作坊。昏暗的灯光、蒸汽与火焰、瓦斯和橡胶混合在一起的令人窒息的气味、简单的重复劳动与机器的轰鸣。
那时,大连市内的公共交通还很落后,夜晚十一点下班时,大家便不顾一切地往北京街的有轨电车站跑,因为如若赶不上末班车,便只能深更半夜地徒步回家了。当时我们还都是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况且又是隆冬。
我这辈子有两大心理疾病,至今难以克服。一是恐高,二便是惧怕黑暗。所以只要上中班,我就会暗暗地盯住一个人,尤其是与夜班同学交接班时,我更会寸步不离地跟定她,她叫张念劬,一个比我大两岁的高个子女生。
听说张念劬是个孤儿,与姐姐、姐夫相依为命。他们是南京人,在五十年代,有许多这样似乎充满了故事却谁也无法细问的家庭。张念劬身材高挑,性格泼辣,在车间里,她会把两条大辫子盘在脑后,活脱一个圣彼得堡兵工厂的妇女代表。
下夜班的时候,她总是摘掉套袖抄起饭盒,风风火火地冲出厂门。我不敢怠慢,死死地跟在她身后,否则她会突然放慢脚步,注意窃听,而一旦发现身后真的没有动静了,她便会猛地转过身来:“唐浩,你又死哪儿去了?”
当然,这样的疏忽绝不可再有第二次,因为张念劬的脾气,我是领教过的,那简直比“狼来了”还可怕。
每天半夜,张念劬会把我一直送到清爽街二号侧门的楼梯口,然后一个人站在大街上,不停地对楼上喊:“到家了没有?”
在黑暗的楼道里,我边爬楼梯边大声答应着:“没有……”
“到家了没有?”
“没有……”
“还没到家,你这个死鬼!”
“……到了……”
午夜的大街上,留下她细碎的脚步声。
张念劬姐姐家在清爽街二号北楼,离我家二百米左右。
初中毕业前不久,张念劬随姐姐姐夫离开了大连,之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
一九六六年初秋,我意外地接到一封发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尼勒克一个农场的来信,随信寄来的照片上,张念劬站在几个女拖拉机手中间,正微笑地望着我。在她们脚下,是一片深沉的沃土,在她们身后,是白雪皑皑的天山。
照片后面有一行潦草的题字:“你还认识我吗?张念劬,一九六六年八月。”
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在全国范围里成为工农商学兵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故乡唐庄的青壮劳力都以连队的形式,抽调到东起彭店子西至迁安县城的滦河北岸。在那里,土高炉林立,炉火昼夜通明,从全县收缴来的各种与钢铁有关的器物,被砸碎后,重新回炉。一时间,滦河一线浓烟滚滚,壮观而繁荣。
秋收到来的时候,村子里的强壮劳动力仍披星戴月地苦战在滦河北岸炉火熊熊的土高炉前,留守村子的老少妇孺,便不得不放弃用镐头起白薯的传统方式,由几个妇女拽着一张木犁,将垄里的白薯硬是耥了出来,而没耥出来的便只能赶上一群猪,任其拱食了。由于牲畜和车辆都被人民公社调去炼钢铁了,村里老幼一时无奈,只能将起出的白薯堆在地里,用土埋上,听之任之了。
一九六〇年春天,当成群的灰鹤又一次鸣叫着飞离故乡大地的时候,乡亲们才发现,埋在地里的白薯全烂了。田间地头到处散发着醉人的酒香,庄稼人开始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一九五九年暑假前不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子女组成的***班访问大连。这是大连市政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接待过的为数不多的外国少年儿童友好团体。因为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涉外活动,作为联欢会的主持人,我先后被几位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约见,回答了包括家庭出身在内的许多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不去核查一下我的档案呢?而且,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我那个可怕的“前科”竟然始终无人提及,这对“百密而无一疏”的那个特殊年代来说,堪称奇迹。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在枫林小学为我填写的个人档案里,关于一九五四年的那件事情竟只字未提!枫林小学当时的校长叫王作声,在学生面前,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冷淡的人。
与德国小朋友的联欢会,是在七七街当年的中苏友好俱乐部里举行的。头一天晚上,父亲用英语为我当翻译,并亲自指导我如何划分段落,平抑语速。
“不要大声喊,你不是作报告,要尽量显得平和一些,友善一些。”父亲嘱咐我。
民主德国的少先队员佩戴的领巾是天蓝色的,像他们那一双双天蓝色的眼睛。一位梳着一头金黄色马尾辫的小姑娘,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用生涩的中文为大家演唱了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
……
秋风吹遍了每一个村庄,
把这个动人的故事传扬,
每一个村庄都含着眼泪,
歌唱着二小放牛郎。
泪水从她凹陷的眼窝溢出,我深深地记住了那双天蓝色的眼睛。
一九八九年十月中旬,当秋风又一次吹遍每一个村庄的时候,我随大连电视台新闻采访团访问了联邦德国(西德)。在汉堡、不来梅、杜塞尔多夫,在科隆、特里尔、美茵茨,面对迎面匆匆走来的这些陌生的德意志人,我曾竭力寻找过那一头金黄色的发辫,那一双天蓝色的眼睛。虽然我十分清楚这里是联邦德国,我知道这里与民主德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在我们即将结束那次采访的时候,柏林墙,这道横亘在欧洲中央的“铁幕”,终于被推倒了。
十一月九日晚上,从滚动播出的电视新闻里,人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东柏林人,像潮水一样漫过勃兰登堡哨所,涌向西柏林的大街小巷。我努力搜寻着,却在电视里看到了无数双天蓝色溢满泪水的眼睛。
临回国前,在法兰克福歌德的故居,我记下了这位狂飙突进运动文学巨匠的一句名言:“人们通过自己的智慧,将人类划分出一个又一个的界限,后来又因为爱,而把这些界限一个一个地推倒。”
在大连,从一九五九年秋实施的城市居民口粮压缩的政策,直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逐渐显出了它的压力。之后,随着市场上几乎所有商品都出现了紧缺,人们已感觉到生活开始日渐艰难。那时母亲每次发工资时,都要到青泥洼桥的南货商店,买些高价的香肠熟肉等解馋的食品,高干特供的烟酒,也开始出现在商店的柜台里。
谁都说不好朱嘉禾是从什么时候起又迷上小提琴的,在这之前,他曾迷上过开汽车。他不仅通晓了汽车动力学的基本原理,而且还了解了汽车从发动到挂挡、到转向、到刹车倒车的全过程。他曾爬上一辆路旁停靠的苏联嘎斯车,绘声绘色地向我倾诉他对汽车的理解与钟情。但当朱嘉禾终于用小提琴将作曲家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演奏下来的时候,眼睛里流露的喜悦还是难以掩饰的。
几天之后的一个黄昏,在明泽湖畔的银杏树下,我试探着问嘉禾:“长大了,你想干什么?”
“当工程师。”嘉禾不假思索地说:“设计国产高级轿车。”
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从一九六〇年春天起,姥姥就出现了老年痴呆的倾向。当时大家都在忙,没有更多的理会她。进入秋天,老人的病情日渐加重了,她逐渐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由我们照顾她了。
九月十日黄昏前,躺在床上的姥姥突然喊我,我却没有马上过去。只听见她独自在那里喃喃地说:“三贝勒家的老闺女和我约好了,晚上到湖广会馆听谭老板唱戏去。”
“几点呀?”我故意在一旁大声地逗她。
“六点半……”
不久,她便睡了。十八点三十分,姥姥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