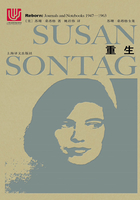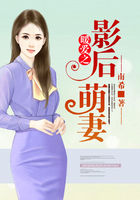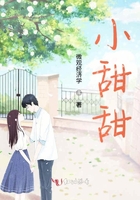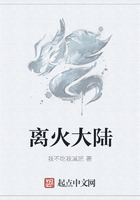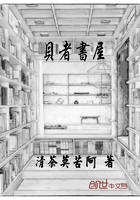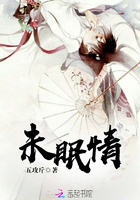1979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其“反革命罪”平反,先后下达两份平反书,第一份称因精神病所有“攻击”言论不作反革命言论,第二份才说:无论有无精神病,所有“攻击”言论均不作反革命言论。(《路翎传》)
如此的字斟句酌,不可谓不“慎重”矣。
那么,有意义吗?当然是有意义的。既往的二十五年,路翎本人、路翎的一家,过着怎样凄惨的日子,我们就不详予描述了,大家只须比照自己所知道的“最底层”境况去想象,绝不比这更好。平反后,路翎回原单位剧协,从扫地工恢复作家、知识分子身份和“文艺四级”工资待遇,1981年迁入新居,得房二间半——这皆拜平反之所赐。
更重要的是,平反后,路翎重新获得“写作”的权利了!他生命最后的十年,几乎完全献给了“写作”。曾卓说,当听说路翎十年间“竟还写出了六部长篇,共写过约三百万字,几乎与他过去创作的字数相等”,先是“令我惊喜”;继而听读过原稿者描述这些作品往往“都仍然纳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钦定的模式之中”,又“感到惊骇,而且难以想象”。曾卓悲问:“难道他的心灵被扭曲到这样严重的地步、思想被禁锢到这样严重的程度么?”
无奈,事实如此。
路翎自己“晚年最满意”的长篇小说《野鸭洼》,主人公海国乔是循“三突出模式”的“主要英雄人物”理念写的。“他是正义和道德的化身,永远正确,永远伟大”。(《路翎传》)
另一部长达一百九十万字的“巨著”《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据看过原稿的朱珩青说,“是试图以‘扑灭了“四人帮”,邓小平时代的来临’的思路来统帅全篇的。”
那部《野鸭洼》写完后,给了当年“同案犯”的老友、人文社的牛汉先生。但凡有一点出版希望,牛汉总会鼎力相助的,但是,“它在牛汉那里没法办”。时为作家出版社编辑的朱珩青也“曾想帮帮忙,然而看后也只有叹气”。自路翎把稿子交出来后,朋友们都保持着“沉默”。至今,“稿件一直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其实,也有光可鉴人的作品。那是涉及朋友、涉及往事的回忆写作,例如本文颇多引述的《我与胡风》,还有《“七月”的停刊》、《忆阿垅》这样一些篇什。只有在回忆中,精神其实一直并不正常的路翎,才找回了通往他心中的文字、思想和感觉精灵世界的桥梁。但是,这种状态只存在于回忆性写作,此外其他,几百万字、六部长篇,都是一堆不折不扣的废纸!
有一行字,从脑海深处慢慢浮上来,愈来愈大、愈来愈醒目、愈来愈压得人喘不过气——那几个字是:
精神奴役创伤
我们知道,这是胡风、路翎所致力的主要的文学主题。从前,他们用思考与笔墨向国人凸显它;后来,他们用遭际亲自验证它。就像他们所鞭挞的,他们自己终于也变成“苦闷的象征”、精神深处遍体鳞伤,甚至真正地“疯”掉了。
然而,这伤痕岂止见于所谓“胡风集团分子”们?我忽然想起来,“文革”后中国文学的第一个阶段,便称为“伤痕文学”。从“精神奴役创伤”到“伤痕文学”,巧合乎?
或许,面对这种“巧合”,不弃“精神奴役创伤”探究的胡风们,可以为他们的深刻而骄傲——极而言之,连同走出大狱时烙在心灵上的那累累的痛苦的伤痕,也是对他们深刻性的一种证明。
中国梵高
1994年2月12日晨,路翎走了。静悄悄地。
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消息呢?我不记得自己当时在做什么。我只是在他辞世十多年后,才开始思索那个时刻。
这两年因为手头的工作,我面对了许多文坛人物。他们都已不在人世。我追索他们的一生,自然,也会感受他们的离去。我发现,对于离去,没有哪一个人比路翎让我想得更多、更久。
原因是,别人的离去,虽也引起这样那样的感慨,但其留下的身影总是清晰的,民族、文坛和公众对他们的认知,与他们一生作为与成就,与他们的精神或人格,大致吻合。可是当我摩挲路翎的作品,在旧照片上打量这个人时,却有个强烈的念头:他是在全中国的疏忽中离开的。
一百年前的一个夏天,一位旷世的绘画天才死在法国的一个小镇,有人在墓边种了他喜爱的向日葵以安息这伟大的灵魂。他的名字是文森特.梵高。是的,同样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一个怎样的人离开了世界。就像路翎在中国那样,梵高是在全世界的疏忽中离开的。生前,人们不能认识他的创作(据说一生只卖出一张画)。而百年后,这个人却几次刷新艺术品拍卖市场纪录。
是的,我必须在谈论路翎时提到梵高。茫茫人海中,我发现这两个背影是相似的——那不仅由于他们离开时的样子,更由于他们经历、精神气质和艺术面貌。当我思索着十四年前那个生命的终止究竟意味着什么时,认识慢慢清晰起来:那是“中国的梵高”的离去……
让我们引用唐湜先生1947年的一句评论:
路翎的作品正是一片阳光,有变幻莫测的光彩与灼人的热,而且他还是早晨的阳光,会给人奇异的,疏阔的感觉。(《路翎与他的〈求爱〉》)
这也正是我们在梵高画作前经常获得的感受,多么相像!
他们都有一颗极敏感、极尖锐、极有力的心灵。
他们的创作都是燃烧自我与生命。
对于艺术,他们同样疯狂——甚至,最后都患上了精神病!
精神病与天才型的艺术家之间,似有不解之缘。路翎精神失常,虽以政治迫害为诱因,但就气质而论,亦无须回避其遗传及禀赋。本文开头即部分地说明这一点。不过,这种气质不等于必然落得疯掉的结局。超强的敏感、剧烈的内心冲突以及躁动的焦灼,可以通过自由而充分的创造来释放,转化为惊世骇俗的艺术作品。倘若如此,那么,像梵高那样即便天意难违、终于疯掉,其生命意志与价值仍可说完整彻底地实现,自我并未压抑。
于是我们发现,“中国梵高”与他的荷兰同道到底有所不同。后者精神失常自杀而离去,某种意义上,走得没有遗憾,甚至走得幸福;有关传记写道:“在寂静的田野里,面对着灿烂的阳光,他用手枪朝自己的胃部开了一枪。随后,平静地收拾起画具像往常一样走回旅店。”(刘世忠《“狂人”画家凡高》)他主宰着自己。路翎却不是这样。路翎的精神失常,恰因艺术生命、艺术自我被抑制、阻碍和剥夺。
也许我们该说,路翎只是半个梵高。但无论如何,具备这种气质,并曾经在作品中表现出原始、灼热、单纯、深厚的生命力的作家,中国只有路翎。八十年代后期,我因失望或困惑,提出“伪现代派”的问题。那时我孤陋寡闻,不了解路翎。后来一经拜读,立即认定:“伪现代派”的毛病——技术上徒具其表的邯郸学步、优孟衣冠、鹦鹉学舌,而生命意识、生命情绪和思维方式仍困茧中,艺术的形式与精神彼此分离,里外两层皮,从而陷于矫情、造作和哗众取宠,对我来说,它所引起的不快,和假古董、伪古迹相仿佛——这些,在路翎那里绝无踪影。路翎的时代,“现代派”尚未变成一种时髦,或贴金的标签,但他的实践,无疑处在这条路上。他坚决拒绝“对于民间形式底拜物情绪”(这是指中国的传统,1942年2月27日致胡风),而对写实主义(西方的正统)则批评它“常常只是罗列事实和追寻外部的刺激”,宣布“我底反抗是去年动手写长篇时开始的”(指《财主底儿女们》,1943年5月13日致胡风)。这种艺术反抗的自觉,充分表现于语言自觉——有人看见路翎作品存在文句不顺、似有语病的现象,就此奚笑、怀疑他的素养,其实,那是他对语言牢笼的主动反抗,他这样回答胡风就此提出的关切:“你说的关于作品的话,想了一下。文句上的毛病,那起源是由于对熟悉的字句的暧昧的反感:常常觉得它们不适合情绪。”(同上)虽然他不曾打“现代派”旗号,评论家也不从这角度来解释他,但很明显,他的文学立场是这样的。然而,他与八十年代中期风靡一时的“现代派”之间,有一个本质区别。即后者乃是从一种理论、一种时尚文学观念那里,获知可以“这样”写作,或更直接地说,是“西方文学”告诉他们可以“这样”展开艺术反叛;而路翎的反叛,却根本不是别人告诉他如何他而后如何,他是从自己心灵、精神内部,升腾起反抗的意识。因此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在精神上通彻一体。他首先在自己思想意识上反叛了,然后才投入创作的反叛。他不是沐猴而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