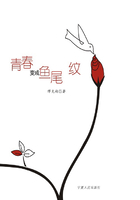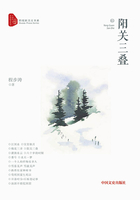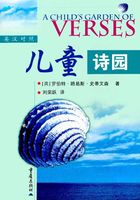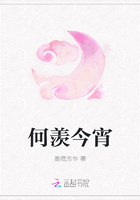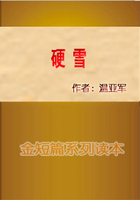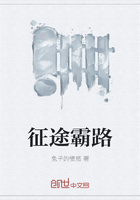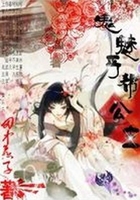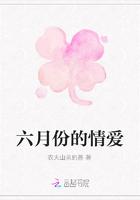他们离开东京到京都,借住友人杨贤江家,开始同居。此后,茅盾恢复了创作状态,写出《虹》。《虹》在《小说月报》连载,轰动一时,出单行本后,销路甚广。秦德君说:“茅盾可以说名利双收了。”根据她的陈述,这部作品的素材乃至思路是她贡献的。梅女士原型是大革命时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四川女生胡兰畦,对此,《我走过的道路》是承认的。而秦德君说,胡兰畦是其同乡好友,茅盾根本没见过她,是她把胡的故事讲给茅盾,“而且胡在四川经历的山山水水、城市乡村,他也没见过,我都尽可能具体、详细地给他描述”,她还负责将小说中人物语言“改成四川话”。秦德君还说,“《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而为《蚀》的名称,也是我提出的。我说,幻灭之感,如日月之蚀,是暂时现象,也是必然现象,茅盾非常赞赏。”三部曲以《蚀》的书名结在一起在开明书店出版,时间是1935年5月,那时茅盾、秦德君仍未分手。
秦德君的讲述,紧扣一点:在那个最苦闷甚而颓唐的时期,是她让茅盾重新振作。除了上面的事例,她还提到茅盾亲口讲过的一些话;这些话,表达着茅盾对她的感恩、珍爱甚至狂热,如:“每当他流露出消沉、悲观的情绪时,我总是耐心地规劝他……茅盾很受感动,说他就像沉沦在大风大浪里,好不容易抓到了我这样一根救生藤。”“他说他不爱他的妻子,要和她离婚,永远和我在一起。”“有一回,我们乘坐高空电车,中途发生故障,电车悬挂空中,乘客们都惊慌起来。可这时,茅盾却露出一张充满激情的笑脸,紧握我的手,凑近我的耳朵说:‘阿姐,就这样掉下深谷里解决了,够多么幸福啊!’”
秦德君说,她先后两次怀孕。第一次是1929年,她回国做了人工流产,然后于9月返日,归途中与胡风轮船相遇——换言之,《胡风回忆录》所提“为茅盾讨版税,看朋友”,并非她此次回国的真正原因(但她确实从叶圣陶那里取得茅盾一笔稿费,用途却是“作住院费”)。第二次发现怀孕则在1930年4月初他们回到上海以后,同样也做了人流,地点是福民医院。
对第二次流产,秦德君有相当凄凉之描写。盖自回沪之后,孔德沚数次前来“哭闹”(其时,秦与茅盾栖身于杨贤江在上海的家中),茅母亦“坚决要求他俩恢复由她一手操办的婚姻关系”——此乃秦刻意之辞,彼夫妇二人从未离异,何来“恢复”婚姻关系一说——而茅盾则渐露屈服之态。当是时,由秦德君提出分手,“茅盾先是不同意,后又同意暂时分手,但要同我订一个‘四年之约’:他以四年写作的稿费支付与孔德沚离婚的费用,然后我俩再图百年之好。经过他的反复劝说,我最终同意了,还约定四年后团圆时,再续完《虹》的后半部。于是他拽着我到附近照相馆合照了一张6英寸照片,说是作为暂时分手的纪念。这是1930年8月的事。”从秦的叙述看,做人流手术与分手乃是同时。秦还说,一周后从福民医院独自回到住处,备感绝望之下,她服安眠药自尽,被侄子发现送到医院救活。
一直至此,我们听到的,全是秦德君一面之辞。在《我走过的道路》里,与这段时间相对应的,是“亡命生活”一节。然而,从18页到48页,整整这一节中,茅盾绝口未提秦德君其人,我们更不能指望听到他表示别的意见。
韦韬、陈小曼《我的父亲茅盾》,也没有转述茅盾本人对此事的任何直接言语,但提供了一些其他细节。他们说,孔德沚是在1929年初冬从叶圣陶那里获知此事,而叶圣陶称,自己是从刚回国的杨贤江那里听说的。顺便指出,《逃墨馆主——茅盾传》的作者似乎把“1929年初冬”理解成“1929年初”了,因而推断孔德沚获悉此事的时间“应为1929年初夏”。这不可能,亦不合理。从秦德君叙述来看,杨贤江的回国当在1929年冬;那时发生了一种形势,日本当局几乎将在日的中共组织一网打尽,“流亡京都的‘红色青年’纷纷回国”,杨贤江大抵即在此人流中。秦德君还说,那阵子她也提议回国,然而茅盾“坚决不肯走,只要我一提起回上海,他就抱着我痛哭流涕”。茅盾何以如此?我个人假设,以杨贤江回国为界,得到消息的夫人乃至高堂大人,多半已有书信来兴师问罪,而茅盾实不知一旦回国,如何措手。
不过,叶圣陶所谓“他是从刚自日本回国的杨贤江那里听来的”,却属托词。他无待回国的杨贤江来告诉他什么,8、9月间,秦德君回国手术,费用即由彼处获得——他替茅盾保存这秘密,已然数月。大约几经踌躇,现在他认清这秘密还是不保存的好。但他总不能从几个月前自己曾为某人提供手术费讲起,恰好杨贤江回国了,这倒是合情合理的由头,于是借这个东风,叶圣陶把茅盾、秦德君之间的故事讲给孔德沚。而叶圣陶“通风报信”之后,到翌年4月初茅盾回到上海,之间长达数月,婆媳不可能不设法与茅盾联系、宣示她们的态度。如果我们的推测合乎逻辑,则在茅盾而言,“何去何从”的思想斗争暗中早已展开,并渐渐有了答案——这便解释了为何回国不久即告分手。
综合各方因素,故事的结局其实是必然的。这故事中总共有四个人物:茅盾、秦德君、孔德沚、茅母。后二人所起作用不言而喻。而茅盾有两个特点,一是奉母至孝,二是禀性理智;这两个特点,既决定了他不可能违母命,也决定了到一定关头他知道并善于反思,行当所行、止当所止。然而最奇怪的,似乎连秦德君自己也在促使故事以这样的结局终止。《我的父亲茅盾》断言,对茅盾来说,这是“并不愉快的插曲”,因为秦德君“是一个只顾自己不顾家的浪漫女性,而且脾气暴躁”。这大约不能视为亲属的袒护,据当时在神户对他二人生活有近距离了解的目击者观察,茅盾会“在不知不觉中对当时与他同居的女友流露出幽怨欠缺的情意。我不便多问,只是直觉地感到他对当时生活的不安与烦恼,有一种难言之隐似的心情,他归国后即与女友分手,可见并非一朝一夕之故。”(钱青《茅盾在日本京都》)可见,故事之如此结局,包含了秦德君这层因素;倘若换一个为人性格与茅盾至为融洽相得的女人,也未必没有其他可能性。
茅盾这一经历,其实倒不值得如何惊讶。一是他对于自己的婚姻,一直以来一定抱着不满意。二是他尚年轻(发生时三十二岁),生命力仍是情胜于理的状态,而且大革命氛围底下,所谓个性的解放也总是与政治激情勃发如影随形,连《我的父亲茅盾》都说那时“杯水主义”爱情是一种流行,“现在父亲自己也陷进了这个泥坑”。三是秦德君其人,年轻、热烈、泼辣、反叛、极其开放(她在茅盾之前,年仅二十岁即曾辗转于二位男性间,与之同居并均有生育),较诸孔德沚,这种“新女性”气质当时恐怕也更易引起茅盾的赞赏(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就写过好几篇鼓吹妇女解放的文章)。四是1927年下半年以后,茅盾真切地陷在“幻灭”中,挣扎于精神和命运的苦海,灵魂最颓唐,意志最脆弱,对于慰藉如饥似渴,亟待找到遗忘、摆脱或者化解绝望的管道。
比较而言,更值得注意或玩味的,倒是他从这一经历中的退却。我们前面谈到了奉母至孝以及与秦德君性情不投对故事结局的影响,其实在我看来那皆非根本。关键是茅盾的性格。本质而论,他是那种安静、内敛、严谨、理性、不浪漫、不喜欢动荡乃至惧怕一切激烈局面的人。综观整个青年时期,血气方刚之下,受着青春的激发,他先后两次置身动荡景状;一次是政治,一次是爱情,而结果出奇地一致:都在矛盾达到顶点时,选择了退却。根因即在他的性格,委实不能适于这种“生活”。他可能一度以为自己能够承受,但到了最尖锐最激烈的时刻,却发现神经实不足以挺过那样的强度——无论在革命中,还是爱情中。经这两次的教育(抑或启迪),加上年龄增长而渐能自觉,此后茅盾基本上彻底地回到固有性格之中,很好地把握了自己。这一点,未来在新疆盛世才那里以及“文革”这两次大的劫难中,都有明确的体现。
他在自己天性引导下从与秦德君的关系中“退却”,与其说是回到孔德沚身边,毋如说是回到“家”中。他是特别需要一个“家”的。“家”对于他,是与动荡的外界之间的一道屏障,是他能够安静地凝视自己的地方,也是一个最终不会失去的藏身之地。我们显然不会说,至少就当时而论他回到孔德沚身边是出于对后者的多大的爱;我们显然也不会说,他这一归来,意味着内心就此泯灭了对妻子以外的异性的“想象”。不过,自那以后“出轨行为”似乎确实未曾再度发生,而其原因,我们宁可认为在于从既有的“出轨”经历中他深刻认识到,这种事情根本不合他的性情。
孔德沚从这件事接受的教训,甚于丈夫。婚后,特别是来上海以后,她只注意到去改变自己“落后”“无知”的形象,比如说进学校补习文化、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以为那样即能缩短与丈夫的差距,却疏于防范和监管。经此一事,她必定痛定思痛,检查自己在何种程度上给了第三者以可乘之机。总之,她从根本上调整了自己的策略,放弃“职业革命妇女”的追求(她已于1925年左右由其好友、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介绍入党)。韦韬说:“从1930年7月起,母亲就完全成了个家庭主妇,把祖母教她的那些治家本领全部施展了出来”。此后,她和茅盾形影不离,把他看得紧紧的,再也没有让丈夫独身一人在外;包括1939年去新疆、1940年茅盾从延安被派往重庆(组织上原来建议她留在延安)、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撤退……在所有这些迁徙中,茅盾总是坚决要求夫妇同行,不仅不能分开,哪怕行程前后脚略微错开亦不情愿。每看到茅盾回忆录中这类叙述,我便不禁一笑:秦德君事件后,孔德沚之严防死守,一至于斯。
虽然茅盾与孔德沚结合出乎母命,对其容貌、教养、品味、脾性等皆难称如意,但最终来看,他最适合的人生伴侣恰恰是孔德沚。本份、忠贞是孔德沚的突出优点;而她持家、治家的能力,料理日常生活时的果决、干练,更给茅盾提供了极大后援。1930年孔德沚从社会回归家庭后,起初,茅盾或许较多感受到的是受“管制”,然久而久之,受“管制”之感便向依赖和倚靠发展。事实上,他再也离不开、缺不得孔德沚。夫妻之情,乃是一个生活实践问题,绝不简单取决于对所谓“理想异性”的预设。只要彼此生而有一种互补的关系,则就会在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生活实践中,达到骨肉般的认同。我们在茅盾夫妇之间,看到的正是这么一种生活过程。
他们这样牵着手,共同走过了五十二年。然而在人生最后一个难关,在垂垂老矣的茅盾七十五岁那年,孔德沚丢下丈夫先自去了。我们知道,自1930年以来,孔德沚未尝一日离于夫君左右,她管理他的一切,照顾他的一切,甚至指挥他的一切,而他则早已只习惯这种生活。偏偏就在茅盾被“文革”从社会中“抹掉”、裹足家中、只剩下“家”的时候,他失去了即便平常也须仰仗依赖的老伴,独守空巢……这该是怎样无边的寂寞!他捧着孔德沚骨灰盒的照片上,表情之凄凉,令人恍然觉得他捧的不是骨灰盒,是“无助”。